從文化關系看中國蒸餾酒技術來源問題
楊海潮 云南大學茶馬古道文化研究中心/茶馬古道研究網www.teahorsetrail.org
從文化關系看中國蒸餾酒技術來源問題
楊海潮 云南大學茶馬古道文化研究中心/茶馬古道研究網www.teahorsetrail.org

楊海潮,云南大學茶馬古道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民族語言與文化關系。
文化相似的邏輯可能
中國的蒸餾酒技術是獨立產生的還是別處習得的?這個問題涉及文化關系的可能性。
從一般意義上來說,不同時空條件下表現相同或相似的兩個文化特征,造成其相同或相似關系的原因,有以下幾種可能:
1,同源。兩個人群系從早期的同一群人分化而來,如果某一文化特征在此人群分化之前就已經出現并為此人群(的各階層)享有,那么,此人群分化為兩個人群之后,在分化出來的兩個人群中一般也會出現。也就是說,兩個人群由于有共同的來源,因此會都具有分化之前即已共享的文化特征。進化論是這種可能的堅強基礎,歷史比較語言學中有非常典型的表現。(徐通鏘1991)
2,接觸。兩個人群不是同出一源,但在長時間的具體接觸過程中,一個人群或者會因為交流的需要而模仿對方的文化特征,或者會因為競爭的需要而強調自己與對方的文化區別,前者使得某種文化特征從一個人群向另一個人群傳播,后者則使得相似的文化特征越來越不相似。陳保亞(1996)細致地呈現了這種傳播的過程,王明珂(1997)顯示了接觸的另一種可能。(當然,兩個人群也可能會共同創造出一個新的文化特征,它在兩個人群的后代中具有同源關系。)
3,偶合。同一個文化特征在兩個人群中出現,既不是同源所致,也不是傳播所致,而是因為這兩個人群出現相似的社會文化條件,促使他們分別創造出同樣的文化特征。Meacham(1977)討論中國南方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關系,其“無中心論研究法”顯示了這種可能性。
4,綜合:這里指以上三種可能性之兩種或三種的綜合作用。例如亞洲、歐洲、美洲各方最初的酒文化應該是獨立產生的,是偶合關系;但現代亞洲的啤酒技術應該是從歐洲學來的,是接觸關系;美洲的啤酒和歐洲的喝啤酒之間則應該是同源關系。
同源關系有幾種較為特殊的形式:一是繼承關系,即父輩和子輩之間的一致,這種關系可以推演到更大的時間尺度(很多世代);二是在文化史上常常涉及的傳播關系,是同源的一種特殊形式;三是模仿或接觸造成的相同或相似,則是傳播關系的特殊形式。如果我們認為不同時空條件下的兩個文化特征之間具有傳播關系,就必須排除其他可能,對這種解釋的唯一性給出嚴密的論證,或者給出可以查證的傳播節點與過程。
古人海量的解釋路徑
漢魏以來的中國古人好像酒量都很大,文獻中常見某人能喝多少石、多少斗而不醉的記載,即使剔除其中明顯的夸張成分,好像也都令人難以置信,因此自宋代以來就有人懷疑過這一點,并提出了許多合理化解釋。
這些解釋的思路大致有三種:一是古今計量制度不同,二是古今酒器不同,三是古今酒質不同。(酒量大小之別也可能是體質原因造成的,但目前還沒有人據此立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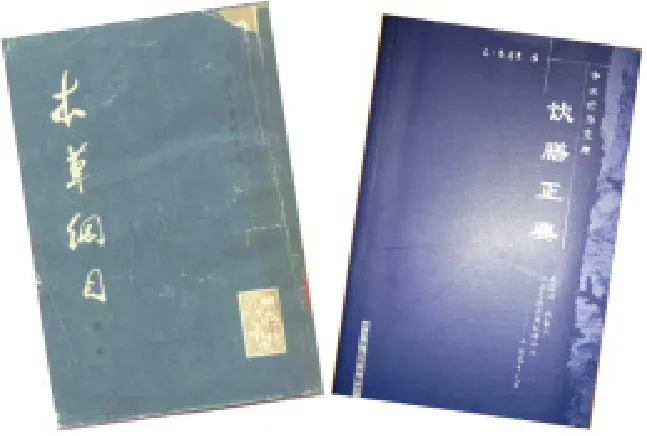
沈括(1031-1095)《夢溪筆談》卷三“辨證一”提出了計量制度變遷的問題(也涉及了制酒法變化導致的酒質不同):“漢人有飲酒一石不亂,予以制酒法較之,每粗米二斛,釀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醨者,每秫一斛,不過成酒一石五斗,若如漢法,則粗有酒氣而已。能飲者因多不亂,宜無足怪。然漢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邪?或謂‘石乃鈞、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計之,石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國飲酒數石不亂,疑無此理。”(2)
這種懷疑沒有將古代的酒器與量具區分開來。王瑤先生注意到了這個區別,認為飲器中最小的是升,樽爵是通稱,斗大概是最大的飲器,文獻說古人用斗飲酒,好像用碗飲,是取其容量大的意思,所以最不能飲酒的人也能飲二升,而多的可以到數石。唐宋以下,以斗作權量的單位,飲酒改用杯盞,所以飲量很少能有到一斗的。(3)但是王瑤先生沒有提及酒精度的古今差別問題。
李時珍(1518-1593)《本草綱目·谷部》“燒酒”條提出中國在元代才有蒸餾酒:“燒酒非古法也。自元時始創其法,用濃酒和糟入甑,蒸令氣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壞之酒,皆可蒸燒。近時惟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秫或大麥蒸熟,和麴釀甕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極濃烈,蓋酒露也。穎曰:暹邏酒以燒酒復燒二次,入珍寶異香。其壇每個以檀香十數斤燒煙熏令如漆,然后入酒蠟封,埋土中二三年,絕去燒氣,取出用之。曾有人攜至舶,能飲者三四杯即醉,價值數倍也……”這種“燒酒”,又名火酒、阿剌吉酒。按照這種觀念,古今酒質差別也會使古人的酒量大于今人:元代以來的中國人喝的酒一般都是白酒(蒸餾酒),酒精度較高,所以酒量較小;而元代以前的中國人喝的酒是甜酒或黃酒、果酒(4),酒精度較低,所以酒量較大。何滿子先生就以蒸餾酒在元代才進入中國判斷古人喝的酒度數很低,所以酒量很大,結論是“現在許多名酒,如汾酒中的竹葉清,四川名酒劍南春,河南名酒杜康酒等,原來的甜酒釀型的傳統酒中就有這些名牌,當根本不是蒸餾法釀造的白干酒,現在這些酒都承襲了古代的酒名,其實和古代名酒是兩種釀造法不同的品位迥異的同名異品”。(5)
但是,文獻有古人“一醉三年”甚至“醉死”的記載,前者如劉玄石(干寶《搜神記》卷19、張華《博物志·雜說下》)、周顗(《晉書·周顗傳》),后者如鄭玄(《三國志·魏書·董二袁劉傳》裴注引《英雄記》)、丁沖(《三國志·魏書·任城陳蕭王傳》裴注引《魏略》)、周顗的朋友(《晉書·周顗傳》)、傅奕(《舊唐書·傅奕傳》),說劉伶“一醉三日”的材料就更多了。如果元代以前的酒都不是蒸餾酒,這些醉酒故事如果僅僅是文學夸張而沒有事實經驗作為支持是不能被人們認可和流傳的,至少“一醉三日”并非不可能之事。另一方面,酒精度之高低,不能成為判斷一種酒是不是蒸餾酒的充分證據,因為也有度數很低的蒸餾酒(“低度白酒”)。所以,從古人酒量之高低,不能判定他們所飲的是不是蒸餾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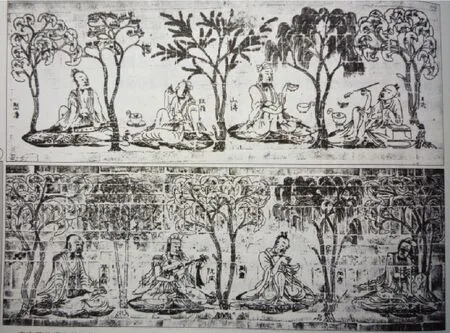
《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雕,南京西善橋南朝大墓出土)
總之,對于古人的酒量之大,以上列舉的這三種解釋思路,似乎都有道理,但如果承認中國古代沒有蒸餾酒就都不足以解決問題。例如,何滿子先生說“這種以蒸餾法提取的高度酒,即使以一爵為一升能夠喝上一斗(以二市兩為一爵,也有兩斤)的,的確是海量了”(6),我認為其不足在于對好酒量、大酒量的想像過于保守了一點,我就多次見過喝高度白酒兩三斤不醉的人,那才叫好酒量。
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于元代以前中國有無蒸餾酒。
蒸餾酒技術為中國原產的證明方法
證明中國蒸餾酒技術的獨立發明,可能有文獻、考古、語言、酒價、酒量、飲酒方式等途徑。目前沒有文獻直接記載元代以前的中國有無蒸餾酒技術,考古工作也沒有發現元代以前的蒸餾酒遺存,因此下面來看后幾種方法。
1,語言:從理論上說,根據歷史語言學的方法,可以通過比較各種語言及其方言之間的蒸餾酒的名稱有無系統對應關系,判斷它們是不是同源詞,從而判斷蒸餾酒技術是不是這幾種語言的主人發明的。例如李炳澤先生認為國內的許多語言中“關于蒸餾酒的詞匯則驚人的相似,這是由于文化傳播所造成的現象,如南方許多民族語言中來源于漢語‘酒’的形式,而北方民族多為‘阿剌吉’”,而“阿剌吉”很可能出自蒙古語詞匯araqi(7)。
實際的語言現象似乎比這復雜得多,例如壯侗語“酒”似乎與漢語“醪”有關系,白保羅(Benedict,P.)認為是漢語從壯侗語借入的:漢語lau ← qlau“醪”(醇酒、酒),澳泰語*(ng)qlarn;漢語普通話tsieu← t s i o/g“烈酒、酒”可能是派生詞(8),而張公瑾先生則認為壯侗語lau3“酒”和lau4“酉”是從漢語借過去的,其時間早至漢代(9)。目前我還沒有能力理清楚其間的關系,這里只討論“阿剌吉”問題。
“阿剌吉”這一酒名,在元代的文獻中有不同的寫法:1)“阿里乞”。《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已集“南番燒酒法”:“南番燒酒法(番名阿里乞)。”2)“阿剌吉”。忽思慧《飲膳正要》:“阿剌吉酒,味甘辣、大熱,有大毒。主消冷堅積,去寒氣。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許有壬《至正集·詠酒露次解恕齋韻》:“世以水火鼎煉酒取露,氣烈而清,秋空沆瀣不過也,雖敗酒亦可為。其法出西域,由尚方達貴家,今汗漫天下矣。譯曰阿剌吉云。”3)“軋賴機”。朱德潤《軋賴機酒賦》:“至正甲申冬(元惠宗至正四年,1344年),推官馮時可惠以軋賴機酒,命仆賦之,蓋譯語謂重釀酒也。” 4)“哈剌基”。葉子奇《草木子》:“酒法,用器燒酒之精液取之,名曰哈剌基酒,極濃烈,其清如水,蓋酒露也。……此皆元朝之法酒,古無有也。”
那么“阿剌吉”又從何而來呢?阿里·瑪扎海里(Mazaheri,A.)認為波斯語araqi的源頭在蒙古語,亞美尼亞語araqi/raki指葡萄酒,印度-烏爾都語arrak指朗姆酒,它們都要追溯到蒙古語詞源araqi。蒙古文arik’kxi指奶子酒,鄂爾多斯蒙古語xara ari’kxi指糧食酒、ari’kxi dararun指燒酒,它們在13世紀中葉傳入波斯。(10)這項研究提示我們,“阿剌吉”系列名稱在元代出現在漢語中,但被李時珍誤以為其指稱對象(蒸餾酒及制作其技術)在元代才開始在漢族人中出現。《本草綱目·谷部》“燒酒”條區分“元時始創其法”的“阿剌吉”是通過蒸熬好酒得到蒸餾酒與“近時”直接蒸熬糧食得到蒸餾酒,奇怪的是李時珍對時間晚近的后一種方法的具體來源卻一無所知,也傾向于支持李時珍純屬誤解。否則,如果漢族的蒸餾酒技術來源于蒙古,已知中原與北方從商周以來就有來往、蒙古族和漢族鄰居且長期交往,我們不僅需要證實蒙古族創造了蒸餾酒技術,還需要證偽這種技術在元代以前沒有從蒙古族傳播到漢族、蒙古族的蒸餾酒技術其實是從漢族習得的,但目前看來證實或證偽都還很困難。
回過頭來看,忽思慧《飲膳正要》成書于元文宗天歷三年、至順元年(1330年),其中關于酒的內容包括卷一之“飲酒避忌”、卷二之“神仙服餌”和卷三之“米谷品”,“阿剌吉”見于“米谷品”之“阿剌吉酒”條,“阿剌吉”之名及蒸酒得露的制法至此在漢文獻中第一次出現,但其中并無只字提及這種酒的制作方法來源或傳播關系,以此推定蒸餾酒技術要晚至元代才傳入中國,證據不足。《飲膳正要》“阿剌吉酒”之前一條為“葡萄酒”條:“益氣調中,耐饑強志。酒有數等,有西番者,有哈剌火者,有平陽、太原者,其味都不及哈剌火者。田地酒最佳。”由于此書“米谷品”下各條所列的酒只能從其名稱和制法中的“釀酒”與“蒸熬”看得出是否蒸餾酒,而沒有片言只字提及酒精度問題,本條所列“西番者、哈剌火者、平陽、太原者”以及“田地酒”就很可能都是蒸餾酒,而“哈剌火”一名與“阿剌吉”的關系尤其值得關注。
2,酒價:同樣數量的同一種糧食,用來做酒,所得甜酒、黃酒較多,白酒較少,差別至為明顯。按此,同等重量的酒,甜酒、黃酒的價格就應該明顯低于白酒。如果我們能找到足夠多的這類價格數據,大概既可以看出當時有蒸餾酒。
劉攽(1023-1089)《中山詩話》:“(宋)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莫能對,丁晉公獨曰:斗值三百。上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亦一時之善對。”丁謂(966-1037)所舉的詩句,見于杜甫(712-770)《逼側行,贈畢四曜》:“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全唐詩》卷217)杜甫因重寫實而有“詩史”之號(孟槳《本事詩·高逸》、《新唐書·杜甫傳》、胡宗愈《成都草堂詩碑序》),這里所說的一斗值三百錢的酒價,即可能出于經歷。
杜甫此詩作于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春,當時他在收復后的長安任左拾遺,是他最后為官的時期,也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時期(11),但他以為用三百文銅錢買一斗酒(不必把這里的數字當作確切值)的價格比較貴(“街頭酒價常苦貴”),而且是一斗酒幾個人喝(“相就”而飲),數量并不多,因此他買的大概就是蒸餾酒。(12)
3,酒量:同一個人或一些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喝酒,雖然體質會影響到具體的某一次宴飲時的酒量,但如果他們表現出前后酒量明顯不同,就應該是喝了酒精度明顯相差較大的酒所致,而酒量明顯較小的時候所喝的酒可能就是蒸餾酒。
這種材料較少,我們因此轉而看酒量的時代差別。何滿子先生說“古書上提到能飲一石的人,都是南北朝以前的,唐代以后就沒有了”(13),如果蒸餾酒技術在元代才傳進中國,即使考慮計量制度及酒器之古今不同,古人的酒量從元代開始應該再大減一次。歷史資料是否會顯示這樣的狀況呢?
先看唐人的酒量:唐代的大斗為6000毫升、小斗為2000毫升(14),考慮到量具與酒具之別,這里取小斗,那么杜甫《飲中八仙歌》提到唐代八個名人的酒量,焦遂10公斤,王源中3.4公斤,李白1.7公斤,李群玉1.7公斤;再看元人的酒量:郭天錫“有鯨吸之量”(俞希魯《郭天錫文集序》)、“醉傾一斗金壺汁”(楊鐵崖題郭界《春山圖》),可以喝9.5公斤酒,雖然不無夸張成分,但好酒量應該沒有問題,否則就算不上豪飲、也不值得時人稱道了。按此,元代中國古人的酒量并不低于唐代,這似乎說明元代才傳進蒸餾酒技術的說法并不可靠,除非元代的士人都放著蒸餾酒不喝而只是喝甜酒、黃酒、果酒了,我認為這是難以想象的。
4,飲酒方式:制作蒸餾酒用的蒸餾器不是一般人自己就可以做得出來的,而甜酒、黃酒的釀造則簡單得多,所以一般人家自己就可以做甜酒、黃酒,但白酒則需要去買。因此,如果鄉野小民也常去買酒,但是帶回家中而不是在酒肆等處就喝掉,那么他們所買的就應該是白酒,否則就不必去專門的酒肆買酒回家了,因為家中一般都會有自釀的甜酒、黃酒。
唐代西域胡人經商、流寓長安的數量不少,在長安賣酒為生者較多,屢見于唐詩如王績《過酒家五首》、李白《前有樽酒行》、《醉后贈朱歷陽》、《少年行》等,長安的食品中以高昌法制出的葡萄酒及依波斯法制出的三勒漿(庵摩勒amalaka/amola、毗黎勒vibhitaka/balila、訶黎勒haritaki/halila)等均為西域傳來。(15)一方面,在唐代之前,西域一帶的釀酒葡萄和食用葡萄已傳進中國,那么隋唐時代寄居長安和蜀地的胡人喝的葡萄酒應該是在當地釀造的,否則成本過高。另一方面,唐代詩人喜歡去胡人經營的酒店喝酒,不能都理解為僅僅是胡姬貌美的吸引,更大的西域運來的可能是這些胡人賣的是蒸餾酒。
下面再通過一個較早的故事來看這個問題,單獨列為一節。

開元款龍紋陶瓶(劍南春酒廠征集)
劉備禁酒和“劍南燒春”的性質
《三國志·蜀書·許麋孫簡伊秦傳》記載,蜀漢期間,“……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如果故事里說的官吏在人家家里找到的“釀具”就是通用的缸、甕之類家庭生活用具,官吏自然無法將其與其他生活用具區分開來,也就不能推斷其主人為“欲釀者”,因此只能是一種專門的制酒工具。
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七“造神麴并酒”專講制酒方法,其中提到的制酒工具如下:1,碗、甕、瓦瓶、炊釜、鐵范、量、臼;2,泥、草、竹、箔、紙、筆、刀、繩、磚、屋、戶、帚、席、布、錦、帛、氈、床;3,甑(蒸、餾)、鍋(炒、炊)、硙(磨)、桶(汲水)、銼(銼)、紗(漉)、椎(搗、槌)、錐(穿孔)。(16)從這份清單可見,直到南北朝,釀造甜酒或黃酒使用的都是一般的家庭生活用具,并不需要特制的器具。因此,蜀漢官吏在人家家里找到的那種“釀具”不可能是無法區別于一般的家庭生活用具的制作甜酒或黃酒的工具,而可能是專用于制造高度酒的蒸餾器。
這一點以當時的四川已經生產蒸餾酒為前題。我們來看這個前提是否可能成立。
李時珍《本草綱目·谷部》“葡萄酒”條說“……葡萄酒有二樣:釀成者味佳,有如燒酒法者有大毒。……燒者,取葡萄數十斤,同大麴釀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紅色可愛。古者西域造之,唐時破高昌,始得其法。……《飲膳正要》云:酒有數等:出哈喇火者最烈,西番者次之,平陽、太原者又次之。或云:葡萄久貯,亦自成酒,芳香酷烈,此真葡萄酒也”,其中分葡萄酒為“釀酒”與“燒酒”兩種,從其所說燒酒之法可以肯定就是蒸餾酒,但是他又說“燒酒”在唐朝破高昌時(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年)就已經得到其制法,那么中西亞的蒸餾酒技術傳入中國的時間就早至唐代初期,與上引《本草綱目》“燒酒”條說燒酒“自元時始創其法”相矛盾,但是支持中國在元代以前就已經有蒸餾酒技術的主張。
西北以至中西亞一帶的居民在東漢就已經大量進入四川,有的胡商甚至形成世家大族(17),四川與中西亞一帶長期保持著商業往來,“六朝、隋唐時代蜀漢亦為西胡行賈區域,其地之有西胡人種往來僑寓,自無足怪也”(18),因此,他們生產蒸餾酒的技術自然也可能早已傳入四川。七世紀中葉成書的《唐本草》已經講到用葡萄制醋(我沒有查到原文,參見勞費爾1919:58),由于制醋的方法和蒸餾酒技術極其相近,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
以上可能性為我們理解“劍南燒春”的性質提供了一個參照。
李肇《國史補》卷下:“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19),河東之乾和蒲萄,嶺南之靈溪、博羅,宜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漿類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謂庵摩勒、毗梨勒、訶梨勒。”這里提到的“劍南燒春”也見于《舊唐書·德宗本紀》:“大歷十四年(779年)五月辛酉,代宗崩。癸亥,即位于太極殿。……(閏月癸未,)劍南歲貢春酒十斛,罷之。”
“劍南燒春”是不是蒸餾酒,文獻沒有說明,無法判斷,但一斛為五斗,即使是取大斗,劍南一年才進貢“春酒”30公斤,其數量明顯較少。“劍南燒春”必有其過人之處才能作為歲貢,傾向于支持其酒精度比較高,“劍南燒春”可能是蒸餾酒。(這一點是陳保亞老師提出的。)
此外,杜甫《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說“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全唐詩》卷227),由于中國文化對酒的態度歷來貴清而忌濁,漢語中古音“農”(泥鐘和三平通)與“清”tshg(清清開三平梗)都符合詩律要求,杜甫在這里用“濃”字就應該是專指酒精度而不是粘稠度(否則這樣的蜀酒就不值得夸耀),也傾向于支持“劍南燒春”是蒸餾酒。
陳保亞1996,《論語言接觸與語言聯盟——漢越(侗臺)語言關系的解釋》,北京:語文出版社。
勞費爾(Laufer, B.)1919,《中國伊朗編》,林筠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
李約瑟(Needham, J.)等1980,對東亞、古希臘、印度蒸餾酒精和酸醋的蒸餾器的試驗比較,潘吉星主編《李約瑟文集》,沈陽:遼寧科技出版社1986年。
Meacham, W., 1977, Continuity and Local Evolution in the Neolithic of South China: a Non-Nuclear Approach, Curent Anthropology, vol. 18, no. 3, 1977,pp.419-440.
王明珂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有限公司。
徐通鏘1991,《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趙榮光2006,《古代傳統飲酒觀的演變及中國人飲酒的時代特征》,《飲食文化研究》2006年第1期。
文中注釋
(1)也有人以酒器的變化來推斷蒸餾酒出現的時間,例如:1999年瀘州市區營溝頭的一處古窖址發掘出土了唐五代時期的陶器酒具,其中有20余件較獨特的小型盛酒器,由于只有高度酒才應小器盛、飲,因此當時已經出現蒸餾酒。這種推斷略嫌勉強,因為人們對于地位尊貴的人(如帝王、高官、長者、名士等)賞賜或贈送的好酒,由于感激和珍重而不愿輕易飲盡,就可能會小杯啜飲而不是大碗牛飲,這時候酒器之大小就不能反映酒精度之高低。
(2)葉夢得(1077-1148)《石林四筆》的解釋思路與此類似:漢代一石為一百二十斤,折成宋秤只有十九斤多一點,但也不是一個人的肚子能裝得下的。(《夢溪筆談》同卷先已討論過計量制度的歷史變遷問題。)
(3)王瑤《中古文學史論》,174-17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48/1986年。
(4)例如賈思勰《齊民要術·笨曲餅酒》記載了蜀人釀制酴酒的方法,其中的“酴酒”即醪糟酒(濁醪)。
(5)何滿子《中國酒文化》,30-36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09年。
(6)何滿子《中國酒文化》,36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09年。
(7)張公瑾主編《語言與民族物質文化》,73-85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
(8)白保羅《澳泰語研究:澳泰語和漢語》,羅美珍譯,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語言室編《民族語文研究情報資料集》(8),1987年。
(9)張公瑾主編《語言與民族物質文化》,5-7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
(10)阿里·瑪扎海里《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耿昇譯,66-67頁,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關于“阿里乞、阿剌吉、軋賴機、哈剌基”這四個名稱的來源,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最先提出來自阿拉伯文araq,劉廣定先生說在勞費爾之前已有Fairley于1905年所列各地的蒸餾酒之名與之相近者即有印度、錫蘭的arrack、蒙古的arika、西藏的arra及南太平洋島嶼的ava。但是我沒有查到劉廣定先生的論著原文。)
(11)王滋源《說杜詩〈逼側行贈畢四曜〉》,《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83年第1期。
(12)唐詩中最常見的酒價是“斗酒十千”,例如王維《少年行》、李白《行路難》、李白《將進酒》、白居易《閑賦詩》、權德輿《放歌行》、陸龜蒙《奉和襲美酒中十詠·酒壚》,但這些詩篇的寫作時間和地點不盡相同,不可能表明各地、各時的酒價都一致,所以王(1151-1213)《野客叢書》卷三“漢唐酒價”條以為“斗酒十千”只是借用曹植《名都篇》“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的典故贊譽美酒,而非確指酒價。
(13)何滿子《中國酒文化》,30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09年。
(14)本文使用的中國歷代的計量制度,來自王力主編《王力古漢語字典》附錄,1807-1815頁,北京:中華書局2000/2007年。
(15)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35-42、52-54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62/2001年。
(16)第三類沒有直接寫出器具名稱,但從其所說釀酒行為中可推出需要使用的工具。此外,此卷評價“世人云:‘米過酒甜。’此乃不解法候”,并引“《食經》七月七日作法酒方”,從酒的味道及出酒量看,可知所講的是甜酒或黃酒,而不是蒸餾酒。
(17)吳焯《四川早期佛教遺物及其年代與傳播途徑的考察》,《文物》1992年第11期;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194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霍巍、趙德云《戰國秦漢時期中國西南的對外文化交流》,152、270-273頁,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
(18)陳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問》,《金明館叢稿初編》,279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9)或作“富平之石梁春,劍南之燒香春”,但《四庫全書提要》評論此書“余如摴蒱盧雉之訓,可以解劉裕事,劍南燒春之名,可以解李商隱詩”等句,因此本文還是取“劍南之燒春”。此外,唐人好像喜歡將酒稱為“春”,這可能對于理解“燒酒”、“燒春”的性質有重要關系,但這里無力詳考。
(統稿:本刊編輯夏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