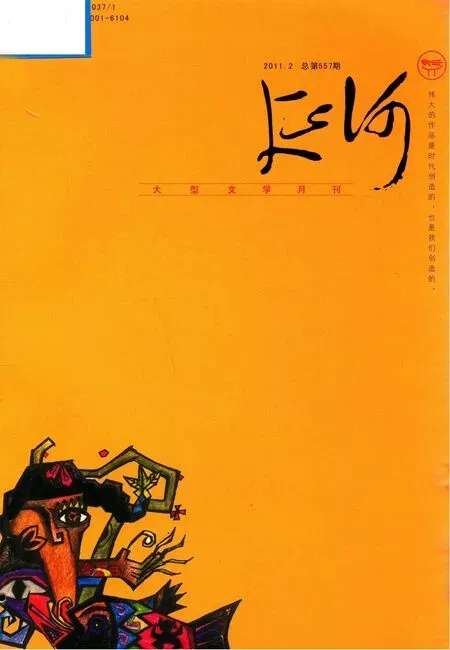美麗的刀子
黃孝陽
美麗的刀子
黃孝陽
1
一個女人。她的美麗像刀子
捅入我的心臟。我想拔出它
又怕鮮血驚嚇了她沉靜的面容
“你應該聽說過這部電影,《桃色交易》。一部老片,改編自歐?亨利的短篇小說,一個乏善可陳的關于金錢與人性的故事。但我喜歡魅力四射的黛米?摩爾,她真美,完美無瑕,至少在扮演這個為了錢與百萬富翁共度良宵的有夫之婦時,她的美麗就像一把完美的刀子。”
午后的街道有著輕微的鼾聲。從高大梧桐樹里漏下的陽光猶如雨點,輕敲著玻璃。玻璃潔凈,恍惚不存在。但數只俯在玻璃上的蒼蠅還是用它們的絕望透露了這個秘密。你們在一幢灰房子的二樓。是一間茶餐廳。不大,寥寥幾個客人,面容暖昧,多半沉默無語。
你呷著杯中暗綠色的液體。他掐滅煙,問侍應生要來紙與筆,很慢地寫下這三個句子。然后把紙條遞給你。字跡挺拔整齊,結體寬扁穩健。
“我的一個朋友的故事,有點俗,也有點匪夷所思。你有耐心聽么?”
他鼻翼處有兩小團陰影,像兩小塊擦不掉的污漬。那是光線的杰作。他的臉很有雕塑感,眼里有血絲,左眼下角有粒痣,身體始終在微微輕顫。
2
女人出生于1980年12月16日。喜歡看法國電影,聽古典音樂,父母健在,還有一個弟弟在念大學。
在一次朋友聚會上,他遇到她。追了她三年,她始終不遠不近,就好像他是行星,她是他圍繞運行的恒星。于是,他說,“請給我七天時間,我們一起去鳳凰古城。如果在經過這段日子后,你仍然不能接受我,我送你一輛凱美瑞。若你覺得我還可以,那我們就發展成戀人關系,車子我也就不送了。”他是從《桃色交易》里得到的靈感。覺得這也算是一種對愛的表達方式。她怎么想的,他不知道。但他這樣說的時候,真覺得她就是黛米?摩爾。
幾天后,她答應了。他們相處得很愉快,有了性生活,還一起與苗族婦女討價還價,買下一大堆銀飾、剪紙、蠟染。她甚至在梳洗畢還對著沱江的早晨快樂地呼喊:“時間啊,請你停止下來吧。”氣流帶著她的體溫,又因為她舌尖的跳躍,有了宮商角羽。他臉頰發燙。她真是勇敢啊。他把來自于她喉嚨深處的氣流貪婪地吸入腹中。她的聲音讓江水更青,江面撐船的阿哥用槳敲船幫,咿咿呀呀地唱。唱的是:秋天落葉遍地黃,哥想妹來妹想郎。唱至最后一句,江面上齊齊響起一聲“吆哦喂!”
她抿嘴笑,就人來瘋,接著唱。唱的是:日出等到日頭落,阿妹等哥來拍拖。
他真喜歡她的樣子,鮮嫩活潑。她與那個他認識了三年的女人好像是兩個人,又或者說前者是從后者體內長出來的。“別人都知道她的美,但只有我知道她的更美。”在幾個時刻,他真想拜倒在她腳下,去親吻她行走后的塵土。他盡了最大的努力才克制下這種莫明其妙的沖動。他不能讓她知道他的這種感受。不能,永遠不能。
他們在狹窄的老街走來走去,嚼松糕、聞熏肉、嘗姜糖,訪沈從文故居,進田家屋,找《烏龍山剿匪記》內景拍攝地——陳斗南宅院。他們倆把青石板踩得是叮當作響。“祖宗明德遠矣,子孫勿替引之。”他們進楊家祠堂。她一本正經地朝正殿里供奉的楊家祖先牌位鞠躬作禮。汗濕了她的鬢角。他忍不住在她腮上親了口。抹著脂粉的講解員嘻嘻笑,把他們領到右側廂房,那里有一張明清式樣的雕花大床。“苗族的愛情就是忠貞。上得這個床,新郎就要對新娘說一句話。什么話呢?床上只睡你和我。一輩子也不準換人。”她向他挑來一眼。這一眼就是一把嫵媚的刀子,要掏出他的五臟六腑。而這將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他勃起了,竟然在那個地方。她發現了。他們來不及趕回賓館,沿木梯悄步上了正殿對面掛著“合族同鑒”牌匾的戲臺,在繪有“楊母教子”的屏風后面,他捂住她嘴中瀕臨死亡動物般的叫喊,用了一分鐘時間,在她體內一泄如注。他是瘋了。她也瘋了。他們都瘋了。
“知道嗎?楊家祠堂原來是鳳凰縣政府駐地。”
他們走出這所側開大門的祠堂。十指相扣,相互拖曳。一種觸電般的麻木使他肌肉僵硬。若沒有她,他就是行走不便的殘疾人了。他是如此感激自己那個拙劣的想法。那一定是因為上帝憐憫,才把它塞入他的腦袋。因為它,他才第一次真正獲得完整,就像凸獲得了凹。
一位兜售“西蘭卡普”的土家族婦女攔住他們。一種圖案斑斕的土家織錦,或為衣裳,或為被蓋,色彩極鮮明熱烈。她的眼睛濕潤得就如同眼淚,“買這張鴛鴦戲水的吧。”他把婦人手中的織錦全買了下來。“她就好像林中空地上的一個池塘,既清澈又深邃。”他忘掉是誰寫的這句話,它在他腦海里一聲聲叫得清澈,猶如鳥鳴。
第五天晚上,他們在家小店吃血粑鴨,手機響了。是他公司里的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鬼使神差,他說,“公司里有急事,我得先趕回去。”然后,他們都愣了。她的筷子掉在地上。他起身重拿筷子時,又打翻了一碟苗家酸蘿卜。蘿卜酸中帶辣,非常好吃。他想起那句話的作者是誰,是毛姆,尖酸刻薄而又才華橫溢的毛姆。書名,《尋歡作樂》。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32開,封面是一個波浪頭發穿紅裙的女人。那是毛姆前妻羅西。“她就好像林中空地上的一個池塘,既清澈又深邃。跳到里面去會覺得很暢快,即使一個流浪漢、一個吉普塞人和一個獵場看守人在你之前曾跳進去浸泡,這一池清水仍然會同樣地清涼,同樣的晶瑩清澈。”他的眼淚幾乎要掉了下來。
翌日,他們回到他們生活的城市。他打電話問她什么時候來拿車,或者給他一個賬號。她嗯了一聲。他聽見話筒那邊刻意屏住的呼吸。他在等待她的聲音,她所等待的又是什么?她終于掛斷電話。他覺得自己都是《等待戈多》里的一個莫明其妙的人。他與墻壁談了幾分鐘的巴赫的《馬太受難曲》,以及巴赫去世五十年的無人問津;又與桌子上的水晶擺件說了一會兒法國電影《羅曼史》,那是一個女人以性為武器與世界斗爭的過程;再上了互聯網,通過校內網把她弟弟的相片與其最近的日常活動瀏覽了一遍。
他們姐弟倆長得真像啊。
心里像被針尖扎了一下,漏了,癟了。成千上萬只螞蟻爬出來,爬上嘴唇,爬至胸膛,爬到膝蓋。骨骼都成了螞蟻。他往胃里倒了一整瓶紅酒,癱軟在地,渾身酸痛虛弱。幾天后,他去南京,找到小百花巷,那是她長大的地方——她在博客里寫下太多的相關文字。那些文字是蝴蝶翅膀上的粉末,一片一片,像魚鱗一樣,有著無以倫比的絢麗之色。小巷曲直深幽,兩側民居青磚小瓦,墻體斑駁,石灰脫露處,偶有數塊燒有銘文的明城墻磚。屋檐的瓦當上多有蘭草花卉,最多的是福壽兩字。又有古井,古井邊有汲水的紅衣婦人,腰肢處露出月牙白。那是普生泉,據說為乾隆皇帝賜名。她是喝著這井水長大的。在離小百花巷不遠的一處小區,他瞥見她父母。這并不難辨認——他在她QQ空間的家庭相冊里早已熟悉兩位老人的臉龐。他沒有想到的是,當他親眼目睹兩位彼此攙扶著的老人,突然有了一種幻覺:那也是他的父母。他默默望著,眼淚汪汪。
手機響了,她打來的,約他今晚吃飯。他幾乎是哽咽著說,“好。”她說了時間地點。他遲疑了一下。他沒法在短短數時辰內趕回去。他說,“明天?”
那是他有史以來最難下咽的一頓晚餐。盡管她用了蘭蔻口紅,抹了迪奧香水,還穿上了她從法國帶來的露背晚禮服,他們之間曾擁有過的親密已經蕩然無存。他結結巴巴,像三流演員背著拙劣的臺詞。他羞愧難當。當她抓住他的手掌,他突然覺得身體不再屬于自己,形同虛設。她幾乎是怒氣沖沖地在他面前褪下衣裙。那個曾被他稱為世上最美的花園,就像是宇宙的黑洞。
3
想念藏在你身體里的天鵝絨,與
蔓延在你臉龐上的火
世上的女人都是你,也都不是你
你是夏娃、大地之母,以及:

室內蝸牛 1920年 拼貼鉛筆畫 31.2×22.2cm
所有要被贊美的雌獸
他喃喃自語,眼睛里有著絕望的光,左眼下部的痣跳得頗有幾分驚心動魄——相書上說,眼下有痣,情多波折。但平心而論,他說的故事確實濫俗。你也沒弄明白這種“俗”又是如何完成向“匪夷所思”的驚險一躍。
你去過鳳凰古城。它有一張奇異的面孔,半邊是眉目如畫的處子,色彩鮮明純凈;半邊是艷俗的放蕩婦人,表情曖昧夸張。這構成它獨一無二的魅力,一種獨特的審美形式,就猶如夜里從沱江水面上飄過的生活垃圾,在散發著潮濕腥味的同時,又彌漫出夢幻、超越現實的光影。它不再是鄉村,也不愿意進化成城市——那是人類最后的高潮。它對鋼筋水泥金屬玻璃有著最本能的警惕,那將使它喪失自己的名字。又或者說,它就像一顆廉價的彩色玻璃球,被一種不加掩飾的膚淺與惡俗,兜售給了蜂擁而來的旅人。人,在那里,極易被催眠,被自我催眠。所以“他同我演戲,我回報以演技”。
窗外的陽光像一個薄得透明的水泡。水泡表面流轉著紅橙藍綠。它們是冰涼的手指,緊捏著你的眼球與心臟。你仿佛置身于傾斜的甲板,不得不努力克制著惡心與不適。盡管你并不想去看,目光還是情不自禁地越過一幢幢房子。
在一所有著深遠出檐與凹曲屋面的房子里,你看見了她,看見了她身上的那個男人。她出生于1980年12月16日,是你的合法妻子。男人,你也認識。一個來自湖南湘西的民工,二十三歲。你永遠也忘不掉他胳膊上紋著的那只模樣猙獰的藍虎。一年前他綁架了她,你給了他十萬塊錢;現在,他們睡在一起。顯然,這并不是他們第一次睡,否則也不可能睡得這般藝術。你不明白發生了什么,更不想去弄明白。妻子,一個多么可笑的詞匯。口中吐出酸水,如同懷孕之婦人。你怔怔地想著。心臟不是被貓抓了,是被小刀剮過,橫著剮了一千零一刀,豎著又剮了二千三百七十四刀。每一刀剮下來的肉皆米粒大小,還會在刃尖跳。
你咬緊嘴唇,讓自己不至于呼喊出聲。你一點點收回目光,手指下意識地按在自己左眼下角那個因黑素細胞增多引起的皮膚突起。你凝視著他的臉,那是你在鏡中所見。“那我要找的面孔,就是世界創造之前我的臉龐。”你嘟囔著,合上眼瞼,拳起四指,以左右大拇指羅紋面按住兩側太陽穴,再以左右食指第二節內側面輪刮眼眶上下一圈。這是小時候學過的眼保健操。
你看見他笨拙地擋開她的手。
她想替他系領帶。你不明白為什么直至今日此刻,她還能這樣深情脈脈。她的表情有點兒吃驚。她在叫他的名字。他覺得他的名字被她的嘴弄臟了。他很想對她說,不要用舔過別的男人那玩意兒的嘴叫他的名字。他拿起公文包。她再次伸手過來,不容拒絕,迅速系好那根斜紋灰底的布條兒。他看著她的眼睛,慢慢地彎下脊背,慢慢地,在她臉頰上親了一下,就與過去一樣。他出門下樓,進地下車庫,把車倒出。在后視鏡里,他看見她還在二樓的窗戶邊站著朝他揮手。他扯掉領帶,擦掉眼眶里溢出的液體,把車拐進林蔭小道。他不知道他的手為什么要發抖,便用力給了自己一耳光。他踩住剎車,凝視著小指上的戒指。戒指深深地嵌在皮膚里,好像是骨頭長出來的一部分,慘白。是她給他戴上的。他粗魯地把手指塞入嘴里。他想阻止什么,還是無濟于事。喉嚨里迸出一聲尖銳的叫喊。他被這聲音嚇了一跳,茫然地望了眼車窗外面。湛藍的天空在幾株梧桐樹的后面,對著這個世界露出古怪的笑容。一種難以言喻的酸楚揪住他的鼻子。黏滑的淚水洶涌直下。他嚎啕痛哭,俯在方向盤上,哭得是那樣傷心,連車身都跟著他的哭聲在顫抖。就好像這個方向盤擰開了他身體深處藏著的閥門。這令人難過,但并不奇怪,你還在北京洶涌人潮的王府井大街上,看見一個白發老者放聲大哭。
你皺起眉頭,小聲問道,“為什么?”
4
餐廳里有一對男女。可能是夫妻,也可能不是。他們坐在你隔壁,聲調不高,剛好還能聽見。語速不快,基本沒有什么平仄起伏。從你這個角度望過去,剛好還能見到那個男人的小半邊臉。男人的黑頭發里有幾根白發,左眼下角有一粒痣。
男人說,“有對夫妻。結婚數年。妻子很快便厭倦了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有了外遇。外遇是對婚姻的有益補充。幾個世紀前的意大利貴族還把妻子有權擁有其他男人作為條款寫在婚約中。要保持婚姻這種形式,又要解決婚姻中的乏味與不和諧,包括性冷淡,外遇是最科學的,是最經濟的。”
女人說,“你想說什么?”
男人說,“丈夫沒有抱怨妻子的外遇。只是請求妻子不要離開。妻子告訴他,除非今天晚上老天下雨。那是星光燦爛的晚上。丈夫聽了后,端著臉盆爬到屋脊上,往妻子的窗前澆水,澆了整整一晚。妻子在天亮后發現后,就沒有再走。”
女人說,“很惡心的《知音》體。那妻子以后還給不給丈夫戴綠帽子?”
男人說,“我不知道,這得問女人。其實婚姻的起源即是對財產的保護,是把女人視作一種可供交換的財產。女人不過是父母待價而沽的商品。若發現某個女人有婚前性行為,這意味著財產的損壞,男人有權向女方家庭索回聘禮或是要求賠償又或干脆把女人休回家,而女人則遭到來自于父母兄弟姐妹的羞辱,認為壞了門風,得投河自盡。為保護財產不被損壞,男人發明了貞操帶、守宮砂。”
女人說,“書讀成你這樣,也可以投河自盡了。‘婚’是什么?把這字拆開。就是一個女人昏了頭。為什么會昏頭?最早男人是用棍棒敲暈的,現在是拿甜言蜜語與閃光的珠寶弄昏的。”
男人說,“女性已淪為商品。這并非只體現在她們的子宮、家務勞動、社會工作皆可通過具體的價格進行描述,而在于她們已經成為整個消費社會饕餮欲望的最重要的符號。對女性的狩獵成為社會的驅動力,而獲取的質量與數量,則定義著一個男人的成功。這是一種可怕的卻已然普遍的價值觀。更可悲的是:大多數女性接受了它。她們的自我認識,基本就是對男性思維的復制。她們在心甘情愿成為男人所豢養的小狗小貓。”
女人說,“你到底想說什么?”
男人說,“有大多數,就有一小撮。所以說我理解《尋歡作樂》里的那個羅西,理解她天真的無恥——因為喜歡,隨意與他人交歡;在極度絕望的時候,投入陌生人的懷抱;一夜狂歡后,又若無其事地回到生活的軌道上。她是蕩婦,但燦若星辰。你看過這本書么?毛姆寫的。羅西有金色的頭發,淡黃色的皮膚。她拋棄了功成名就的丈夫,與一個破產了的男人私奔。當所有人都認定她晚景凄慘時,她還幸福地活著,生機勃勃。”
女人說,“我不喜歡毛姆。沒看過他任何一部作品。也不想看。你說,人為什么要結婚?”
男人說,“社會的角度,家庭是社會的細胞。人,作為社會人,必須建立家庭。不結婚的人被視作病態。社會的壓力迫使人們接受婚姻;經濟的角度,買一張床要比買兩張床劃算。兩個鋪蓋搬在一起,能降低生存成本;性的角度。性在婚姻中的價格趨于零,是最便宜的。雙方事先為其支出各種成本,比如隱私空間被侵犯等;生物的角度,婚姻提供了繁衍的合法性,保證基因傳遞……”
女人說,“你是傻逼中的戰斗機。”
5
你笑了。他也笑了。你又重復了一遍剛才的問題,“為什么?”
“因為你是我的咽喉。因為你,我才可能品咂書上所有的詞語,用我的舌頭,我的五臟。或者說,你是我的咽喉炎,使我咳嗽、低熱、眩暈,坐立不安,全身不適。而正因為這些癥狀,我才知道我還活著,這個糟糕的世界也從未有一刻遺忘了我。”
你把目光投向窗外的馬路,“你知道的,我問的不是這個。”
“那天晚上,她睡著了,我也睡著了。我在夢里遇到她。我們交媾完后一言不發各自離去。我以為我會再也想不到她,像水忘掉了水,就算在路上偶遇,只會禮貌地抱以一笑。這樣過了三十年,我老了,庸俗了,膽怯了,圓滑了,牙齒松動,看什么東西都模糊不清,只依稀記得從小寒起,太陽黃經每增加30°為另一個節氣。我以為我會安然地死去,但有一天,一個二十歲的女孩找到我,說她愛我,愛我滿臉的皺紋、癟掉的嘴唇,不再光潔的額頭,已經松馳的皮膚。她還給我背杜拉斯的《情人》的開頭,與葉芝的詩篇,說時間,這個暴戾而又偉大的君主,就藏在我這張備受摧殘的面孔上。
“你不要笑。她說的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個年輕而又漂亮的姑娘來到我面前說愛我。我接受了她的愛情,與她舉行了盛大的婚禮。洞房夜,當賓客們都走了,她侍侯我躺下,開始脫衣服。脫得很慢,一件一件。過了很久,好像有一個世紀那樣漫長,她白晰的胴體就猶如閃電。我覺得要腦溢血了,想叫她拿瓶藥端杯水來,可我的眼珠子動不了。她還在脫,脫的是皮,像周迅在《畫皮》里脫掉那件從美國運來的仿真人皮。她把皮扔在椅子上,問我是否害怕。我已經說不出話。那張在電影中只出現了6秒鐘的仿真人皮,據說花費了一百多萬元,真的夠貴了。
“我仔細地回想,問她為什么要這樣。我又不是英俊瀟灑家財萬貫的王生,不值得花上這么多錢。她問我是否還記得她是誰。我就想起來了。她老了,雖然談不上老態龍鐘,也花白了頭發。她身上有一種異乎尋常的優雅。這讓我想起了法國作家芭貝里筆下孀居多年的門房老太太荷尼。這么老了,還扮文藝女青年羞也不羞。我很想提醒她把《情人》看完。杜拉斯在書里毫不諱言,她所熱愛的只是中國情人帶來的性與現金。但我最后說出口的卻是‘我愛你’。我不知道我為什么要這樣說,可我就這樣說了。
“男人說謊,就好像他們在女人體內射精;女人說謊,卻是男人高潮的春藥。我老了,所以我知道我沒有說謊,也知道了她的誠懇。她是愛我的,就那樣口齒不清地愛著。她說她一直忘不掉我,就在花甲那年去韓國做了一個全身的美容手術,回到自己二十歲的模樣。她說,若是我愿意,她可以再穿上那件人皮衣裳,再不脫下。
“她真傻。既然知道了是她,我還會在意是二十歲的她,或者六十歲的她么?所以夢醒之后,我立刻向她求婚,她答應了。”
6
我要你看著我,看著
我的雙眸、雙唇、雙手
看著上面曾屬于你的
體態、體液、體溫
我將用一生來收集你所有目光的重量
并置于天平一端。當它們
達到某個數值,我體內60萬億個細胞
將只為記錄你的一切而存在
你以為你是你,不是的。你并非自我選擇的結果,而是一個不明確的手勢,一張陰郁的臉龐,乃至某個早晨一場突如其來的雨水所給出的。這并非是你的錯。沒有多少人能獲得自我意志的蘇醒,繼而越過事件森林,擺脫詞語的眩暈,抵達傾頹荒蕪的神殿,在被青苔覆蓋的石柱上找到那行幾乎已不能辨認的神喻。
你揉碎紙團,拋入廢紙簍,摸起擱在旁邊的公文包,結賬,出餐廳,下樓。這個世界是搖晃的大海。灰房子,紅房子,黑房子,白房子。白房子,黑房子,紅房子,灰房子……它們是在海面上航行的船。而你是你自己的船。你沒開車,走得不快也不慢,借助于用條形引導磚與帶有圓點的提示磚鋪成的盲道,你閉上眼睛,在腦海深處仔細地搜索,過人民中路,在第一個紅綠燈處左拐至馬鞍街,前行五十米,約七十五步,進入福田花園的側門——盲道消失了,你貼著墻壁,緩步右行,好像是十米,好像是十五米,你還是找到樓梯入口處的鐵門。你的眉頭舒展開來,一步一個臺階,上了二樓。你睜開眼,輕吁出一口氣,在掏鑰匙的一刻,你遲疑了一下,伸手敲門。
門開了。是她,系著圍裙,手上還帶著膠皮手套,光潔的額頭上有細小的微汗。她在忙碌。在忙碌什么呢?你飛快地朝四周瞟了一眼,打開公文包,掏出一張影碟,“我剛去買了這張《桃色交易》。恩,今天是我們結婚三周年紀念日。”你注意到她眼中的欣喜與失望。你從褲兜里摸出一個盒子,是幾天前在周大福買的,鉆石墜子,有一克拉重。你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把它送給另外一個女人。現在,你把它扔給了她,“還有這個。”
責任編輯:宋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