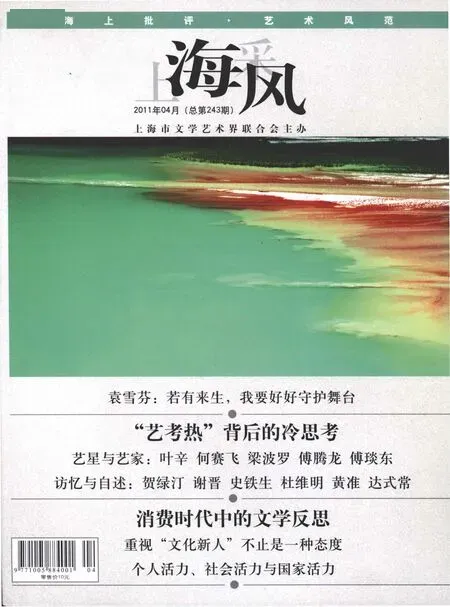表演事業是我一生的鐘愛
文/達式常
表演事業是我一生的鐘愛
文/達式常

表演事業是我一生所從事的事業,也是我畢生鐘愛的事業。演員就是這點好,年輕時可以演年輕的角色,現在老了還可以演年老的角色,只要你演得動,只要有人請你演,你就可以一直演下去。這里回顧的是我曾經扮演的角色。
岳明華:剛毅而粗曠的軍人形象
《曙光》是先有話劇,后來被改編成電影的。我扮演的是紅軍獨立師師長岳明華,他是當時賀龍手下最得力的一員干將。這是我演員生涯中塑造的第二個軍人形象,前面一個就是《難忘的戰斗》中購糧工作隊隊長田文中。雖然田文中是以文戲為主,但他畢竟是個騎兵團副團長出身的軍人,軍人就一定要有軍人的氣質。之前身邊也有人對我塑造軍人形象抱懷疑的態度,這方面孫道臨老師給了我很大的鼓勵;道臨老師平時給人的感覺也是文質彬彬的,但他在《渡江偵察記》中成功地扮演了李連長,他認為我也能像他那樣演好一個軍人。應該是我第一個軍人形象最終還是得到了業內認可,才又有了《曙光》中岳明華這個角色。而岳明華是屬于那種受壓制、受迫害的軍人,紅軍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影響,他被誣陷為國民黨的改組派,看到自己最親密的戰友馮大堅被殺害,他很不理解很痛苦,因此他要為真理而抗爭,為自己的命運而抗爭。他的情緒表現更為激烈,他的形象也更粗曠。
我印象深刻的有這樣一場戲,潛伏在黨代表身旁的內奸藍劍,帶著警衛隊馬上要把岳明華押赴刑場,這一瞬間我要跟難友們告別。怎么演這場戲呢,不能簡單地處理成站著發表演說,這是絕對不真實的,一個將要被押赴刑場的人怎么還可能讓你在那兒慷慨陳詞呢?所以你必須在一種激烈抗爭的狀態下把這段話說完,這是非常核心的一段臺詞。當時我就跟沈浮導演建議,讓藍劍身邊的兩個打手將我押赴刑場,我要跟難友說話,他們就上來阻止我,因此就是在這么一種撕扯當中,跟難友們告的別,這樣才真實啊!
為什么岳明華這場戲我印象特別深呢?因為這段臺詞比較長,我在演這場戲的時候,沈浮導演就說:“小達子啊,你當中要停一停,往柱子上靠一靠,然后再說第二段。”岳明華是在負傷的情況下被捕的,這個時候他的傷還沒好,因此在這段和打手的抗爭中他還是很痛苦的。我覺得沈浮導演提醒得很有道理,而這段話有了一個喘息之后再往上走不是能表達得更好嗎?我們在山區的老房子臨時搭了監獄,監獄外面的走廊盡頭有幾根柱子,我第一段話說完之后他們就拼命來拽我,我把兩個臂膀一甩,他們都倒在地上,我自己也站不穩,踉蹌地靠在了柱子上,然后我就喘氣,傷口疼痛。喘息之后我馬上利用這一瞬間再次沖向鏡頭說了第二段話。拍攝的時候攝影師也來勁了,從正面跟拍,這場戲最后還是完成得比較出色的。
現在想來,還是覺得沈浮導演非常了不起,他就這么輕輕地一點撥,角色本身有傷,通過這樣的喘息還原了他的真實性。臺詞的節奏也控制好了,讓這場戲顯得更生動更富有激情!
《曙光》這部影片拍攝的時候還是很艱苦的,因為是在浙江四明山的山區里拍攝,住宿條件比較差。山上原本就沒有能力接待我們攝制組幾十號人,只好讓我們住在茶葉倉庫里,又陰冷又潮濕,連床單被褥都要我們自己帶。床也沒有,用山里的竹子現編竹床,那么多人睡在一起,竹床一動就嘎吱嘎吱地響,根本休息不好。
《曙光》在八十年代初期還是一部挺重要的影片,即使現在回頭去看,還是有它深遠的意義。它寫的是紅軍年代,當時中國共產黨內部受左傾機會主義的影響很深,給我們黨造成巨大的損失,也是血的教訓。1976年“文革”結束,1979年就出了這個片子,我認為這里包含了作者白樺對“文革”的一種深刻的思考和認識。
傅家杰:細膩而感人的知識分子
《人到中年》就是寫知識分子命運的,當時選我可能是覺得我有書生氣吧,這部電影最早確定的角色就是我扮演的陸文婷丈夫傅家杰。
非常有意思,還沒有人邀請我拍這部電影之前,我已經看過了諶容寫的小說,當時就很感動。記得有一次坐在車上不知怎么就跟我們上影廠當時分管劇本的副廠長聊起這篇小說,我說這篇小說根本就不用再寫分鏡頭稿,按小說情節直接就可以拍電影。那時候還有別的戲邀請我拍攝,我征求過周圍其他老藝術家的意見,他們都一致認為,肯定是接《人到中年》。可見這電影還沒開拍就有很多人看好它。《人到中年》有它一定的現實意義,它畢竟反映了中國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
我扮演的傅家杰是搞科研的,搞科研的人經常要到實驗場地去啊。搞汽車工業的就要去車間,要了解你研究的金屬材料在工作中會出現什么樣的狀況等等,這些你都要熟悉,你也要經常和工人們打交道。所以他跟醫生還不太一樣,醫生主要就是在醫院,而傅家杰他是搞金屬力學的,所以他總是在工地、工廠、車間等這些地方出現。這部電影是在長春拍的,我在拍攝前先去長春一汽體驗生活,其實那些工程師,你接觸一下就知道了,他們興趣愛好很廣泛,畫畫、音樂、打球,他們在家里還是做家務的一把好手,北方的冬天要儲存大白菜,他們都是在家里自己動手挖窖。
《人到中年》講述的是“文革”后中國知識分子的現狀,那時候的知識分子真的很可憐。我是深有同感,當時我的生活狀態跟陸文婷、傅家杰也差不多,他們還有一個11平方米的房子,我剛結婚的時候房子比他們還小。生活雖然清貧,但他們又是精神生活的富有者。傅家杰會朗誦詩,這不足為奇,我身邊就有這樣的人,我有個親戚是工程師,但他的古詩詞功底非常好,還會吹口哨,非常動聽悅耳。說實話,《人到中年》是以陸文婷為主的,傅家杰只是綠葉。如果是以傅家杰為主線的話,相信同樣能拍出一部令人感動的影片來。

《曙光》劇照

《人到中年》劇照
形象的塑造當然是導演、化裝師和演員共同完成的。但是,首先你自己要非常細致深入地去推敲這個角色,你要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說我一開始就提出要理個小平頭,我還要求穿工裝,為什么要穿工裝呢?工裝是工人穿的,但因為你這個知識分子是要跟工人一起干活的。穿工裝還有什么好處呢?你在家做家務、做什么都很方便,穿工裝還很有那個年代的味道。我身邊就有不少知識分子平時也經常穿工裝。在這些細節的處理上我要感謝導演,演員你再有想法,你為這個人物設定好一些細節之后,那還得看導演是接受還是不接受呢!有這么一場戲,陸文婷覺得丈夫太苦了,連寫東西、搞設計的時間都沒有,所以就讓他一定要搬到宿舍去住。我設想的是坐在床上一邊洗腳一邊說,說著說著就開始脫衣服準備睡覺。我已經不按常規出牌了,一般人總是汗衫外面套襯衫再是毛衣,可是我在戲里要是先脫毛衣再脫襯衫,時間不允許不說,那時經濟那么困難,也不可能這么講究啊!所以毛衣一脫就是件汗衫,還是件滿是洞的破汗衫。導演還給了那件汗衫一個特寫鏡頭,這就說明導演接受了我的想法。當時這部電影放映之后,有不少婦女就跟我說,他們的丈夫在家里就是這個樣子的。
再比如說,我非常注意夫妻關系在細節上的處理。傅家杰知道老婆身體不好,總是懸空坐,坐久了腰會吃不消。我就把棉被塞到她背后,讓她有個依靠,可以減輕腰部受力,這樣一個細微的動作也體現了傅家杰對妻子的愛。但這樣的細節不能胡亂用,它必須符合這個人物的特點,符合規定的人物關系,符合這場戲的規定情景。我的設計都來自于生活,因為它來自于生活,所以它是有生命的,不是你簡單虛構捏造出來的。這樣的表演才是最真實的,才能真正打動人們的情感世界。
影片中,傅家杰朗誦了裴多菲的抒情詩《我愿意是急流》。影片上映后,有不少年輕人給我寫信要這首詩,說是要作為婚禮上的禮物朗誦給新娘聽。影片中,這首詩先后被朗讀過兩次,情景是完全不一樣的。第一次是兩個人還處于甜蜜的戀愛中,傅家杰深情而又舒緩地表達了他對陸文婷的愛情,那是一種美的意境。第二次是陸文婷生命垂危、處于彌留之際,他要用這首詩來喚醒她,用這首詩來鼓勵她、激勵她要頑強地活下去。但其實這一次傅家杰在讀這首詩的時候,他自己是非常心痛,非常難過的。所以,我對先后兩次朗讀在語言上的處理是完全不同的。我們說表演要生活化,首先語言要生活化,但語言生活化并不等于語言就沒有一點美感,沒有藝術魅力。你在表達的時候還是要有一種不同的味道,這對演員來講是對藝術修養的一種追求,也是語言功力的體現。好的朗誦作品,足以達到震撼人心的作用!

《譚嗣同》劇照
譚嗣同:悲壯而有氣節的君子
當時長影廠傳來消息說要我去演譚嗣同這個角色,我就問了一句話:“是去試鏡頭還是決定讓我演了?”對方回答說:“就是你了,沒有試鏡頭,沒有第二個人,導演就認準你了!”
我多少讀過些歷史書,譚嗣同當然略知一二,史稱“戊戌六君子”之一,確實是一位令人敬佩得五體投地的歷史人物。然后一看劇本,寫得也挺震撼的,所以我就毫不猶豫地決定去演,何況人家還那么信任你。這部影片的導演是陳家林,他當時還不是很有名,但已經初露才華。所以長影破例把這么一部重大歷史題材的影片交給這位年輕導演,他也非常認真。他跟我開玩笑說:“老達,你要賣點力氣啊!”我當然會傾盡自己所能地去演,否則不是對不起長影對我的信任嗎?最主要的是譚嗣同確實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值得讓我為這個角色百分百地投入和付出。
要演好這個人物,首先要去理解他、感受他的思想,尤其是他最后選擇“取義成仁”的做法。其實他是有機會可以逃脫的,梁啟超帶著日本領事館的人勸他趕緊走,他不走;他的夫人在他被捕前到北京勸他,他還是不走。他有這樣一段臺詞,大意是:各國的變法都有人流血犧牲,但是中國至今還沒有,所以他要帶頭第一個來為變法作出犧牲。活著是艱難的,由你來,死是容易的,由我來!你看他倒過來說。他就要用他的一腔熱血來驚醒黎民百姓,這就是為什么譚嗣同要選擇死。
譚嗣同不像一般的知識分子唯唯諾諾,他是活得有意境的。這樣的一位人物讓我來演的確有一定的難度,譚嗣同畢竟是一位100多年前清朝末期的歷史人物,所以很多戲的表演處理你要花費更多的心思,尤其是他的語言。這部戲人物的語言帶有不少古漢語的特點,你得讓人家聽清楚聽明白,還得聽著悅耳啊,能傳達你的意思,甚至能傳達一定的意境,這都是需要琢磨的。
比如說他第一次進宮,既要跟皇上說出他的想法但又要掌握一定的分寸,他勸說皇上:“朝綱……”停頓了好一會兒才說“……獨斷”。看皇上沒有太大的反感,便繼續說“獨斷朝綱”。這種語言節奏的把握體現了人物內心的情緒,也使語言有了一定的韻味。
但他在辯論場合的語言表達卻又是意氣風發,那也是全劇的一場重頭戲,譚嗣同和保守派之間的一場辯論,針鋒相對。那些演保守派的老爺子都很厲害,有北京人藝的鄭榮老師、牛星利老師,還有八一廠的劉江、長影的浦克等等,他們的語言功力都很好。這么重要的一場戲你的語言要是站不住,這個人物形象就會大打折扣。他不同于在前線打仗的人,他是用他犀利的思想、鋒利的語言來達到一種戰斗的效果。譚嗣同對變法維新滿腔熱情、激情似火,他的話也很在理:“變則通,通才能久遠。”這種時候的語言一定要有力度,有煽動性,這個人物就站住腳了。人物的語言表達往往也是需要設計的。
拍這部影片我年紀已經不小了,還要舞劍。一開始我學的是短劍,后來另外一個教練說短劍不好看,還是要舞長劍。要是再年輕一點,我可以舞得更漂亮,當時只能算基本能對付吧。當然有些動作也需要有一定的力度表現,比如說有一場戲,大刀王五來找他,要接他去天津,他卻拔出劍要王五帶人一起去救皇上。王五說:你這不是把脖子送到刀架上去嗎?這怎么行呢?他也知道不行,氣啊!本來是要把劍插回去的,我跟導演說,讓我劈一劍吧,一劍就把旁邊一個花瓶劈得粉碎,我覺得這樣演更容易表現他的激憤。導演同意了,王五一說完,我就“啪”一下劈向花瓶,一個特寫,花瓶碎了,然后我再把劍收起來交給了王五。
譚嗣同在被捕之前,已經開始做好為變法而獻身的準備了。怎么表現這場戲呢?我心神寧靜,一襲白衫,盤腿而坐,仔細閱讀。等到別人來叫我的時候,我還閉著眼睛,異常平靜。然后睜開眼睛,你說這個時候的眼神是不是不一樣啦,人物所表現出來的思緒和狀態已經處于一種更高的意境了,已經看得非常遠,想得非常深了,已經對最后的結果無所求了,如同他最后在刑場砍頭前說的那樣:“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這部影片中還有一個很好的小細節,就是在譚嗣同被砍頭之前,有一只小昆蟲落在了他的斷頭臺上,他不愿意讓鮮血玷污了它,就輕輕地把這只小昆蟲吹掉,然后抬頭看了看他熱愛的國家,看了看藍天白云,才將自己的頭顱放了上去。這個細節給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這個細節也是我給導演建議的,導演接納了,而且導演還精心設計了一組鏡頭,給了昆蟲一個特寫。其實譚嗣同是非常熱愛生活,熱愛生命的一個人,但是為了這個世界更加美好,不要這么腐敗墮落下去,他可以付出他的生命。細節是電影中非常好的表現手法,如果能找到一個好的細節表演絕對能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因為它是立體的,形象的,它是富有生命的,它會引起人們無限的聯想,最后它也會深深地鐫刻在每個人的心中。可能這部電影很多情節人們已經忘了,但這個細節不會忘。很多人看到我講起《譚嗣同》,就會說起這個小昆蟲,就像講起《人到中年》,就會講到那件破汗衫一樣,它的作用遠遠超過了語言的表達。
從改革者到乾隆皇帝
如果說譚嗣同是一個歷史的改革者,那么《T省的八四、八五年》中的廠長程戈就是當代的改革者形象。這是一部帶點國外紀錄片風格的電影,它曾經獲得過剪輯獎,我也因此獲得了“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獎”。記得當時去領獎的時候,我穿的衣服就是這部影片拍攝時穿的一件牛仔服。這個電影最主要的核心情節就是權與法的抗衡。1978年以后,我們國家已經進入到改革開放階段了,改革的深層次問題是體制改革的問題。說到底,這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實行真正的民主,法制是否健全的問題,而《T省的八四、八五年》正是對這樣一個話題深層次的探討。盡管改革開放的態勢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逐步接受的過程,觀念的改變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這部電影反映的意識形態在當時已經很超前了。

《T省的八四、八五年》劇照
這部影片在整體語言上的處理,當時的上海電影局局長張駿祥是非常滿意的。影片中有一場在法庭上打官司、辯論的戲,一般人都會在法庭上慷慨陳詞,聲音高亢。但是我的理解恰恰是有理不在聲高,況且在戲中我是跟黨委打官司,我和他們之間并不是階級敵人的關系,大家還是同事,是平等的,只是在某個問題的看法上不一致而已,相當于黨內民主會議。盡管在法庭上應該是很嚴肅的,但我對法庭陳述在語言上的處理是聲音低沉有力,語氣有理有力有節。導演一開始覺得我這樣的聲調處理是不是會使人物顯得太弱,但我說絕對不會,你要相信我。后來導演也接受了我的這種處理方式。因為這樣的陳述更有力,更符合雙方人物的關系。
1985年和1986年,我應邀拍攝了《江南書劍情》和《戈壁恩仇錄》,扮演乾隆皇帝。這兩部電影幾乎所有重要的部門——導演、攝影、武術指導,全是香港人。導演許鞍華,武術指導程小東,這在當年都已經是很出名的了,投資方是天津,但香港方面還是組織了一個很好的攝制班底。許鞍華就是因為看了《譚嗣同》之后,認定了要我演乾隆。影片在拍攝前我已經看過劇本,覺得劇本不錯。這兩部電影雖然是武俠片,武打動作比較多,但是也有不少刻畫人物的情節。再說皇上一般是不用動手的,皇上有千軍萬馬,他只要吩咐別人去做就行了。所以我不需要去打斗,我還是演我的文藝戲。當然要刻畫好乾隆皇帝這個人物也不容易,皇上自有他的威嚴,絕對不能允許你紅花會反清復明,肯定是要鎮壓的。但乾隆皇帝對紅花會,對他的兄弟陳家洛又存有一份感情。所以他們說我演得還是有點陰險,可能就是指乾隆這種矛盾的心里表現。
我覺得跟導演許鞍華和劇組其他香港工作人員之間的溝通還不錯,不過他們也有些工作方法我覺得不是特別科學。比如說武打場景的設計拍攝,他們不是根據人物情節的需要事先編好套路,而是一定要到拍攝現場再編動作,這樣的話,其他所有的演員都得在現場等著。其實拍攝場景和環境都是之前看好的,看過場景你就完全可以先編排好動作,到了現場只要根據實際情況和角色表演的需要做些微調就可以了,這樣做不是能節約很多時間嗎?我提過建議,但是他們不接受,也許他們已經習慣這樣操作,要改變也比較困難。當然,在劇組我還是堅持我一貫的做法,我談我的想法,導演能接受就接受,認為不行就不行。畢竟你是導演,我只是盡心盡力地去演好這個人物,把我對角色的認識與導演溝通就行。那時我也不年輕了,我很尊重他們,他們也很尊重我。
我覺得這輩子運氣還算不錯,能夠在人生最好的階段接到像《人到中年》《譚嗣同》等這樣的好戲,好角色。還能跟我的一些前輩,以及一些有才華的年輕導演合作,又能碰到好的劇本和優秀的主創班子,當然也加上我自己的勤奮和努力。后來《中國電影時報》和《文匯報》兩家報社聯合舉辦過一次評1980—1990十年間的最佳男演員和最佳女演員,各評三名,非常榮幸我是其中之一,這說明我的表演、我的創作還是被觀眾所喜愛和認可的。 (趙青整理)
達式常
籍貫江蘇南京,生于上海。1962年畢業于上海電影專科學校表演系,同年任上海電影制片廠演員。
主要電影作品有:《兄妹探寶》(1963)、《年青的一代》(1965)、《難忘的戰斗》(1976)、《萬里征途》(1977)、《曙光》(1979)、《燕歸來》(1980,獲第4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男演員獎)、《人到中年》(1982)、《譚嗣同》(1984)、《T省的八四、八五年》(1986)、《江南書劍情》(1987)、《戈壁恩仇記》(1987)、《站直啰,別趴下》(1992)、《畫魂》(1994)等近30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