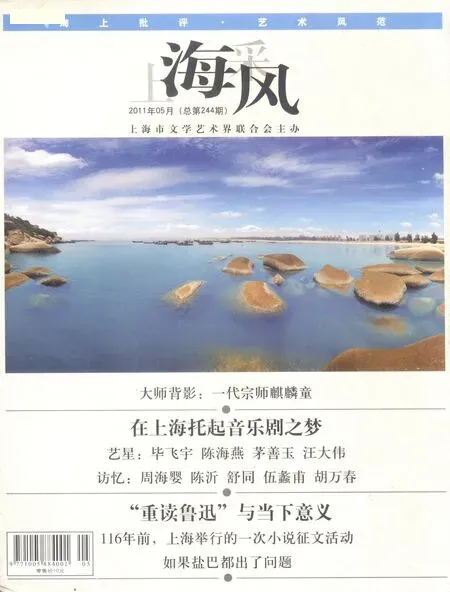畢飛宇:我最大的才華就是耐心
文/本刊記者 劉莉娜
畢飛宇:我最大的才華就是耐心
文/本刊記者 劉莉娜

早春三月,南京的早晚雖然依舊春寒料峭,中午時分卻是暖意融融的,日漸淳厚起來的陽光鋪撒在雞鳴寺下盛放的早櫻花瓣上,玄武湖畔的楊柳樹也抽出凝汁般的綠芽,春色讓這座城市里的人都忍不住慢下腳步來。可是三月的畢飛宇卻很忙,剛剛飛去參加完熱鬧的北京書蟲國際文學節,他便迅即飛往香港出席英仕曼亞洲文學獎頒獎典禮。他2001年出版的小說《玉米》被中國文學翻譯家葛浩文翻譯成英譯本《Three Sisters》(《三姐妹》),去年8月份由哈考特出版集團出版,就憑借這本書,畢飛宇和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日本作家小川洋子、印度作家曼努·約瑟夫和塔畢什·卡爾一同進入了第四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的決選名單。
英仕曼亞洲文學獎(Man Asian Literary Prize)創立于2007年,與英國“布克獎”一樣受到英仕曼集團資助。早期獎項頒發給未以英語出版過的亞洲小說,2010年以后改為頒給當年度首次以英文發表的亞洲小說。它的第一屆獲獎作品是姜戎的《狼圖騰》,第二屆獲獎作品是菲律賓作家米格爾·西喬科的《幻覺》,第三屆獲獎作品是蘇童的《河岸》,英譯為《救贖船》(The Boat to Redemption) ,也就是說,畢飛宇是英仕曼亞洲文學獎4年歷史中獲獎的第三位中國作家,也難怪畢飛宇一開始對自己獲獎并沒有抱任何期望。“這個獎頒了三次,已經有兩屆給中國作家了,另外這次還有大江健三郎在,一個正常的判斷就是我肯定不會得獎的。”畢飛宇說,“我之所以過去,主要是特別渴望和大江健三郎見一面。”然而當晚的頒獎晚宴,兩位入圍的日本作家也許是因為地震的原因都未能前來,畢飛宇并沒有如愿見到大江健三郎,但是,主持人報出的獲獎者名字卻是他。因此,有香港媒體報道稱畢飛宇“擊敗了諾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對此畢飛宇表示很不認同:“我很反對這種說法,我非常尊重他。”而對于為什么最終是畢飛宇獲獎,該獎的評委主席大衛·帕克說:“這個獎項并非獎勵終身成就,而只是為了一本小說。畢飛宇這本書英文名是《三姐妹》,我覺得他在書中對人性認識的嚴肅程度讓我聯想到一位嚴肅的俄羅斯作家——同樣創作了戲劇《三姐妹》的契訶夫。”
據悉,用一本已出版的小說帶走3萬美元獎金,這在英仕曼亞洲文學獎還是頭一遭,因為之前的三年獎金都還是1萬美元而已。記者笑問獎金何去何從時,畢飛宇大笑表示:“獎金都給老婆了,我是好丈夫!”不過,獎金雖是笑談,但“在金錢面前不動搖”,畢飛宇說,他真的可以做到——直到現在畢飛宇都有一個習慣,不管條件多么誘人,他絕對不為合同而寫作。比如這次得獎的《玉米》就可以說是這樣一本拒絕金錢誘惑寫出來的作品,因為當年為了寫《玉米》,他謝絕了20集、5萬一集的《青衣》電視劇的編劇邀請,為此夫人一個晚上沒和他說話。《玉米》出版之后,畢飛宇把書拿在手上,給夫人看,對她說,《玉米》這本書不是100萬可以衡量的。“所以,即便現在獲獎后回頭看,《玉米》也是我比較滿意的作品。”畢飛宇說。
過去的一年來,中國的長篇文學創作處于比較低迷的狀態,因此畢飛宇的這次獲獎也讓中國文壇有了揚眉吐氣之感。對此畢飛宇呼吁說:“我們對中國文壇要有耐心,畢竟每年都有好作品出現的概率太低了,幾乎不可能。”他拿自己舉例說,自己在這20年里一共寫了3部長篇,10多個中篇,不到50個短篇。“20年間只寫了這么些作品,讀者和評論界都覺得少了點,特別是如果我兩三年沒寫一部作品,人們就會不斷追問,是不是我的創作不行了?靈感枯竭了?”畢飛宇對此有點郁悶:“真是開玩笑!我一直在往前沖,這只有我自己知道。寫了一二十年,我最大的才華就是耐心,我總是將耐心用到最強才寫。”在他眼里,作家的耐心是抵抗浮躁的手段,只有具備耐心,才能才會發揮,判斷才會可靠,感受也才不會變形。比如寫上一本長篇《推拿》,他就耐心用了幾年時間,走遍南京的十幾家盲人按摩中心,與一位位盲人師傅聊天、談心,之后用了十八萬字,去講述這一群盲人推拿師內心深處的黑暗與光明。“盲人的人生有點類似于因特網里頭的人生,在健全人需要的時候,一個點擊,盲人就具體起來了;健全人一關機,盲人就自然而然地走進了虛擬空間。總之,盲人既在,又不在。盲人的人生是似是而非的人生。面對盲人,社會更像一個瞎子,盲人始終在盲區里頭。”畢飛宇說,所以他寫《推拿》,摒棄了傳統習慣中對特殊群體“自上而下的悲憫與同情”,以一個推拿店里一群盲人的生活為中心,去觸摸屬于黑暗世界中的每一個細節。這部小說的敘述非常有特色,以不同的盲人按摩師為題,以很小的切口入手,以每一個或幾個不同的人物特點形成的故事作為小說的章節,把盲人的日常生活作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來書寫,寫出了殘疾人的快樂、憂傷、愛情、欲望、性、野心、狂想、頹唐,打破了我們對殘疾人認知的單一和平面。小說中的每一個故事都無不表現了尊嚴、愛、責任以及欲望在人生中的糾結與暗戰,而這些人生的矛盾與掙扎在黑暗的世界里似乎顯得愈發敏感、清晰與沉默。雖然,這部小說的主角們都是盲人,但是讀完小說的每個人都會捫心自問,畢飛宇僅僅是寫盲人嗎?那種人與人之間的無可奈何的錯位,那種微妙復雜的真實情感是那樣令人感觸乃至震撼。而畢飛宇自己的收獲則是:“通過寫盲人,我最大的欣慰就是知道了自己的局限,我不會為這個痛苦。局限是恒定的,正視自身的局限對我們有幫助,有時候,也許正是我們的局限在挽救我們。”正是因為這樣的細心觀察,靜心感受,耐心書寫,去年,這部《推拿》在中國臺灣高票獲得華語世界深具影響力的“開卷好書獎——中文創作獎”。

《三姐妹》英譯本
問到最近的創作動態,畢飛宇說他正在寫新的長篇。寫的是什么內容?書名想好了沒有?他堅決不愿透露半點。但他透露說,是一部當代現實題材作品,“寫得比較困難,因為我對社會比較茫然,這不僅僅是我一人如此,當下的很多中國人兩個眼睛都不能聚焦。但反過來說,這也是一個機會。因此,我有耐心邊想邊寫。”為了更好地觀察和思考,他還從2009年就開始嘗試一種“轉型”,就是把自己的時間更多地花在“一線”上。他經常在各種工地一呆就是很長時間,他非常喜歡和那些“一線”的工人們聊天,他說,那是直接觸摸現實社會最好的方式。“我曾經說過,我渴望隱姓埋名。因為人們一旦知道你是誰——比如你是記者或者我是作家——真話就少了,人們腦子里的那個過濾器就開始自動啟動了。好在那些工人并不知道我是誰,所以和我什么都聊。這樣的聊天很有意思,比方說,聊得好好的,他突然左看看,右看看,再向后看看,我就知道了,他打算說老板的壞話了。”
作為一個職業作家,畢飛宇已將文學創作視為生命,即便在人們對文學前景并不樂觀的情況下,他還是抱有堅定的信念:“文學可能會邊緣化,但文學不會死。”他認為,文學是人類的本能之一,正如人類永遠熱衷于偷窺心理和饒舌那樣。“作家和長舌婦唯一的區別就在于,長舌婦是對某一個人說話,而作家是對整個社會說話。”
記者:好像你是頒獎現場唯一穿唐裝的,是為了參加頒獎典禮特別定制的么?
畢飛宇:沒有,我去之前完全沒有獲獎的期望,我去參加頒獎原本就是想去和大江健三郎坐著聊聊天以及向他表示祝賀的,可惜他沒去。要說還有另一個目的么,也是為了要做給我兒子看,在國內的評獎中他經常看見我體面的上臺領獎,所以這次我原本準備讓他看到,即便爸爸沒有獲獎,也仍然可以像個男人一樣體面地站在那里。
至于唐裝,當然不是定制的。去香港之前他們特別致電我,明確要求了頒獎典禮的服裝:黑色正裝配領結,或者是選擇民族服裝。為此我和夫人特地去商場挑西服,可是相中的那套價值3萬多,我自認為自己是不可能獲獎的,所以想就不要花那個冤枉錢啦。后來忽然想起來夫人曾經在高淳給我和兒子一人買了一套唐裝,只花了150元,平時我和兒子在家經常穿了表演功夫片,效果不錯,所以就穿著那個去了。
記者:聽說評委主席大衛·帕克說你讓他想到契訶夫,而你的獲獎作品《玉米》的英譯本叫《三姐妹》,亦和契訶夫的戲劇《三姐妹》同名,這是個巧合么?
畢飛宇:其實得獎結果出來以后,評委之一,哈佛大學文學教授霍米·巴巴也問了我相同的問題——為什么用《三姐妹》做英譯本的書名,和“玉米”有什么關聯。我告訴他,其實我小說的原名和契訶夫作品無關,在漢語里,“玉”和“米”這兩個字搭配在一起,正好可以作為一個不錯的女孩名字。但是到了英文里頭,一個姑娘名字叫“棒頭”是很不像話的;并且《三姐妹》是根據我的單行本《玉米》翻譯的,書里面包括了《玉米》、《玉秀》、《玉秧》三個篇章,所以譯者葛浩文把它翻譯成了《三姐妹》,我覺得挺合適的。——我之前的《青衣》被翻譯成《月亮的歌曲》《月亮女神》什么的,西班牙版的《玉米》居然叫做《王家莊的壓力》……那才叫千奇百怪呢。
記者:英仕曼亞洲文學獎的三部獲獎中國作品好像都與“文革”時代有關,你注意到這點了么?
畢飛宇:可能是巧合吧。但我個人覺得“文革”是不該被遺忘的。我對“文革”最深的記憶是父親的名字,我一直以為父親的名字是“爸爸”,有一天,所有的人都在喊“打倒畢明”,我才知道我的爸爸叫畢明。一個男孩子以這樣的方式知道父親的名字,他在長大后不能不問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