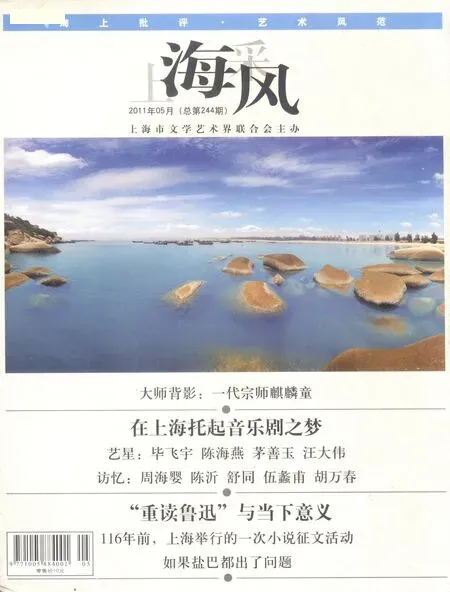汪大偉:美術教育新思路
文/袁龍海 任 律
汪大偉:美術教育新思路
文/袁龍海 任 律

在上海美術教育界,汪大偉是一位繞不過去的人物,他不但是一個優秀的藝術家,還是藝術領域新思路的引領者、拓荒者、實踐者。
藝術“萬里行”
汪大偉從小受到其父親——著名畫家汪觀清的影響,喜愛繪畫。然而中學畢業后命運卻安排他奔赴北大荒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八年艱辛的知青生活,練就了他對生活特有的洞察力,練就了一身堅強的體魄和為藝術百折不饒的性格。“知青難忘的日子我經歷過了,沒料到成為一筆人生財富。”汪大偉說。
汪大偉1978年考入浙江美院,師從李震健、方增先、周昌谷、顧生岳、潘韻等名師,1982年執教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四年后又考入浙江美院成為顧生岳的研究生。1992他以創作《都市奏鳴曲》《蠡族老人》《蝶》等作品知名于世,其藝術樣式既有精湛線條,又有西洋光影運用,風格細膩飄渺、沉郁概括,產生別樣的意境和視覺效果。他以徽州人特有的細膩和有經北大荒粗獷豪爽民風的熏陶,形成獨特個人氣質。這種氣質自然地顯現在他的藝術作品中:靜謐而不失奔放,幽邃而不失飄逸,剛柔相濟,別具一格。
1992年,時任上大美院國畫系主任的汪大偉,在教學與創作的同時也看到了某些不足,便率先推出第一項重大教育改革——“中華五千年文化萬里行教學”,為時三個月,足跡跨越長江、黃河,走入河西走廊、絲綢之路,翻越祁連山。21位師生置身于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大課堂,獲得了全面立體的認識,回滬后在上海、日本舉辦的匯報展引起轟動,《尋夢》系列及大批速寫真實地記錄了他這一時期的心路歷程。
汪大偉對這次“萬里行”記憶猶新,當時得到他北大荒時期老戰友的支持,資助了十萬元經費。那時還沒有百元面鈔,只有十元、五元的面額,出發時隨身攜帶著很有體積感的五萬元現金,由三個老師穿著馬甲背著,一路擔驚受怕。此外,新疆喀什市公共汽車公司的袁經理還為他們提供兩輛面包車行走絲綢之路。“好幾次,眼看著要出事,是老天保佑我們躲過劫難,是老天看我們虔誠啊!”比如,去馬蹄寺的路是斜的,荒無人煙,只能走坑坑洼洼的走馬車的路,上山轉彎時為了保持車的平衡,全部人要靠在一邊,反方向轉彎又必須及時移到另一邊,就這樣進了祁連山脈。由于太投入,大家忘記規定時間趕回,天暗了車子不能開,一行人只能在山溝溝里步行……直到發現光亮看到公路了,大家才長舒一口氣,“想起來還后怕”。“萬里行”之后,汪大偉及其團隊師生,對傳統文化有了更系統深入的了解,繪畫史中彩陶、巖畫、壁畫各階段文脈直接印在腦海中。
這次生命的遠行真可謂“不虛此行”,使汪大偉心里隱伏下根須,互相通氣了,“我受用一輩子”。其中一個謎,汪大偉至今也沒有破解;兵馬俑如此寫實的藝術風格,在他之前與之后的年代中卻沒有藝術上銜接,好像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但是,所有的感受、體悟和思考,正在這一次生動的萬里歷程中,悄然萌生和相互貫通了。
可以說,有了這樣歷練的團隊,為他兩年后全面主持上大美院領導工作,實施一系列新思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數碼藝術之花
自1992年始,汪大偉的主要精力轉入數碼藝術、公共藝術學科創建與探索之中,從此,他把自己的命運和美院的征程分不開了,從前是以紙為媒介進行創作,而今則是將美院看成他自己可以耗盡一生去創作的最宏大的作品,整個美院就是他的創作舞臺。為了美院的未來考慮,順應上海發展,將美術教育與當下社會發展結合,汪大偉從此一發不可收。

《蠡族老人》
事實上,今天的生活已經須臾離不開數字技術、數碼藝術,“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因為它涉及到各個門類,比如軍事仿真、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等。什么都不是,因為它僅僅是技術。就本質而言,計算機只是工具,專業支撐的部分還是傳統藝術,比如效果圖,只是用計算機來繪圖而已。汪大偉指出:“數碼藝術與其他所有藝術類別最大的區別就是‘交互’,令其參與溝通最終成為自己的一部分,它通過人機對話實現交互。”這也是數碼藝術的本質。
上大美院數碼藝術專業,是全國最早開展數碼藝術教育的機構。數碼藝術學科經歷了從計算機輔助設計——多媒體藝術——交互式數碼藝術的過程轉變。

汪大偉在“尋找桃花源”項目中的視頻互動連線
汪大偉不無感慨地說:“我記得計算機美術開始興起時,國家花費了20萬美金從香港轉口貿易引進了一臺SGI工作站,成立了計算機美術研究所。到1992年我們就用它完成了上海地鐵一號線的一個設計項目,當時做出來的效果圖令地鐵方耳目一新。”那時的地鐵效果圖有32兆,可用的移動儲存設備卻是只有1.44兆的三寸盤,怎么辦?他們就把大圖切割,一張盤里裝一兆,到打印前再重新拼接。又把打印公司的新打印機采取優選法調試成功,此舉,直接促成了同打印公司合作開發了多媒體光盤項目,就是后來獲得了上海高等教育教材一等獎的《中國古代美術(CD-ROM光盤)》開發。緊接著在1995年,汪大偉拿著這個光盤到日本進行演示,讓同期正在制作《三國志》的日本同行驚訝不已,回國后,日本方帶來了50萬的投資,與美院合建了多媒體工作室。之后,工作室創辦網絡雜志《藝術大地》時,由于資金短缺,當時是憑借為上海熱線設計頁面,來換取他們50兆的網絡空間來支撐運營,那時上傳還在使用電話線,而且都是手搖式的分機電話,通常一上傳就是一整夜,和幾個學生一起如此艱難地堅持下來。
1999年,美院廣泛招賢納士。其中請到漢字數字化專家顧國安合作,招收電子出版方面的研究生,第一屆是漢字數字化設計研究(即是數碼藝術系的第一屆研究生),美院又派學員到日本東京多媒體研究所學習,學成歸國后自己培養了一批師資。美院成為中國數碼藝術教育探索的先鋒,汪大偉的得意門生金江波,現在已是這一領域的佼佼者。之后數碼藝術專業開設了本科,包含了網絡、視頻、游戲、展覽展示等多種專業課程。
在2002年的上海雙年展上,《尋桃花源記》利用互聯網視頻實時實況將相距500公里遠的安徽西遞、宏村與美術館聯系起來,溝通了鄉村與城市,它將村落搬入美術館,讓上海市民與當地村民進行對話,討論了原始風貌的保存問題,完成了傳統與現代的一次交流與對話。而在2003年由美、英、法、日、挪威、希臘等參與的“九國數碼藝術展”,更是將美院的數碼藝術拉到國際平臺上進行了橫向比較,結果發現上大美院從觀念、表現手法上,絲毫不遜色于任何先進國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0年上海世博會上,觀眾廣泛使用的數字化交互游戲觸摸臺,就是他們最先研發的。“當時微軟是9月14日對外發布,而我們在此之前就通過了展覽會發布,并申請到了該項專利。”可以看到這一技術和微軟幾乎同步,足以證明美院在這一方面的創新技術和思路、方向都是世界級的。
當我們問到團隊的作用時,汪教授連連點頭,并做出有力的手勢:“這要歸功于美院師生的團隊合作,我們的數碼藝術學科研發團隊,是來自數學、機械自動、信息管理、雕塑、設計、史論等科系的學生,學科背景并非純美術,而是加入多層知識結構,才有了這樣一支走向世界的團隊。”
是啊,這就是團隊的力量!高端技術與完美藝術的結合,具有前瞻意義。
公共藝術之果
說起公共藝術,可以追溯到1933年美國政府組建的“公共設施的藝術項目”機構,而我國公共藝術起因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公眾對機場壁畫和城市雕塑的質疑和批評。1998年6月,汪大偉在《裝飾》雜志上發表題為“公共藝術設計學科——21世紀的新興學科”的文章,第一次公開闡釋了公共藝術作為一個學科來建設的概念,同年9月,美院創建了國內最早的公共藝術學科,開我國該領域之先河。公共藝術與上海這個發展著的國際化大都市緊密結合,經歷十幾年建設,已經形成一整套完善的運作機制,覆蓋了繪畫、雕塑、美術學、藝術設計、工藝美術、建筑、藝術管理、會展等8個專業,成為上海大學重點發展的優勢學科之一。
可以這么說,上海都市的發展,為公共藝術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反過來,公共藝術為都市服務的理念,培養造就了藝術家。這個密切的相輔相成的關系,在汪大偉腦海里顯得十分清晰,于是在實踐中,他始終向同事同行“灌輸”這一理念。
世博期間,美院承擔了世博中心的14萬平方米的藝術裝飾工程,其中包括了80多件擺件,60余幅4米以上的布置畫,其中最大一幅長達43米,完全需要手繪原創,而實際制作時間僅僅只有20多天。當任務交到美院的時候,全校老師、研究生、本科生齊出動,每個工作室都徹夜趕制。其中有兩位老師帶著研究生花費了一周,創作了自己的作品,氣勢恢弘張揚,裝裱好放在會議大廳里,結果連作者自己也覺得明顯不合適。汪大偉說,“這樣的繪畫放在美術館里是件作品,但布置在這里卻不協調,公共藝術受到空間功能的制約。”所以,在后來的工作中,他更加注意空間的和諧與平衡。
上海大學美術學院立足上海,依托上海,服務上海,配合上海乃至全國的城市建設與文化建設,參與了多處城市重大工程項目的主創設計,可謂碩果累累。比如:上海城市標志性城雕、《東方綠舟》知識大道歷史名人雕塑群、人民大會堂國宴廳和上海廳裝飾設計、上海南京路下沉式廣場、上海城市規劃館等等。由汪大偉領銜主持設計的項目有:《地鐵1號線黃陂路站壁畫》、上海市住宅博物館(主持設計)、上海盧浦大橋紀念碑、南京市秦淮河景觀設計工程、上海市應急聯動中心形象設計、上海M8線環藝規劃設計、上海世博會主題館(城市文明館)規劃設計、地鐵7號線車站總體設計、2009年世博會博物館總體設計、上海寶山民間藝術博覽館總體設計與實施工程等等。其中,上海地鐵南京路下沉式廣場獲得第十屆全國美展設計金獎。

上海世博會博物館:城市成長


地鐵7號線車站大廳設計
據統計,在上海2010年通車的112個車站中,有66個車站的裝飾整體設計都是由上大美院承擔的,可以說上海地鐵70%的車站壁畫成了展示上大美院公共藝術的一道城市風景線。當記者問起通過參與上海地鐵建設有什么體會時,汪大偉說:“公共藝術,已不僅僅是表現手法,更是一種工作方法,一種運籌的工作機制。”“公共藝術存在于廣大人民群眾活動、休閑、觀賞的場所空間中,因此對人的關懷、對人的尊重、對人的體貼是其設計最基本的出發點。”由此可見,公共藝術要探討的問題,其實已經關系到藝術的社會功能性與民生層面了。
走進當代與繼承傳統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華大地已涌現一批勇于創新與變革的優秀藝術家,有一部分當代藝術家如蔡國強、陳箴、谷文達、艾未未、仇德樹等,已取得了不俗的業績,在國際上獲得西方同行的贊譽。但是,游戲規則、價值標準的話語權在別人手里,中國當代藝術大致上是按著別人的規則和標準下“思考”、“創意”。什么時候,中國的當代藝術能夠由中國和國際同行的共同標準來判別優劣,我們才算擁有了真正屬于自己的當代藝術。
面對這個棘手的問題,汪大偉沒有忘記對當代藝術的思考,作為身處上海的都市美院,如何在國際上引得關注負起責任?對此,美院啟動了兩項國際合作。
利物浦雙年展與威尼斯雙年展、惠特尼雙年展并駕齊驅,在“引領世界藝術走向”上起到坐標作用。美院在2010年與英國約翰·摩爾基金合作“約翰·摩爾當代繪畫獎”,直接參與利物浦雙年展,這項大獎在英國已有50年歷史,在中國是第一屆。國內評選出一件大獎,四件優秀獎,直接參與利物浦雙年展,成為利物浦雙年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同其合作,就是一次中國當代藝術同國際的對話,在尊重國際游戲規則的同時學習別人的管理經驗,逐步建立完善我們自己的當代藝術評價體系,參與國際游戲規則,爭得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此次選定中國的當代藝術家谷文達、曾梵志與英國另三位當代藝術家共同擔當評委,而操作過程則完全參照國際模式,評委們在充分討論和充分溝通下加強了解,“可喜地見到上一屆獲獎作品都具有一定的中國文化元素,大獎是顯現了中國畫寫意精神與油畫材料融合手法創作的作品。”國際游戲規則和我們自己的觀點有機地結合,令國內的當代藝術,成為了指向性很清晰的中國文化展示。
2011年即將啟動“公共藝術獎”,由上大美院牽頭,美國公共藝術基金會、英國公共藝術委員會、上海《公共藝術》雜志、香港當代文化中心四家共同發起。四家機構相繼負責美洲非洲、歐洲、中國大陸、東南亞的組稿。“‘公共藝術獎’是首次嘗試,在國際上也沒有慣例可參考,因此大家共同建立游戲規則。”作為中國藝委會主席的汪大偉信心十足。可以想見,這些國際合作,將帶動我國的當代藝術走向世界,贏得一定的國際地位。
當記者提到新的上大美院如何傳承老美校的文脈時,汪大偉首先向我們提供了一套美院50年校慶時特別制作的書籍共十四本,該套書對美院各專業的發展進行了梳理,包括國、油、版、雕、建筑、數碼藝術、公共藝術實驗中心、史論系、夜大、附中、美院歷史、院慶實記等。
根據文獻資料得知:從1959年“老美專”的第一屆招生開始,經歷了文化局劃分到輕工局,直到文革前后,校址由馬勒別墅、天津路、圣約翰、陜西北路、漕溪北路等一路搬遷。辦學樓卻越搬越小,能延續到今天,靠的是美院精神的“形散神聚”。這50年變遷,有動蕩有波折,但承載的是藝術家們對藝術事業的無限追求和使命感,作為上海的代表,時代發展需要我們在藝術上求新求變;靠的是最早的唐云、張充仁、俞云價、應野平、俞子才、喬木等海派藝術代表人物的傳幫帶;靠的是顧炳鑫、廖烱模、章永浩、韓和平等藝術家的自強不息;靠得是陳家泠、王劼音、凌啟寧、張培礎、王孟奇等教授百折不撓,勇于創新,以及當下全體美院人共同的努力,海派精神“一以貫之”不變,美院的精神得以延續至今。在學院建設上,也始終重視師承、繼承傳統、順應歷史、面對現實,這就是海派精神的形散而神不散。
曾有人說現在美院國畫系變弱了,汪大偉解釋道:“實際上應該說是方向改變,不再以傳統的標準去衡量。上世紀八十年代,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國,上海作為前沿陣地最早受到影響,國畫也轉向走向當代,這里,陳家泠老師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他率先求變求新,到了現在周鐵海、丁乙的新一代則換了新貌。我們看到,即便是吳昌碩、任伯年、黃賓虹、潘天壽等先輩海派大師,當時他們的畫風也是在求新求變中發展的。上海的美術事業求新求變的觀念并沒斷層。美院國畫系正是繼承了努力創新的海派精神。”

汪大偉在2009年50年校慶時提出了“研究型的都市美院”概念:“都市美院是應都市而生,并與都市同呼吸、共命運、相輔相成。都市美院培養的人才應成為都市發展的再生動力”。作為一個把握方向盤的人,他清醒地認識到:在上海這個國際都市,作為上海的美術學院,應該成為都市概念的文化引領者。
如今,上海大學美術學院與中央美院、中國美院遙相呼應,成為具有一級博士點的美術教育機構,成為上海地區唯一一家國家級實驗教學中心——公共藝術技術實驗中心。美院以開放的姿態面向全國、面向國際,博士導師也可以由社會招聘。此外,美院于去年秋天,還成立了“中國書畫研究中心”,由國畫大師陳佩秋先生領銜,將借助上海大學的高新科技設備,如隧道顯微鏡、原子探針等,作輔助鑒定和對比。誠如上海大學一位領導所說:我們都知道X光設備固然好,但誰來讀片診斷呢?顯然陳佩秋先生就是這個讀片人。傳統底蘊加上創作經驗,在這位大師的帶領下,美術史專業的8位教授和十多位博士一起組成一支傳統繪畫研究的基本隊伍,另外借助技術團隊、高新科技設備等力量,最終形成中國書畫研究中心。該中心從繪畫創作研究、繪畫考證研究和研究性數據庫三方面著手建設,將為傳統研究打下非常扎實的根基。一方面打破傳統教育模式,建立以工作室為教學載體、以科研項目細化為課題進行研究和教學的新模式,另一方面則是繼續尋找和傳承藝術之魂。
汪大偉
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執行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上海創意設計工作者協會主席,上海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教育部高等院校藝術設計專業執導委員會委員,上海地鐵建設環境藝術委員會委員,上海藝術博覽會藝術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