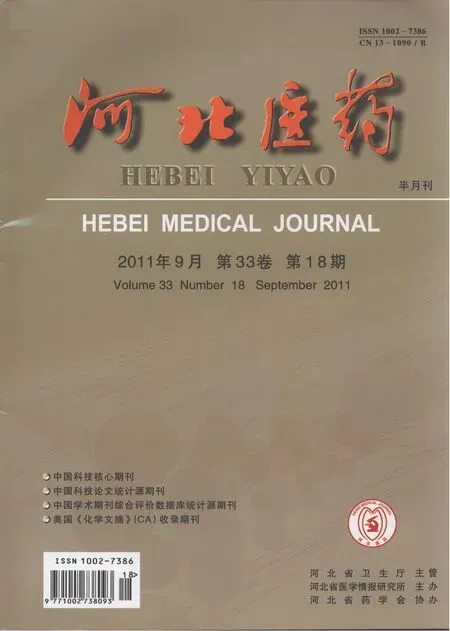血清新喋呤對急性胰腺炎診斷及判斷預后的價值
張麗華 王麗芳 張朋偉 張起鵬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是臨床上常見病和多發病,臨床表現差異極大,輕癥與重癥的治療及預后截然不同。特別是重癥AP患者的病死率在20% ~30%以上[1],而早期預測和正確評估AP的嚴重程度,把握其進展趨勢,在臨床工作中顯得尤為重要。新喋呤是反映體內淋巴細胞-巨噬細胞軸所介導的細胞免疫狀態的重要標志物之一,其臨床意義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有資料證實,炎癥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腫瘤及器官移植患者血清或尿液中新喋呤含量均明顯升高[2]。我們既往的研究發現,AP對循環新喋呤的持續產生有顯著影響,動態觀察新喋呤變化將有助于監測重癥急性胰腺炎的發生、發展過程[3]。本研究通過對68例AP患者血清中新喋呤水平檢測,結合臨床病情變化,以探討其對AP的診斷、嚴重程度及其預后判斷的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收集2006年4月至2008年8月在河北醫科大學第二醫院急診科、消化內科病房住院的AP患者68例,其中男36例,女32例;年齡19~69歲,平均年齡(36±14)歲。發病24 h內入院者49例,24~72 h內入院者19例。AP的診斷標準符合2003年全國胰腺會議確定的急性胰腺炎診療指南[4]。輕癥急性胰腺炎(moderate acute pancreatitis,MAP)37例,重癥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31例,合并有并發癥的SAP患者11例。正常對照組20例,均來自健康體檢者。其中男12例,女8例;平均年齡(34±4)歲。此外,參照Goris等[5]提出的計分方法對SAP并發MODS者進行評分,包括肺臟、心臟、肝臟、腎臟、血液、胃腸道、腦等器官,其中0分表示無功能障礙,1分表示有輕度或中度功能障礙,2分表示嚴重功能障礙,累積計分0~14分。將SAP組31例患者按是否并發MODS分為2組。
1.2 檢測方法 患者分別于入院后第1、3、7和14天抽取空腹外周靜脈血2 ml,而對照組于清晨一次性抽取空腹外周靜脈血2 ml。血液標本離心后收集血清,新喋呤采用德國IBL公司生產的酶聯免疫吸附試驗(ELISA)試劑盒測定,檢測范圍至111 nmol/L,該方法檢測下限為0.7 nmol/L。操作嚴格按照試劑盒說明書進行。同時,監測患者生命體征、血氣、血常規及反映肝、腎、心等器官功能損害的生化指標改變。
1.3統計學分析應用SPSS 11.0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s表示,采用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3組血清新喋呤變化比較 正常對照組血清中新喋呤水平為(6.1±1.8)nmol/L。有49例 AP患者24 h內入院,新喋呤高峰值出現在住院第3天,而剩余19例AP患者發病后24~72 h內入院患者,新喋呤于入院后第1天最高。37例輕癥AP患者新喋呤在入院第7天開始下降,14 d后恢復正常;而31例SAP患者新喋呤下降緩慢。重癥組發病后各時間點血清新喋呤均值高于輕癥組(P<0.05)。入院第1天,無論輕癥組還是重癥組,血清新喋呤水平均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1。

表1 AP患者和健康人血清中新喋呤濃度變化
2.2 SAP合并MODS患者血清新喋呤水平的改變 31例SAP患者按是否并發MODS進行對比分析,可見MODS組發病第1天起血清新喋呤含量持續并顯著升高(P<0.05),而非MODS組升高幅度明顯低于MODS組(P <0.05),入院后第14天趨于正常對照范圍(P >0.05)。見表2。

表2 SAP并發MODS與非MODS患者血清新喋呤水平比較
2.3 新喋呤水平與MODS積分值相關分析 11例SAP并發MODS患者中,出現2、3、4和6個臟器衰竭者分別為4例、4例、2例和1例,平均積分值為(4.5±2.8)分。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入院后第 3天(r=0.823,P <0.01)、第 7天(r=0.547,P <0.05)MODS患者血清新喋呤水平與MODS積分值呈顯著正相關,但其他時相點相關不明顯(P>0.05)。
3 討論
AP是一個多因素、多環節共同作用引起的全身炎性反應綜合征,由于缺乏有效的生物學指標,致使臨床上不能及時、有效地判斷AP的病情發展。雖然臨床上使用血、尿淀粉酶來判斷AP的發作變化,但不能有效地估價疾病的預后發展。近年研究表明,SAP的發生和發展是機體全身炎性反應不斷加劇、持續惡化,與代償性抗炎性反應之間平衡破壞及免疫機能紊亂的結果,這一過程持續發展將最終導致 MODS的發生[5]。MODS是當今ICU首要死亡病因(50% ~80%)。目前的研究認為,早期識別與診斷是防治MODS的關鍵,尋求反映該綜合征病理過程的有效預警指標和監測方法無疑具有重要臨床意義。新喋呤作為一種綜合反映體內細胞免疫和炎性反應程度的新標志物,具有穩定性好、持續時間長、不易失活或降解等優點,它克服了某些炎性介質穩定性差、特異性不強和容易受干擾的缺陷[2,6]。因此,探討AP新喋呤的變化規律及其與致死性并發癥的關系,可能為其病程監測提供新的方法和手段。
本組臨床觀察結果顯示,AP病程第1天新喋呤明顯升高,其高峰值出現在發病后第3天,以后逐漸下降。根據患者病情程度分類可見,輕癥組新喋呤水平呈現一過性上升,其變化幅度及持續時間顯著低于重癥組。上述結果表明,AP可導致循環新喋呤水平明顯升高,且與病情程度存在一定相關性。這與我們前期的觀察及文獻報道基本相符[3]。一般認為,感染或急性損傷后多種因素均可影響機體淋巴細胞-巨噬細胞軸,使之產生γ-干擾素等細胞因子,進而激活單核-巨噬細胞系統,引起新喋呤的持續產生[2]。有人曾比較感染患者中性粒細胞-彈性蛋白酶、C-反應蛋白和新喋呤等指標的變化情況,結果發現以新喋呤的升高更為持久和明顯,且與膿毒癥等并發癥密切相關[7]。值得注意的是,本組資料中重癥組新喋呤升高幅度尤為顯著,這對于輔助評估患者的疾病的嚴重程度可能具有一定臨床價值。
進一步分析可見,SAP并發MODS者血清新喋呤水平發病1~14 d顯著高于非MODS者,其改變與MODS積分值呈正相關關系。這初步說明,循環新喋呤的持續升高與SAP并發MODS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動態觀察其變化可能有助于MODS病理過程及器官損害程度的監測。研究表明,SAP并發MODS發病的本質是全身性炎性反應失控和機體免疫機能紊亂,而體內淋巴細胞-巨噬細胞軸和血管內皮細胞是參與該病理過程的重要系統,因此新喋呤作為綜合反映上述主要免疫炎性細胞群激活程度的穩定標志物可能為MODS的診斷提供新的手段[8,9]。
上述結果均表明了發病早期新喋呤就明顯升高,且升高的幅度與AP的嚴重程度及預后呈正相關,也充分提示了新喋呤可以作為SAP的早期診斷指標。利用新喋呤在AP的診斷中的優勢及其動態測定有助于判斷AP病情嚴重程度、并發癥的發生及其預后,簡單實用,是臨床工作中對AP診治的一個重要指標。
1 Baron T,Morgan DE.Acute necrotizing pancreatitis.N Eng J Med,1999,340:1412-1417.
2 Fuchs D,Weiss G,Reibnegger G,et al.The role of neopterin as a monitor of cellular immune activation in transplantation,inflammatory,infectious,and malignant disease.Crit Rev Clin Lab Sci,1992,29:307-341.
3 張麗華,王麗芳,張朋偉,等.血清新喋呤對急性胰腺炎的診斷及預后判斷的價值.河北醫藥,2010,32:872-873.
4 王興鵬,許國銘,袁耀宗,等.中國急性胰腺炎診治指南(草案).中華消化雜志,2004,24:190-192.
5 Goris RJ,te Boekhorst TP,Nuytinck JK,et al.Multiple organ failure:generalized autodestructive inflammation?Arch Surg,1985,120:1109-1115.
6 吳葉,姚詠明.創傷后新喋呤改變的意義及其機理.國外醫學創傷與外科基本問題分冊,1998,19:7-10.
7 Kellermann W,Frentzel-Beyme R,Welte M,et al.Phospholipase A inacute lung injury after trauma and sepsis:its relation to the inflammatory mediators PMN-elastase,C3a,and neopterin.Klin Wochenschr,1989,67:190-195.
8 姚詠明,陳勁松,于燕,等.新喋呤測定在燒傷后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早期診斷中的意義.中華醫學雜志,2000,80:199-200.
9 Delogu G,Casula MA,Mancini P,et al.Serum neopterin and soluble interleukin-2 receptor for prediction of a shock state in gram-negative sepsis.J Crit Care,1995,10:6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