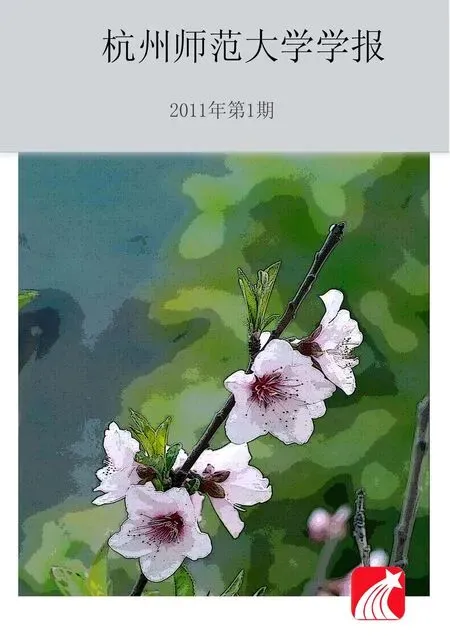用彼之言語,以敘我之性情
——試論賴山陽的漢文
王 標
(日本大阪市立大學,日本 5588585)
海外漢學研究
用彼之言語,以敘我之性情
——試論賴山陽的漢文
王 標
(日本大阪市立大學,日本 5588585)
日本江戶時代后期漢學家賴山陽的《日本外史》曾對明治維新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同時也是一部頗有爭議的史著。除了史實考證以及體裁等史學問題之外,對于賴山陽漢文中的日本化傾向,后世的評價也經歷了一個從否定到肯定的過程。對此,必須回到賴山陽的話語世界,探討它與荻生徂徠的“華音”、本居宣長的“國學”等江戶時代中后期有關漢文的其他話語的關系;并根據《賴山陽文集》中出現的中國文學家人名、漢籍書名及出現次數等資料,揭示賴山陽的知識世界,藉此分析由此構筑起來的漢文創作的文化實踐,即賴山陽的文章論。最后,通過考察賴山陽對同時代清朝文學(尤其是袁枚)的認識,探討江戶時代后期漢學家對日本漢文的自我認識(自我定位)。
賴山陽;江戶時代;漢文;自我認識
一 明治以降的賴山陽評價
賴山陽(1781-1832),名襄,字子成,幼名久太郎,號山陽外史、三十六峰外史。日本安藝(今廣島縣西部)人,父賴惟完,號春水,是當時著名的朱子學者。賴山陽18歲時,隨叔父賴杏坪游學江戶,進入當時的最高學府昌平黌(昌平坂學問所)學習,然未滿一年而歸。歸鄉之后,據說得了憂郁癥,品行不修,遂于寬政十二年(1800)脫藩出奔京都,后被強行帶回,剝奪嫡子身份,從此幽居反省近十年,直至文化六年(1809)被他父親的朋友菅茶山(1748-1827)收領進入福山藩(今廣島縣東部)的藩校廉塾執教。然而僅僅一年之后,賴山陽不顧眾人挽留,再度出走京都。之后,以開塾授徒、鬻文賣字、講學著述終生。
賴山陽的畢生事業是他用漢文撰寫的自平氏至德川氏諸氏執政的武家政治的興衰史《日本外史》。該書最初成稿于十年幽居期間,最終修訂完成于文政九年(1826),前后歷時20年。書中體現大義名分和尊皇賤霸的儒家史觀,對幕末的王政復古以及后來的明治維新產生了巨大影響。*明治維新三杰之一的木戶孝允(1833-1877)認為維新志士“能慷慨忠憤、殞命于國事,鼓舞海內之士氣,當該言及山陽著外史之功”。日本的首任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1841-1909)也指出:“我長州藩立勤王之志,多在外史之功。”轉引自趙建民《賴山陽的〈日本外史〉與中日史學交流》,《貴州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第76頁。然而,在其問世之初,批評的聲音似乎要多一些,其中包括對賴山陽漢文水準的質疑,即所謂的“和習”問題。例如,帆足萬里(1778-1852)曾譏諷說:“賴生所作,無論文字鄙陋,和習錯出,加以考證疏漏,議論乖僻,真可以覆瓶醬。渠以是橫得重名,真可怪嘆。”[1](P.681)
何謂“和習”?根據神田喜一郎的定義,“指日本人所特有的構思方法或表現手法,或是源于日語的語言特征而帶來的句法缺陷,或是由于漢字的和訓而產生的漢字誤用,這些出現于日本人的漢詩文之中,帶有日本人特征的東西,就稱為和習”。[2](P.102)
不過,明治以降,對賴山陽漢文的評價基本上轉而持肯定的態度。德富蘇峰(1863-1957)主張日本漢文的發展經歷了如下的一個過程:林羅山的和習→荻生徂徠的漢習→賴山陽的日本化,他認為賴山陽的“和習”是一種有意圖的積極進行日本化了的漢文:
他能夠在漢文里使用日本風格的文字語句,而且是刻意使全文的聲調得到強化,或是使色彩變得更加鮮明。這與羅山等人在不知不覺中運筆作文而無意識地露出所謂和習者,豈可同日而語。這在《日本外史》中隨處可見。他自謂“如邦俗語,卻有直用足見本色者。凡此非權度精切者,不可與之語也”。*賴山陽原文見《書伯夷傳后》,《賴山陽全書》第1部《文集·山陽先生書后》卷中,東京:國書刊行會,1931年,第57頁。所謂“邦俗語”,如《源氏記》中的“欲食者先器”、“野豬而介者”,《織田記》中的“膽生毛”等。他不僅是寫文章的行家里手,而且是備嘗其中甘苦的人。[3](P.230)
德富蘇峰的發言背景是日本明治大正以來進步主義和文化主義思想的高揚,關于語言的話語空間已經發生了變化,以往作為典范的“中國”(包括中國的漢文)已經不再是價值判斷的核心。森田思軒(1861-1897)更具體地指出,《日本外史》之所以讓人覺得有很多“和習”,是因為日本漢文是以訓讀為前提書寫的,它追求的是訓讀時的音聲悅耳,他把“和習”界定為內在于漢文之中的“風調”(melody)。[4](P.225-230)
德富蘇峰和森田思軒都強調了賴山陽漢文(訓讀)的節奏感,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應該是明治以降今文體(漢文訓讀體)的出現,才使得這種節奏感被人重新發現,并被賦予了國語的價值。問題是,賴山陽漢文的節奏感是自覺還是暗合?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回到賴山陽,看看賴山陽以及同時代的漢學家是如何書寫漢文的,從中理解他們的種種心得和苦惱。所以,本文試圖回到賴山陽的話語世界,探討它與荻生徂徠的“華音”、本居宣長的“國學”等江戶時代中后期有關漢文的其他話語的關系;并根據《賴山陽文集》中出現的中國文學家人名、漢籍書名及出現次數等資料,揭示賴山陽的知識世界,藉此分析由此構筑起來的漢文創作的文化實踐,即賴山陽的文章論。最后,通過考察賴山陽對同時代清朝文學(尤其是袁枚)的認識,探討江戶時代后期漢學家對日本漢文的自我認識(自我定位)。
二 “鐘呂之饗爰居”:荻生徂徠和賴山陽
江戶時代被稱為日本近世的文藝復興時期,是由儒者主導的漢文學的全盛時期,尤其是元祿以降,由純粹的儒者漸生出所謂文人氣質,日本的儒學與文學自是判若二途,其始作俑者,就是荻生徂徠(1666-1728,字茂卿)。徂徠的出現,對日本漢詩文的飛躍性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晚清學者俞樾(1821-1906)強調徂徠在日本漢詩詩風變遷中的重要地位:“東國之詩,至徂徠而一變。”[5](P.3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注意到,“東國之書,每行之旁,多有譯音,惟徂徠無之。朝鮮人成龍淵謂:即此一端,可知茂卿為豪杰之士”。[5](P.5)
俞樾此處所稱“譯音”,就是日本漢文訓讀法中特有的“返點”(讀音順序符號)和“送假名”(跟隨在漢字后面,指示該漢字的詞性或讀音)。依靠“返點”與“送假名”,使漢文的詞句仍保留漢語的形態,而在閱讀時,語序與讀音都轉換為日語。可以說,訓讀法就是保留原文形態的一種翻譯,是一種與日常語言不同的人工語言。
徂徠對訓讀法持批判的態度,指出“此方學者以方言讀書,號曰和訓,取諸訓詁之義,其實譯也,而人不知其為譯矣。但此方自有此方言語,中華自有中華言語,體質本殊,由何吻合?是以和訓回環之讀,雖若可通,實為牽強。”[6](P.24)他認為日本儒者學習漢文的本意是探求圣人之教,而圣人之教存在于用漢語書寫的詩書禮樂之中。通過“和訓”獲得的,只能是“黃備氏(發明訓讀法的吉備真備,695-775)之詩書禮樂”(偽真理),而不是“中國之詩書禮樂”(真理),這種以假亂真的禍害甚至大于原本的語言不通(“則其禍殆乎有甚于侏離舌者也哉”)。誠然,兩種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原本至多只能是近似化的過程,譯文與原文之間不產生過剩意義的理想化翻譯是不可能的。為了避免出現這種弊害,徂徠提出只有“口耳不用,心與目謀,思之又思,神其通之,則詩書禮樂,中國之言,吾將聽之以目”,才可以“通天下之志”,最終達到“東海出圣人”。[7](PP.3-6)他在指出中國與日本之間存在著語言的非連續性時,使用了一個比喻:
則吾東方之民又奚適?亦唯言語異宜,鐘呂之饗爰居。彼謂之侏離舌者,吾眎猶彼。[7](P.3)
“鐘呂之饗爰居”的典故出自《國語·魯語上》和《莊子·至樂第十八》。徂徠認為,漢語與日語就像鐘鼓與爰居的關系一樣,彼此原本是異質的非連續性的他者語言;但是,日本的儒者卻錯誤地以“和訓”來模糊二者之間的界線,造成連續性關系的假象。所以他認為應該以華音直讀的方法來讀解中國文獻,這樣才能完全忠實于原著。也就是說,既然中國的詩書禮樂是形成于古代中國的理想共同體內部的歷史構成物(“中國之所有,四海之所無”),置身于共同體外部的人不可能了解由內部生成的事象,要想獲得同質的共同性感覺,只能通過模仿性的同化和回歸。換句話說,中國的詩書禮樂只有通過古代漢語為媒介才可以避免產生過剩的意義,而獲得真正的理解。
徂徠的新方法遭到了其他儒者的反對,因為當時的儒者既不會說,也沒有必要說漢語。他的華音說以及模仿明七子的古文辭學,被視為越境的模仿,所謂“事事欲模漢人,字字欲擬漢人”[8](P.4),侵犯了民族意識中本應堅守的邊境。賴山陽也是華音說批判者之一,他在寫給門人小野泉藏的《答小野泉藏論詩律書》中,談到了該不該學華音的問題。
賴山陽根據自己此前旅居長崎兩個月的經驗(與長崎清客楊兆元、陸如金等人的交游),認為“華音不足學,八病不足拘,以其在彼已廢歌唱也。而強說之者,舌官驕人之具耳”,盡管在詩歌的格律上應該遵守中國的標準,但是,華音則不必學:
音節諧否,不待華音者,本書已言之矣。更有一證,試取明清人評古詩者覽之,曰某篇有調者,我亦覺其有調,曰某字不響者,我亦覺其不響。如袁倉山論“群山萬壑赴荊門”,不可改“群”為“千”,誦而味之,信然。非意有異同,所爭音節而已。是故詩之驚心動魂總在吟誦之際,不必待細繹其義,而涕已墜之。是知聲音之道,和漢無大異也。假令浮切不差,如譯家所言,而歌以華音,聞以邦耳,是亦爰居鐘鼓,何感情之有?[9](PP.369-370)
“詩之驚心動魂總在吟誦之際,不必待細繹其義,而涕已墜之”,賴山陽此處所謂吟誦,指的是“素讀”,即根據漢文原文上標注的返點和送假名,進行朗讀,這是當時漢文教育中最基礎的學習方法。如前所述,訓讀是一種與日常語言不同的人工語言,它的節奏(音節)既不同于漢語的節奏,也不同于日語日常語言的節奏,但是,通過童蒙時期的“素讀”教育,訓讀的節奏作為獨特的節奏被身體化。因而,能夠在“細繹其義”之前,感受到由非日常語言節奏帶來的非日常的鏗鏘昂揚或纏綿悱惻的美感。所以,賴山陽認為“聲音之道,和漢無大異也”。
問題是,倘若像“譯家”那樣,用日本人聽不懂的華音來吟誦的話,那將會如何呢?其結果肯定無異于“鐘呂之饗爰居”。既聞之茫然,不知所云,那么,詩歌里的情感何以傳達?
概括地說,荻生徂徠和賴山陽最根本的分歧點在于:徂徠是站在“解釋者”的立場,而賴山陽則站在“作者”的角度。解釋者需要進入文本的“內部”(事物與言語的統一體),與作者(圣人)獲得共感。而賴山陽考慮的是怎樣“用彼之言語以敘我之性情”[9](P.367),漢文只是一種藉以表達自我思想情感的工具。
在近代之前的日本,其書記系統大致可分為“純漢文”、“變體漢文”、“假名文”、“漢字假名混雜文”等數種。但是,作為高度文明之載體的漢文,是具有價值規范的高級語言,因而具有普世性。例如,賴山陽在《續八大家文讀本序》中,提到自己撰寫《日本外史》到豐臣秀吉的傳記時,“蓋有投筆而嘆者”:豐臣秀吉出兵朝鮮時,有人提議讓通曉漢文者從軍出征,但豐臣秀吉笑著說:“惡用漢文為,吾直將使彼用我文耳。”*事在《日本外史》卷十六《德川氏前記·豐臣氏下》。賴山陽認為假使當年豐臣氏有通曉漢文者作參謀,“能得彼之要領,而施我機宜,不至如當日之失乎肯綮、禍結不解必也”。所以,他總結說:
夫我非無文也,而終不及彼。資于彼,用于我,何為不可?茍以我所自有為足乎,雖所謂藥物,不必須彼之參、茋、硝、黃。參、芪、硝、黃之必須于彼,可以知文亦必須于彼也。要以其辨是非,別利害,言之簡明,傳之不謬者。漢文之用,寧可廢哉。[9](P.458)
他承認日文在表達上不如漢文來得簡潔準確,但是,充其量只是取資和借用,反對全盤漢化(如荻生徂徠)。同時,亦反對本居宣長“國學派”的刻意排斥漢文。
本居宣長(1730-1801)認為唯一能夠正確地記述本國諸神創世的典籍,不是《日本書記》,而是《古事記》。因為前者是用漢文書寫的,是站在中國的角度來審視日本的歷史;而后者只是借用漢字表音,實質上保留了日本上古時代的口語,“未加絲毫自作聰明”[10](P.288),故而最為可信。在意識形態上,他主張以“和魂”(日本人固有的心性)對抗“漢意”(中國式思維樣式)。但是,正如酒井直樹氏指出的那樣,在本居宣長的著作里刻意使用的文體本身,盡管試圖通過排除起源于漢語的發音,以使語言更為本土化,但是,他的這種嘗試幾乎是絕望的。因為表音符號和表意符號已經完全融入日語之中,如果把所有表意元素都剔除掉的話,書記系統將徹底崩潰。[11](P.380)
作為儒者的賴山陽,首先在思想上不可能接受本居宣長的神道思想。在對待漢文的態度上,其主張亦截然相反。他在《讀本居氏家言》中說:
余嘗謂王跡熄而神道興,當其盛時,誰敢舉祖宗之事,嘵嘵樹門戶哉?如近時本居氏,尤甚者也。余嘗謂其徒弟曰:“子之師,幸不出八九百年前耳。若然,必不免議王憲之誅。”又謂之曰:“子等小視我邦,故介介然抑漢揚和為務,如余以為我邦至大,取四外所貢文籍,以為我用,何敢以漢為對。”其人爽然。[12](PP.76-77)
“王跡熄”云云,最早出自《孟子·離婁下》“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但是從“王跡熄而神道興”整句以及后文所要表達的意思來看,我覺得更像模仿元代王漸《穆天子傳序》*《賴山陽文集》中雖然沒有提及《穆天子傳》,但是,《穆天子傳》在日本并不陌生,大約成書于寬仁2年(1018)的《和漢朗詠集》就已經出現了使用《穆天子傳》典故的漢詩作品,如菅原文時《韻鳥聲管弦》詩中有“周穆新會,西母之云欲歸”句(《和漢朗詠集》卷下)。中的“王跡熄而圣言湮,處士橫議而異端起”。也就是說,在他眼里,本居宣長的所謂國學乃是一種異端思想,并且是一種狹隘的小國思想,刻意的“抑漢揚和”實質上是潛意識中的自卑心理在作祟。他主張,在文化上應該采取普遍主義、拿來主義,這才是文化大國應有的姿態。而且,他還認為,作為儒教之本質以及文化之核心的“道”是普世性的,非一國所私有,“今天下之仁義也,儒者指而私之曰:是漢之道也。有稱國學者,斥而外之,曰是非我之道也。皆非也。道豈有彼此”?[13](PP.21-22)荻生徂徠“事事欲模漢人,字字欲擬漢人”以及本居宣長刻意提倡“和魂”的做法都是錯誤的。
那么,在詩文創作實踐中,賴山陽是怎樣處理漢文(形式)和性情(內容)之關系的呢?前引賴山陽在寫給門人小野泉藏的書簡中,談到既然使用漢文這種文體,就不得不依照漢詩文的一定規矩,但是,他接著說:“但就其規矱中,必避其病之最可忌者,其故設險艱者,不必學可也。”這是就漢詩而言,漢文的情況亦然。荻生徂徠曾經指出,日本人在書寫漢文時應遵守三條戒律:第一,戒和字(同訓異義字);第二,戒和句(詞序顛倒);第三,戒和習(語氣聲勢不類中華)。賴山陽的漢文在避免和字、和句上,作到了徹底防患。例如,他在撰寫《日本外史》的時候,曾向友人借閱皆川淇園(1735-1807)《史記助字法》作參考。[9](P.135)但是,對荻生徂徠所謂的“和習”*后世對“和習”的定義要比荻生徂徠來得廣義。因而,徂徠的“和習”,如果換一個詞來表達的話,或許應該稱為“和意”。并不十分在意,因為他覺得“生于日東之儒,其職分在于較量和漢時勢人情,所謂西土之圣訓應合我邦之時宜,為此君民之理所當然也”[3](P.105),他在漢文中表現的是日本人的精神氣質。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前述森田思軒指出《日本外史》乃是以訓讀為前提書寫的,它追求的是訓讀時的音聲悅耳。
原則上,訓讀原本是為閱讀而發明出來的技法,然而,它也介入到寫作之中。若將“漢文原文”→“訓讀文”→“和漢混合文”→“日文”(意思理解)這個過程的順序顛倒過來,從原理上,又可以還原到漢文。事實上,在當時的學校教育中,就有這種被稱為“復文”的訓練。
賴山陽曾談到自己在撰寫《日本外史》時,對《史記·項羽本紀》的模仿:
《史記》百三十篇,篇篇變化,然求其局勢尤大、法度森嚴者,在《項羽紀》。要觀其大開合處,然不逐段細繹,其大者亦不可悟。余嘗手寫一通,隨讀批圈勾截,及修《外史》,每晨朗誦一過,覺得力不少。[10](P.84)
賴山陽此處所謂“得力不少”,除了齋藤希史氏指出的訓讀節奏之外,我覺得更多的應該還是從《史記》中體味出來的史筆與文章軌范。晚清學者譚獻在評論《日本外史》時,認為它“有意規摹《左傳》《史記》”,雖然只是形似,但是遠在明代王世貞之上。[14](P.130)應該說,譚獻的判斷頗中肯綮,尤其是與王世貞的比較。因為在賴山陽的時代,日本漢學界的文學主張基本上就是反對復古摹擬,修正以荻生徂徠為首的古文辭派對明七子的盲從。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賴山陽在這方面的文學主張,即應該怎么學習寫漢文的問題。
三 賴山陽的文章論
首先,根據賴山陽的編年《文集》,可以將他所創作的古文,大致分為“前外史時期”(1791-1799)、“外史撰寫期”(1800-1809)、“外史修訂期”(1810-1826)和“后外史時期”(1827-1832),其中“前外史時期”因為尚為古文學習初階,文集中收錄的文章很少,而且時間也較短,所以不在本文統計范圍之內。再根據《文集》中出現的中國文學家人名、漢籍書名的時代進行縱向分類,大致可分為“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以唐代為主)、“宋元”(以宋代為主)、“明”、“清”。按照橫軸的三個時段,分別統計出各個時代中國文學家人名(表1)、書名(表2)的出現次數和比例,以揭示賴山陽的知識世界。

表1 《賴山陽文集》中出現中國文學家人名次數的階段性分布

表2 《賴山陽文集》中出現漢籍書名次數的階段性分布
通過整理人名和書名出現次數的階段性分布情況,可以掌握如下特征:賴山陽在撰寫《日本外史》期間,提到最多的是先秦兩漢的文學家和漢籍;在修訂《日本外史》時期,亦是他漢文創作的黃金時期,提到最多的是唐宋文學家,宋元時代漢籍也從前期的8.3%迅速上升為20%;后外史時期,也是賴山陽的晚年,提到最多的依然還是唐宋文學家,但是,清代文學家出現的次數,比前兩個時期有了顯著增長,僅次于唐宋,說明他在晚年加強了對清代文學的關注,這一點也表現在清人詩文集出現的比例上,高達39.1%,第一次超過了先秦兩漢。
如前所述,《日本外史》在史筆和體裁上模仿《左傳》和《史記》,所以表1和表2的“外史撰寫期”提到最多的是先秦兩漢的文學家和漢籍,分別是48%和45.8%。而表1的后兩個時期,先秦兩漢的比例明顯下降,主要是因為在這兩個時期,在京都開塾授徒、講學著述的賴山陽主要是談一般漢文的寫作,而非撰史,所以,他強調的是對唐宋八大家的學習。不過,唐宋八家的源頭還是先秦散文,因而,表2出現的漢籍書名次數一直以先秦兩漢為最。表2中之所以出現大量的清朝書籍,因為清代與江戶時代差不多屬于同一時代,從事中日海上貿易的清客販運到日本的當然多為本朝圖籍。另一方面也說明日本文壇很敏感地關注著來自中國文壇的最新動向。
接下來,讓我們再來看看出現次數比較多的都是哪些文學家,都提到了哪些書(表3)。

表3 《賴山陽文集》中出現文學家與漢籍的排名表
從出現次數較多的人名來看,唐宋八大家出現了五個,這基本上符合賴山陽對唐宋八大家的評價。除了蘇洵之外,賴山陽對八家中的另外兩家,即曾鞏和王安石的評價不高,反對將其列為大家。如《八大家文讀本沈德潛序例注》云:“余所不滿于茅(坤)者,以曾(鞏)、王(安石)列焉。蓋茅師王遵巖,遵巖喜曾,故收之也。大抵明嘉(靖)、萬(歷)間,世多厭宋習,頗倡秦、漢,而王與唐荊川樹幟敵之。以歐、蘇易流淡泊,而曾差豐縟,王差峭潔,足以相救,于是取用之。而茅亦依其繩尺焉耳。要之,曾、王豈可列為大家哉?”[9](P.404)
大約在明末清初,古文辭派和唐宋派流傳到日本。經過荻生徂徠旗幟鮮明的提倡和大力推廣,李攀龍、王世貞的古文辭風靡了日本近世文壇,“遂使家有滄溟之集,人抱弇洲之書”。[5](P.4)進入江戶時代后期的文化、文政年間,反徂徠派的抬頭,使古文辭說得到了全面修正。在詩歌方面,由推崇唐詩轉而尊奉宋詩;在文章方面,唐宋八大家風行文壇。文化十一年(1814),官版翻刻了沈德潛的《唐宋八大家讀本》。文政四年(1821),昌平黌大學頭(校長)林述齋受松山藩的委托,在講述漢學研究入門書的講義《初學課業次第》中,將《唐宋八大家文鈔》列為學習漢文的必讀書目。“寬政三博士”中的尾藤二洲(1745-1813)和古賀精里(1750-1817)——賴山陽在昌平黌時的老師——都提倡以唐宋八家的古文為模范。不過,在唐宋八家中,尾藤二洲更重視韓、柳、歐、蘇四家,[15](P.221)他的主張為賴山陽所繼承。賴山陽論文主要也推崇四家,他在寫給門人甲斐國干的《經說文話十則》中指出:
文宗秦漢,而韓、柳、歐、蘇其梯也。四家去陳言,以達意為主。其弊至明,化為冗易。北地、信陽其志則可,其文則不可。至歷城、大倉,欲掩前人,遂陷魔道。是等小家數,不可與前四家比。……不多誦先秦書,則其文弱矣;不多誦四家文,則其文澀矣。議論敘事,皆以自了為了。己不自了,焉能了人?多誦古文,多作自家文,他無秘訣。[12](PP.665-666)
古文的理想形態存在于先秦兩漢,而唐宋四家則是上達理想的必要階梯。而且對于初學者而言,若不依照一定格式的話,則散漫不成文,所以,他在寫給另一位門人村瀨士錦的信中指出:“文各有體,體昉于八家,涉讀八家文選,會所結構,自不失格焉,否則不成文字。”[9](P.217)但是,八家之文不過是尋求古文理想形態的階梯(工具),不是目的本身,他以文法與劍法相比較,認為“抑其起伏開闔、頓挫撇脫諸法,文與劍同。劍有此法,而期于防己、制敵而已;文有此法,而期于辨是非、別利害而已”,不能“拘乎其法,而失其所以為法”,否則“終為無用”。[9](P.459)賴山陽曾經在文政三年(1820)冬至翌年春,對《唐宋八大家讀本》施以評點,后陸續有所增補,即安政二年(1855)出版的《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并在文政九年為村瀨誨輔(1781-1856)的《續唐宋八大家文讀本》作序。賴山陽對唐宋八大家,尤其是《唐宋八大家讀本》在民間的普及和流行起了重要作用。[16](P.80)
關于先秦兩漢古文與唐宋四家的關系,賴山陽在年輕時(大約在文化初年)*據德富蘇峰的考證,《古文典刑》成書于文化二年(1805),《小文規則》成書于文化三年(1806)。分別見《古文典刑解題》和《小文規則解題》,《全集》下《古文典刑》,第1頁,《小文規則》,第1頁。曾編撰秦漢古文和唐宋四家小品,分別編為《古文典刑》和《小文規則》。他在《古文典刑》的《凡例》中指出今人學八家之文,之所以“不及其如江如海者”,就在于一味沿襲韓、柳古文的定體,“沿而不泝”,未能推本溯流,編撰此書的用意就在于“欲使人悟韓、柳用筆之所本”。[17](P.2)然而,秦漢之文和唐宋之文,乃是構成古文世界的一個整體,文雖宗秦漢,卻不可不博覽秦漢以后之文,就像詩宗盛唐一樣,若“唯盛唐是守,而不博觀中、晚、宋賢,吾知其不能為李杜奴隸也”。[9](P.217)關于這一點,可以說亦是尾藤二洲之主張(或者說,此乃當時的通論),尾藤二洲《靜寄余筆》卷上云:
詩至李、杜,文至韓、柳,體制備矣,模范立矣,后世作者,無得而逾焉。然學韓、柳,非多讀周漢古書則不可。學李、杜,非多讀魏晉撰詩則不可。譬諸樹焉,周漢、魏晉,根也;李、杜、韓、柳,干也。干堪棟梁,靡不由根之蟠屈。若知干而不原諸根,見根而不觀諸干,猶為不知樹。[15](P.200)
不過,盡管各家或稱“八家”,或稱“四家”,但由于各人的性向喜好不同,就唐宋八家之中,也各有所偏重。前述表3所列文學家人名出現次數最多的是蘇軾,也就是說,賴山陽在八家中尤其重視蘇軾的文章。賴山陽主要重視蘇軾的論策之文,而這方面恰恰歷來不為日本漢學家所重。如《讀櫟園書影》云:
余常嘆我國古今文運兩開,每開未學彼之佳,先學彼之惡,前為駢儷體,后為古文辭,未及為韓、歐。即有為者,其業不大且熟也。至為蘇者,絕無矣。蓋我稱文者,序、記、銘、贊,無事于議論大文故爾。[12](P.104)
他自稱幼時秉承家學,唯“爛熟《小學》《近思錄》而已”,十四五歲時,偶然的機會接觸到蘇軾的史論,“詫曰天地間有如此可喜者”,“自是遂有學文之志”。[12](PP.91-92)而且,認為“子瞻心胸之間,常有天下二字,文辭特其游戲”,同感于蘇軾“以曠世之識、絕人之才,而不得一施之事業,獨其執筆,為人主指畫天下大事者”。[9](P.116)可以說,這也是賴山陽欲以修史來鼓吹勤王的原點之一。賴山陽常以東坡自況,時人亦以東坡目之,以致有“日本東坡”之稱。門人小野泉藏曾有贈詩云:“天下文章萃一家,長公最是患才多。到處逢人何所說,方今都下有東坡。”[18](P.443)賴山陽的漢文在文章雄健、長于議論之處,得到了當時日本漢學界的共識。古賀侗庵(1788-1847,古賀精里次子)在批評《日本外史》行文“平衍卑凡,靡一點古色”的同時,又盛譽其中的論贊部分,說:
然子成夙心醉于蘇,長于論而拙于紀述。即使之處心不偏以成史,不過加于斯書數等,斷不能大動人。每讀《外史》到卷末論,頓覺輝光奕奕四射,可知人各有能與不能焉。子成別有《通議》一篇,專論經世要務,其瑰奇更勝《外史》。《外史》紀論參半,間露子成之短。《通議》一于論,正為子成擅場,真全璧也。[18](P.126)
為古賀侗庵所激賞的《通議》,正是得力于蘇軾,賴山陽在《讀東坡論策后》中提到了《通議》對蘇軾論策的模仿志向:“余作《通議》,欲一語仿佛不可得也。”[12](P.93)
賴山陽的漢文,除了史論之外,其他諸如碑版、敘記之類的文章,后世評價不是很高。其主要原因是賴山陽是才子,而非學者,他的漢文是才子之文,而不是學者之文。然題跋、論難、品詩論畫之類,不待學力而偏重才氣的小品文,頗能做到意到筆隨、簡潔而有雋味。但是,“其文品不似東坡,而近隨園。”[18](P.169)其實,不獨小品文,賴山陽的漢詩尤近袁枚,故又有“近世之隨園”的稱號。[19](P.1)不過,有趣的是,賴山陽對袁枚的評價卻非常苛刻。
四 “漢物之不必可尚也”:賴山陽的清文認識
在江戶時代后期,袁枚是日本詩人中最受歡迎的同時代人。袁枚所提倡的性靈說,將日本詩壇從明代七子所鼓吹的盛唐詩風模仿(格調派)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可謂影響巨大,尤其是對市河寬齋(1749-1820)一派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賴山陽在《浙西六家詩鈔》(道光年間吳應和輯)卷之五《仿元遺山論詩》的眉批中,論及袁枚:
渠嘗評阮翁為一良家女,五官端正,薰以名香,被以錦繡,假動一時耳,非天仙化人,一見銷人魂者。是為稍確。余欲評此叟曰:隨園如黠妓,雖無姿色,善為妖媚態,眩惑少年子也。[19](PP.49-50)
賴山陽所引袁枚對王士禛的品評,在《隨園詩話》卷3第29條。宋琬曾有“絕代消魂王阮亭”之說,有人便問袁枚,這是不是真的?于是,袁枚作了上述比喻。所謂“薰以名香”,是指王士禛詩在修詞琢句上,“捃摭于大歷十子、宋元名家,取彼碎金,成我風格”。亦即錢鐘書所謂“漁洋以人工勝也”。[20](P.97)賴山陽之攻隨園,一如章學誠的頭巾氣盛。
賴山陽在文集中提到清代詩文時,多處將批評的舌鋒直指袁枚。如《書倉山詩鈔后》提到市河米庵(1779-1858,市河寬齋子)評價《小倉山房全集》曰硬,“余加一字,曰粗,更加一字,曰俗”。[12](P.118)又如,在《書藏園甌北詩鈔后》中,認為“隨園學不及甌北,才不及藏園,而意常踞二人上。其嘗評厲樊榭吊古詩,曰數典而已。是袁自道可也。”[12](P.119)袁枚的諧謔之作如《落齒》詩,或可以用“粗俗”二字來形容,但是,說“數典而已”乃袁枚夫子自道,則大失公允之心。其他如稱袁枚為了對抗沈德潛“格調說”在乾嘉詩壇的正統地位,“每事反于沈,沈獎雅黜鄭,故袁不得不獎鄭黜雅”[9](P.599),固為不易之確論,因為無論“獎雅黜鄭”還是“獎鄭黜雅”,不外乎是借此在文化生產的場域樹立起一種優劣關系,“雅樂”和“鄭聲”不過是保證自我卓越性的社會符號,所以,一“獎”一“黜”,可以說,就是雙方爭奪各自價值體系正統性的符號斗爭。不過,賴山陽對袁枚的種種批評,很難說是他的獨出機杼,不外是沿襲王昶《湖海詩傳》之類的腔調,近乎耳食而已。*賴山陽評點的《浙西六家詩鈔》,原書卷五的袁枚小傳中,幾乎全文引用了王昶《湖海詩傳·蒲褐山房詩話》有關袁枚的評述。然而,倘若揭掉這些習套的批評,我們是否可以發現一些賴山陽的真實想法呢?
賴山陽評點的《浙西六家詩鈔》,在他歿后十七年的嘉永二年(1849),于大阪刊行,賴山陽的摯友篠崎小竹(1781-1851)為其作序云:
山陽評清人詩文,有抑有揚,至于隨園,則抑之殊甚。予察其意,非惡隨園也,亦為隨園也。隨園才學,能壓當時,其議論著作,悉脫陳腐,出人意表,凌轢古今,自成一家。觀者爽然,莫之敢攖矣。山陽以為子才實才子,然亦太傲慢,因索其疵瑕,指擿不遺,使隨園不得專權藝圃。乃移史筆于詩詞,發新意于詠懷,自成其家,一時仰之,亦近世之隨園也。學者欲名世者,不可無隨園、山陽之志,然所須先自量其才與學。[19](P.1)
在這篇序文中,固然不免充滿了揄揚的氣氛,然而卻說明了很重要的兩點:(一)賴山陽批評袁枚的真實意圖是見獵心喜,欲通過刻意貶抑,使其“不得專權藝圃”;(二)最終要達到的目標是“名世”,藉以標榜一家之學,而非僅僅滿足于與隨園分庭抗禮而已。
這種競爭的意識,使得賴山陽十分在意收集有關袁枚的信息。文政元年(1818)八月,賴山陽西游長崎,與清客楊兆元(西亭)、陸如金(品三)進行了筆談,這是他唯一一次與中國“文人”之間的對話:
聞吳中為人文淵藪,見今最著稱者何人?襄謹問。
下問。只潘石泉、董山霞二先生為最,其余不可申數。如再覆。
袁隨園先生在陋邦亦大名耳,料已下世矣。同時齊名者何人?襄。
隨園已故。其時齊名者沈歸愚,字德潛,諱恪士也。才學相同,而貌亦相若。如。[21](P.445)
雖然賴山陽從筆談中獲得的有關中國文壇的情報并不多,但是,從他的提問中,可以看出其對袁枚的關注程度。
賴山陽對袁枚的詩貶抑過甚,而對袁枚的古文卻揄揚有加,《書倉山文鈔后》云:
袁倉山在此方嘩稱其詩,而文實出詩上數級。雖序、記、論不免時習,至碑傳、書柬,其敘寫辯駁,皆有生色。然吾嘗疑當時名人碑板,似無不倩其手,何哉?后閱王蘭泉《詩話》,知渠不待倩而作,以暴人耳目。其文雖佳,其人可薄如此。[12](PP.118-119)
賴山陽認為袁枚在古文方面的成就要勝過詩歌,倘若隨園有知,必歡呼曰“實獲我心”,因為袁枚所自負的正在古文。其《答平姚海書》云:“今知詩者多,知文者少,知散行文尤少。枚空山無俚,為此于舉世不為之時,自甘灰沒。”[22](P.528)又《與孫俌之秀才書》云:“仆年七十有七,則死愈近而傳愈急矣。奈數十年來,傳詩者多,傳文者少,傳散行文者尤少。”[22](P.642)
遺憾的是,對于袁枚多為名人碑志而不待其子孫之請求者,賴山陽還是難免和多數人一樣,站在道德層次上進行批判。據郭紹虞先生的解釋,袁枚之所以如此,是自有苦心的:“他以為局局促促以小題目自限者,都不免有一些鄉野氣。他正因為不要有鄉野氣,所以欲得大題目而為之。……他之為名人傳志,一方面為不負其才,一方面亦報國之道。”[23](PP.487-488)所謂的“大題目”,就是足以翼贊圣人之道的古文。要之,通過表彰名人的功德忠勛,以“敷贊圣旨”,從而實現我之不朽“立言”。最高層次的“大題目”,應該就是修史吧。賴山陽的私修國史,又何嘗不是“不待倩而作”呢?
實際上,賴山陽與袁枚的文論,多貌異心同者。例如,袁枚在《虞東先生文集序》中認為形而上的“道”只有通過形而下的“文”(器)來表現,貼切的言語表現是正確表達內容的先決條件,而且還是吸引讀者以達到教化目的的必要條件,因而善文者有助于明道。[22](P.184)而賴山陽亦云:“治經者罵攻文者為陋,文與經,如此殊途乎?馬、鄭、孔、邢之徒,果能得古圣人之意,而韓、歐否乎?”*賴山陽《問村瀨士錦條目七則》,《賴山陽文集》卷六,第223頁。很難說賴山陽受了袁枚的影響,因為在撰寫此文的文化九年,賴山陽尚未看過《小倉山房全集》。文化十二年出版的《清百家絕句》未收袁枚的詩,該書《凡例》云:“乾隆三家,獨取蔣藏園,不及袁倉山、趙云松,他日見兩家全集,可收入續編。”可為佐證。認為文學與經學殊途同歸,質疑像馬融、鄭玄、孔安國、邢邴這樣的經學家,是不是就一定比韓愈、歐陽修更能洞悉真理(古圣人之意)。故而他認為治經應以文章為先:
不以經視經,而以文視經,且置六經,旁讀先秦古書,熟其語意口氣,然后還看六經,向之詰屈聱牙者,將迎刃而解。諸家注疏,概屬無用矣。夫經豈別物,亦文而已耳。世之儒生,童習白紛,仡仡不通,皆坐不以文視經而以經視經也。故仆授生徒,以文章為先。作為文章,溯秦漢,沿唐宋,秦漢、唐宋之文,如己口出,則千載之人,旦暮逢之,鄭、馬、程、朱,于我何有?[9](P.220)
從賴山陽的這段文字來看,尤其是“經豈別物,亦文而已”,表面上似乎隱含著“六經皆文”的主張,其實不然。因為他講的只是讀經的方法論問題,并沒有涉及“六經”和“文”的關系孰優孰劣的價值問題,更沒有像章學誠的“六經皆史”那樣,否定經書權威而隱含足以顛覆儒教根本的破壞力。他只是涉及語言的連續性問題。也就是說,在研讀經書時,最重要的不是借助歷史上各家(“鄭、馬、程、朱”)的經書解釋,來進行輔助性的理解,而是試圖通過閱讀先秦古書(最接近六經的上古語言),使之熟練化、身體化(“如己口出”),這樣,被身體化了的上古時代的漢語與經書語言之間構成了一種連續性的關系,“然后還看六經,向之詰屈聱牙者,將迎刃而解”。換句話說,他的這條授徒指南,希望解決的是學生在研讀經書過程中的語言障礙問題,而不是懷疑經書的價值,他至多是在質疑諸家注疏的價值。總而言之,賴山陽不是一個博覽的學者,更不是嚴謹的經學家,他甚至認為不得已需要借助經注時,也只要看一二家就夠了,當問題依然無法得到解決的時候,采取“姑且闕之”的態度。*賴山陽《讀五經正義》云:“吾使從游者治經,唯平心讀正文,循其語勢,又取古書與同時者,錯而誦之,習其口氣,則可了四五分。遇不通處,然后看注,注主一家。猶不通,更看他注。猶不通,則姑闕之。是省力法也。”可知,賴山陽的以文讀經的方法,并不能完全解決語言的問題。《山陽先生書后》,第36頁。這種方法是讀書的,卻不是治學的。
如前所述,賴山陽之攻擊袁枚,并非僅僅是一種“性靈派”和“格調派”,或者“道學”與“反道學”之間的門戶之見。相反,他反對日本漢學家人云亦云地輕易卷入中國文壇的門戶之爭。《書藏園甌北詩鈔后》云:“彼斗其名于大海外,何干我輩事?此間文士,不詳人之爭端,每每視其后出樹幟者,欲黨屬之,何哉?”[12](P.119)更不是簡單的文人相輕,因為他要對抗的不是一個袁枚,而是整個清國的文壇,是對日本漢文如何自我評價、自我定位的一個思考。
作為歷史背景,首先,江戶時代的日本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變化。寬文九年(1669),儒學家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實》一書中,對中國和日本的優劣進行了比較,認為日本從未受到過異族的征服和統治,也從未有過王朝更替(天皇萬世一系論),而同時期的中國在1644年發生了明清鼎革,而且是由漢民族王朝向異民族王朝的更替,以此為根據,主張日本才是真正的“中華”。[24](P.34-67)這就是所謂的“華夷變態”。*長崎奉行將正保元年(1644)至享保二年(1717)之間,從中國貿易船獲得的有關中國的情報(風說書)約2200通進呈幕府,幕府儒者林春齋、林信篤據此編輯為《唐人風說書》,后改名為《華夷變態》。參照大庭修《徳川吉宗と康煕帝鎖國下での日中交流》,大修館書店1999年版,第66-67頁。而且,在16世紀末,日本停止了日明貿易,事實上已經從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制中脫離出來。不過,在內面上,漢文以及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朱子學依然支配著江戶時代日本的核心價值觀念。例如,作為“載道之書”的六經,是中國得以自稱中國的根據,在經學方面,中國人的研究具有絕對的權威:“六經,漢土物也。六經之可言者,漢土人盡之矣。而日本人敢是非之,是猶三家村子弟,月旦都下演劇,其說可行三家村,不可行于都下。藤(伊藤仁齋)、荻(荻生徂徠)之張于此間,何以異之。”[9](PP.213-214)在中國人的經學(包括清朝的考證學)面前,深懷無奈與自卑。然而,在詩文創作方面卻不無敝帚自珍之處。
文化十二年(1815),賴山陽的幾個門人輯鈔清人絕句,編為《清百家絕句》,送賴山陽審閱,他先是把它扔到了地上,說:“咄!辮發虜所為,安足取哉?子等枉費精力耳。”充滿了鄙夷之情。稍后他又自笑說:“吾輩開口輒曰唐、曰宋,其所以自撰者,曾不能仿佛西土黃口小兒,猶夫日摹《蘭亭》,而不及蘇杭舶商俗書。”意思是,自詡出現華夷逆轉,標榜自我文化正統性的日本文人,其詩文書畫的藝術水準,實際上還不如墮落為“夷”的清國兒童和商賈。清朝人的詩,作為上達唐宋的階梯,亦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遂取而一閱,略刪其繁蕪,以與之”,[9](PP.273-274)同年十月,由名古屋永樂屋刊行。
前面談到賴山陽在處理漢文的形式與內容時,曾經說過“生于日東之儒,其職分在于較量和漢時勢人情,所謂西土之圣訓應合我邦之時宜,為此君民之理所當然也”,對于舶來的中國文化(包括圣人之道),賴山陽認為應該根據本國的情況有所擇取,而不是照單全收。《送醫人之長崎序》云:
羲、農、堯、禹之道,不過土其土、民其民,各從其宜而已。故六藝之文,猶覺其多。何也?有宜乎我,有不宜乎我,宜者十七,而不宜者四。然儒之拘愚者,重彼輕我。茍為彼乎,一圖一籍,尊奉不措,費精而究。孔、鄭而降,以至于今,疏于其疏,如縷與蟻者已。論即喧諍咳唾,極無益者,亦珠璣視之。至其施諸我也,不酌其宜,而求必通,猶通方蓋于圓底,拘矣!東京以降之圖籍,譬之彼之罽絨琛瓊,不啻無益于我,或有費于我。況羲、農、堯、禹之土,今也約于覺羅滿氏,乃鼠尾馬蹄之人,自盛其咳唾于船而東,東之人乃尊而奉之,愚矣
賴山陽認為圣人治世的時代,世界上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產,不求互通有無。“六藝之文,猶覺其多”,即《論語·子路篇》:“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才學貴于適用,若多學而不能用,則如不學也。”所以,如果要謀求通商互市的話,也不是多多益善,要看適用于己與否。宋代以后的書籍,雖然對于中國來說也許是奇珍異寶(罽絨琛瓊),但是,卻無益于日本。而實際上,舶來的中國文化,不適用于日本的占了四成,尤其是清代人的詩文(咳唾)。他曾以和酒為喻,指出日本的漢文未必輸給中國,《題手批海紅園小稿》記述了文政九年(1826)昌平坂學問所書生寮長野田笛浦(字子明),護送清國漂著船至長崎,華商中有朱柳橋者,“蓋浙中紳衿子弟,以場屋利緩,輟而從事舶估”,幕府為他們準備了十二壇“劍菱”名酒:
朱生輩初意其不佳,飲其所齋浙酒,已而稍稍沽唇,乃鼓舌稱妙,遂非我酒不飲。蓋與所嘗飲崎酒例視,后乃知有大不侔,雖彼中酒不及。猶渠輩常輕視此間文詞,而忽逢如子明者。[9](PP.465-466)
朱柳橋他們在未喝“劍菱”之前,并不懂得日本酒的妙味,就像未看過野田笛浦的文章以前,常常輕視日本漢文一樣。但是,喝過“劍菱”之后,“非我酒不飲”。言下之意,看過野田笛浦的漢文之后,是不是也“非我文不觀”呢?同樣,他又舉了日本產的毛筆為例,說日本人崇拜中國舶來的“唐筆”,而清客江蕓閣卻特意托他購買日本生花堂的毛筆[9](P.643),而且,他自己曾經買過中國的“小文筆”,質量粗惡不堪,于是,他得出的結論是:“亦知漢物之不必可尚也。”[9](P.281)
甚至在為文人陶工、南畫家青木木米(1767-1833)翻刻的清代朱琰《陶說》作序時,稱朱琰在《陶說》中所謂“人心優裕,民力綏閑,地產物華,應運而起”者,“將不在彼而在此”[9](PP.492-493),筆下充滿了文化的自信力。
五 結束語
文政十一年(1828),晚年的賴山陽模仿明代李東陽以樂府形式吟詠歷代史實的《擬古樂府》,作《日本樂府》66篇,以篇數合日本66國數。其內容是以年代為順序,歌詠日本國史上的事件,或可謂是他的另外一部史著《日本政記》(神武天皇以來的歷代天皇史)的詩史形式作品。他在《日本樂府跋》中,自稱希望通過歌詠日本獨特的“風氣人物”,以闡發治亂機竅和名教是非的經世致用宗旨。對于《日本樂府》在形式上,與李東陽《擬古樂府》以及清代尤侗《擬明史樂府》的關系,作了辯解:
今茲臘尾,人忙我閑,就國乘中掇取題目,得六十六闋,如我州數。我國風氣人物,何必減西土,恨余詞鄙俚率薄,不足齒漢兒。然人茍耐讀,盡頭至尾,于治亂之機竅,名教之是非,或可以小喻大。客曰:“然則是模擬李、尤耶?”余哂不答。見研旁銅瓶插臘梅,指問客曰:“渠香色固讓楳矣,然天地所置,日月所照,各含一造化,乃曰汝擬梅也,渠當肯否?”曰:“不肯。”[9](P.525)
否認《日本樂府》只是李東陽和尤侗作品的簡單模仿,*但是,他在這一年寫給女弟子江馬細香的信中,卻明明白白地說是模仿李東陽的樂府。而且,賴山陽在《跋》中,對中國樂府詩源流的概述,亦大體沿用了李東陽在《擬古樂府引》中的表述。雖然外觀形似,甚至在遣詞造句上相比遜色,但是,在所表現的內容上,日本和中國各自有獨特的發展繁衍的歷史事象,這是無法模擬的,各有各存在的價值和意義。該書刊行于文政十三年,并經由水野媚川(?-1846,負責管理供清客住宿的“唐人屋敷”)和沈萍香,介紹到中國,《履園叢話》的作者錢泳(1759-1844)為其題詩二首,盛贊《日本樂府》“實比李尤工”。[25]賴山陽在《跋》中所表現出來的文化上不服輸精神以及對漢文創作的自信,似乎傳遞到了中國并得到了充分領會。
蔡毅先生曾通過考察賴山陽《日本樂府》和市河寬齋《全唐詩逸》向中國的“逆輸出”(feedback)現象,探討江戶時代中后期日本漢學界的文化自覺,指出以明治維新為分水嶺而發生的日中文化“逆轉”現象,早在江戶時代中期已經出現了先兆:“在江戶時代后期,日本漢學界已經不再滿足于對中國的追隨,試圖展現自我特色。同時,將其成果積極地傳達給文化的宗主國中國。”[25]而同時代中國文人善意的揄揚,反過來又為日本漢文學的進一步繁榮推波助瀾。關于這一點,有一個非常值得關注和思考的文化現象,即日本進入明治時代之后,開始走上西化和近代化的道路,西方文學和思想被大量引進,照理說伴隨著新小說和新詩的勃興,理應衰退的傳統文學的漢詩,反而在明治時期得到了空前絕后的繁榮,號稱“漢詩全盛時代”[26](PP.355-356),尤其熱衷于學習清詩,以至當時的漢詩人們可以不讀李杜韓白的詩,但是,對于厲樊榭、黃仲則、張船山、陳碧城的詩卻是趨之若鶩。[27]
其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根據前人的研究,其中包括明治詩壇領袖森春濤(1819-1889)對清詩的鼓吹、清詩選本的流行等。*主要研究成果有揖斐高《明治漢詩の出発——森春濤試論》(《江戸文學》21號《特集·明治十年代の江戸》,1992年12月)、福井辰彥《宮崎晴瀾と張船山——明治漢詩における清詩受容の一斑》(《國語國文》812號,2002年4月)、入谷仙介《近代文學としての明治漢詩》(東京:研文出版,1989年)、神田喜一郎《日本における清詩の流行》(《神田喜一郎全集》第八卷,東京:同朋舍出版,1987年)等。關于清詩選本,前述賴山陽評點的《浙西六家詩鈔》以及監修的《清百家絕句》,皆對明治時期的清詩流行產生了很大影響。*關于選本在日本漢詩發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可以參閱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325頁。不過,張伯偉先生只提到中國選本,而未論及出自日本人之手的選本。除此之外,1871年《日清修好條規》的締結,使日本的文士有了與清朝文壇直接交流的機會,這可能是尤為重要的原因。
[1]帆足萬里.復子庾[M]//帆足萬里先生全集:上卷.大分縣速見郡日出町:帆足記念圖書館,1926.
[2]神田喜一郎.墨林閑話[M].東京:巖波書店,1977.
[3]德富豬一郎.賴山陽[M].東京:民友社,1926.
[4]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學圏[M].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5.
[5]俞樾.東瀛詩選[Z].東京:汲古書院,1981.
[6]荻生徂徠.荻生徂徠全集:第5卷[M].東京:みすず書房,1973.
[7]荻生徂徠.荻生徂徠全集:第1卷[M].東京:みすず書房,1973.
[8]五井蘭洲.非物篇[M].大阪:懷德堂·友の會,1989.
[9]賴山陽.賴山陽文集[M]//賴山陽全書:文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31.
[10]吉川幸次郎.仁斎·徂徠·宣長[M].東京:巖波書店,1980.
[11]酒井直樹.過去の聲——十八世紀日本の言説における言語の地位[M].東京:以文社,2003.
[12]賴山陽.山陽先生書后[M]//賴山陽全書:文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31.
[13]賴山陽.日本政記[M]//賴山陽全書:全集中.東京:國書刊行會,1931.
[14]譚獻.復堂日記[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5]尾藤二洲.靜寄余筆[M]//靜寄軒集.東京:株式會社ぺりかん社,1991.
[16]佐藤一郎.唐宋八家文論[M]//中國文章論.東京:研文出版,1988.
[17]賴山陽.古文典刑[M]//賴山陽全書:全集下.東京:國書刊行會,1931.
[18]市島春城.隨筆賴山陽[M].東京:クレス出版,1995.
[19]賴山陽.浙西六家詩抄[M]//賴山陽全書:全集下.東京:國書刊行會,1931.
[20]錢鐘書.談藝錄[M].北京:中華書局,1998.
[21]賴山陽.賴山陽全書:全伝[M].東京:國書刊行會,1931.
[22]袁枚.小倉山房文集[M]//袁枚全集:第二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23]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M].香港:宏智書店,出版年月不詳.
[24]山鹿素行.中朝事実[M].東京:雄山閣,1938.
[25]蔡毅.近世日本のアジアへの発信——漢文學を通して[J].南山大學アジア·太平洋研究センター報(4),2009.
[26]木下彪.明治詩話[M].東京:文中堂,1943.
[27]神田喜一郎.日本における清詩の流行[M]//神田喜一郎全集:第八卷.東京:同朋舍,1987.
ADiscussiononRaiSanyo’sKunbun
WANG Biao
(Osaka City University, Japan, 5588585)
AnUnofficialHistoryofJapan, written by Rai Sanyo, a scholar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during the late Edo period, had exerted a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the Meiji Restoration. However, it is also a controversial history book. In addition to issues such as historical data and style, the evaluation of the Japanization of Rai Sanyo’s Kanbun (Chinese classics) has also undergone a process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ries to enter the Rai Sanyo’s discourse,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other discourses such as Ogyu Sorai’s “Kain” (Chinese pronunciation) and Motoori Nobunaga’s “Kokugaku” (National Studies). Furthermo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inese writers’ names, the titles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 number of appearance inTheCollectedWorksofRaiSanyo, the auther reveals Rai Sanyo’s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analyzes his cultural practice of Kanbun writing. Finally, the author explores Chinese classics scholars’ self-awareness or self-positioning of Kanbun during the late Edo period, by investigating Rai Sanyo’s understanding of the literature of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Yuan Mei).
Rai Sanyo; the Edo period; Kanbun; self-awareness
2010-11-20
王標(1969-),男,福建福州人,文學博士,大阪市立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從事清代思想史和日本漢學史研究。
I109.4
A
1674-2338(2011)01-0063-12
(責任編輯:朱曉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