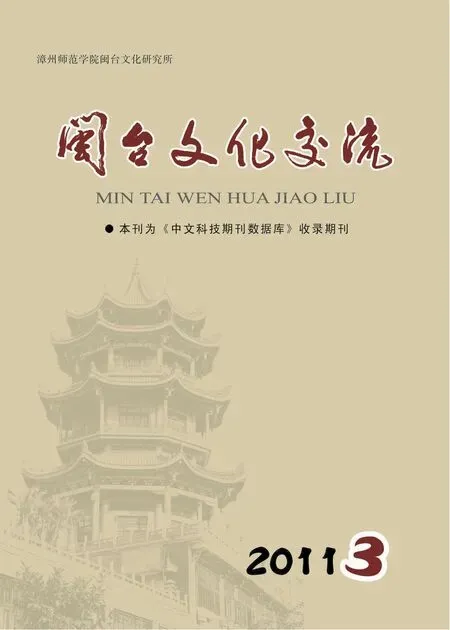福建報紙對“二·二八”事件的報道與時評——以廈門大學圖書館館藏報紙為例
劉凌斌
福建報紙對“二·二八”事件的報道與時評——以廈門大學圖書館館藏報紙為例
劉凌斌
1947年臺灣“二·二八”事件發生后,全國媒體高度關注,大陸的各大報紙均密集報道,刊發事件見聞和評論,剖析事件發生的原因,提出因應之策,留下了大量有關“二·二八”事件的重要資料,近來也日益為學術界所重視,不但海峽兩岸的學者紛紛利用當時國內重要報刊的相關報道和評論作為分析“二·二八”事件的重要資料,有的學者還搜集當時的報刊資料匯編成書,以供后人研究。[1]不過,以往學者們所運用的報刊資料多來自于上海、天津和武漢等大城市的重要報紙,如《文匯報》、《僑聲報》、《益世報》、《大公報》、《大剛報》等,對于與臺灣隔海相望的福建報刊則較少注意。這與民國時期福建報紙保存的不完整有關系。
民國時期福建的報紙數量相當多[2],但由于年代久遠,大多未能保存至今;而有幸保存下來的,大多并不完整。廈門大學圖書館館藏1945—1949年間的部分福建報紙,主要有《中央日報》福建版,福州的《福建時報》,泉州的《福建日報》和《泉州日報》,廈門的《江聲報》和《星光日報》等,保存相對完整。上述各報既有福建省政府和國民黨地方黨部創辦的官方報紙,又有民間社團和個人創辦的民營報紙,他們對于同一事件的報道和評論的偏重與取舍不盡相同,因而,具有一定代表性。本人由于學力有限,未能最大限度地搜集福建省相關的報紙資料,尤其是與官方立場相異的報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故目前只能暫時以廈門大學圖書館館藏的相關報紙為基礎資料,搜集其中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報道,進行分類并作簡要分析。
一、福建報紙對“二·二八”事件的相關報道和分析
由于閩臺特殊的歷史、地理淵源,光復初期福建人赴臺經商、任教和當公務員的甚多。“二·二八”事件消息傳來,福建各界尤為關注他們的安危,加之有大批外省人逃回福建,因此,各報刊出了不少從臺灣返閩人士的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見聞。[3]各報刊由于政治立場不一,報道也不盡相同。不過綜觀這些報道,尤其是作為國民黨官方喉舌的報紙,如國民黨福建省黨部機關報《中央日報》福建版和廈門分版、福建省政府機關報《福建時報》、國民黨泉州黨部機關報《泉州日報》等,大多將“二·二八”事件說成是“奸黨煽動”(共產黨策劃)的、不少流氓浪人參與的暴亂,著重描述外省人在臺灣被毆打、被殺害、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的情形,而對于當局的血腥鎮壓以及臺胞的傷亡提及較少。民營報紙雖不時會發表一些針砭時弊的評論文章,但大多站在官方和反共的立場,因而實際上并不能全面客觀地反映“二·二八”事件的真實情形。盡管如此,其中仍不乏較客觀的報道,為當時民眾提供了了解臺灣“二·二八”的重要窗口。
(一)對“二·二八”事件原因的探討
“二·二八”事件雖是由一起偶然事件引發,但最終卻釀成了全臺性的大規模動亂和流血沖突,各報也從不同角度進行分析。
民國時期廈門歷史最長的民營報紙《江聲報》盡管總體上支持國民黨,但敢于揭露社會黑暗,抨擊當局的腐敗。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后不久的3月8日和12日就刊發了兩篇社評,詳細分析了“二·二八”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光復以來,陳儀在臺灣實行的“嚴格而不合理”的經濟統制政策,與民爭利導致物價高漲、失業增多,“將人民生機剝盡,至人民鋌而走險”,該報引用臺灣旅滬同鄉會理事長李偉光的話說:“二·二八事件實為臺省民眾對當局不滿之總爆發”。另一方面,事變發生后,行政長官公署應變不力,處置失當,導致事態擴大。因此《江聲報》認為,陳儀為首的行政長官公署要為事變負主要責任,既不應該單單把責任推給開槍傷人的軍警,也不應把責任統統推給日本人或者中國共產黨。[4]
3月11日,福建省政府機關報《福建時報》的一篇社論,則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分析了“二·二八”事件爆發的歷史的、心理的原因,認為臺胞在日本殖民統治的五十年中處在嚴密的警察監視之下,“絕對沒有言論和行動自由,其所積蓄壓結的怨毒憤怒,從無發泄的機會”,光復以后,“驟脫重重的束縛,對于自己的前途,自不免懷過大的希望。不幸勝利后的祖國,因受內亂的影響,物價無法安定,政治也不能按理想的計劃進展,傳統的積習與戰時因物價激增所釀成的惡風,卻都從內地流入臺灣,這與日人現代化的統治技術相形之下,反而難免見拙”,因此臺胞“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久受壓制的‘情意綜’[5]失望的情緒交織而成的精神狀態,一旦受環境的刺激,集合而成群眾,其蘊積已久的怨憤的潛意識遂激發而成暴行。”[6]3月17日,《江聲報》刊登的另一篇評論也分析了光復后臺灣人的心理變化,指出:“日本投降以后,臺灣人的希望極大,祖國成為四強之一,臺灣應該是自主、進步、康樂的一省。然而,一切是一個夢,祖國因內戰糜爛得不成樣子,臺灣接收之初,貪污的廣泛,真是驚人,臺灣人就是這么由熱望中墜入深淵。”[7]顯然,兩篇評論都認為光復以來一年多的社會現實讓原先對祖國抱有很大希望的臺胞感到無比失望,形成巨大的心理落差,這是“二·二八”事件爆發的重要原因。
著名華僑胡文虎創辦的星系報紙之一《星光日報》經常發表支持民主運動、批評國民黨當局的文章,政治立場比較進步。其3月8日的一篇短評《臺北暴動前因后果》認為,“二·二八”事件“斷非單純一種專賣走私所引起而系久經醞釀之政治與人民之隔閡,藉此專賣事件而導火耳”,“光復后人民希望清廉光明之治,當然極殷,而接收之官員中之行動失檢,使政府與人民脫節”,文章指出臺民對外省公務員的官僚習氣和貪污橫行的不滿是引發此次事變的主要原因。[8]3月11日社論《臺灣民變正論》更是直言:“臺灣此次民變,無疑義地完全是陳儀的黑暗專制的統治所造成”,并綜合分析了“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原因。[9]《江聲報》的社論《臺灣善后處理中》則在客觀評價日據時期實行的各項殖民政策,并在將其與陳儀治臺政策進行對比的基礎上,分析了陳儀治臺“雖政治專制并不如日人之甚,經濟統制亦不至更嚴于日本”的情況下,卻釀成“二·二八”事件這一歷史悲劇的原因。[10]
既有的研究表明,“二·二八”事件爆發的背景極其復雜,學者們大多認為事件的發生與臺灣當時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面臨的深刻危機大有關系,主要原因是陳儀領導的行政長官公署不當的各項政策所致。[11]綜合福建報刊對“二·二八”事件爆發原因的分析,雖然各有所側重,但涉及到陳儀的治臺政策、經濟統制、貪污問題、省籍矛盾、當局的應變措施以及社會心理等諸多層面,應該說,福建報刊的這些分析文章是比較全面、客觀和深刻的,觸及事情的本質,切中了要害,為當時人們提供了一個深入了解和理性思考“二·二八”事件的方向。
(二)對陳儀個人及其治臺政策的評價
由于陳儀主持閩政有得有失,毀譽參半,[12]福建各界對其相當熟悉,因此相較全國其他地方也就更為關注陳儀在臺灣的所作所為。“二·二八”事件爆發以后,福建報刊紛紛刊載文章,對陳儀治臺的功過得失進行評價,這些評論文章在對陳儀的治臺政策,如經濟統制、政治上的專制予以猛烈批判,并認為陳儀應該為“二·二八”事件負責;同時又大都肯定陳儀的政治抱負、個人能力,贊賞其正直、廉潔的作風。
《江聲報》的社評對陳儀的評價較為客觀,文中贊賞陳儀“無疑是中國少見有能力的地方政治家”,指出他主政福建七年,“政治方面成功,經濟方面則失敗”。但陳儀卻將主閩時的經濟政策又搬到臺灣,醉心統制經濟,終于釀成“二·二八”事件。[13]該報的另一篇文章則分析道:“陳儀在臺灣的作風就他個人來說是進步的,但效果卻是失敗的,原因當然很多,主要的是他自己也還沒有通盤的計劃,確定的方針,不折不扣的實行。”[14]
《福建時報》則刊發專文《陳儀究竟是怎樣的人物》,對陳儀作了全面的評價,認為陳儀不像上海許多報紙宣傳的那樣暴虐,肯定他是一位“正直而嚴肅的長者”、“廉潔無私剛直不阿的不可多得的人物”,還分析了陳儀治臺失敗的癥結所在:“無論陳氏如何的律己已嚴,然而他所用的人卻大不行。無論陳氏如何正直無私,然而他倔強固執的個性卻毀壞了一切。”作者認為陳儀用人失當,過于倔強、固執的個性和過于自信的政治作風造成了他的失敗。對于陳儀繼主政福建之后在臺灣又迎來了“一個失敗的悲劇”,作者感嘆:“這是一個很冤枉的老人”,“這又是一個很值得惋惜的老人。他的剛直的個性里僅僅只缺少了些德謨克拉西(即英文“民主”一詞的音譯)的成份,但由于這個不治之癥,他不能與一個作為新中國的建設者有緣了。”[15]
《福建日報》系泉州商會辦的大型日報,政治上偏向國民黨當局,發表的經濟方面的社論或評論較多,但也注意維護商人利益,經常刊登一些反映商人情緒的報道和文章,也曾發表過一些抨擊時弊的評論。5月15日發表社論,認為陳儀該為“二·二八”事件負責,也該受處分,但也指出“臺灣治得不好是真的,但一般情形總比其他省份好也是真的”,因此“讓陳儀單獨負責是不公的。”文中還肯定了陳儀的抱負和努力,對他“敢作敢為固執從事的精神和風度”甚感欽佩,為他的結局而嘆息:“這樣一位有政治抱負的人物,也難免失敗,溺斃在中國政治的陷阱中,著實很慘。”“他主臺政,不但有他一貫的抱負,也確實費了力,想做事的。聽說,這位老人家連午飯都是在辦公處吃,沒有回家休息的,而今卻落得這樣一個下場。這豈是陳儀的不幸?倒真是中國的不幸。在陳儀能夠卸此任勞任怨的重職,一聲‘謝謝’而去,有何不幸,真正不幸的,恐怕是中國,是臺胞。”“中國官場的秘訣是‘多做多罵、少做少罵、不做不罵’,陳氏應是屬于‘多做多罵’的人物,所以他到處挨罵。但是這種人到底比少做,不做的‘無為而治’的政治家更值得佩服,更偉大。也許他離開臺灣以后,臺灣人會像福建人一樣蠻戀他哩!”[16]
由此可見,福建媒體通過對陳儀治閩和治臺政策的對比分析,并結合陳儀主閩的政策得失和帶給福建各界的觀感來評價陳儀在治臺期間的功過,既指出了陳儀治臺政策的若干嚴重缺失,又肯定了陳儀的抱負、能力和品德,而不似當時大陸的某些政客和媒體那樣,把陳儀批評得一無是處,必欲除之而后快。[17]因此,福建媒體對陳儀的個人及其治臺政策的評價是較為客觀和公正的。
(三)關于“二·二八”事件的教訓和反思
關于“二·二八”事件的教訓和反思,這也成為當時福建媒體關注的另一個焦點。各報紛紛發表評論,呼吁國民黨政府和全國人民從“二·二八”事件中吸取教訓,要好好反省,避免類似悲劇重新上演,希望內地人民能給予臺胞同情和理解,化解誤會,冰釋前嫌,融洽相處。
《江聲報》的評論指出,“二·二八”事件不只是臺灣政治的失敗,也是整個中國的失敗,每個中國人在臺灣同胞之前都應加以自省。[18]
泉州《福建日報》的社論詳細分析了臺灣的重要地位以及對中國的重要戰略意義,論證了臺灣與祖國的關系,文中寫道:“臺灣不能離開中國,正如孤兒依賴慈母,中國不能離開臺灣,也正如母愛子乃出乎人之本性”;認為要從“二·二八”事件中吸取教訓,“要糾正臺胞的心理,必須從教育方面入手,不但徒教他們懂得國語就夠,還要以寬大仁愛的教育精神,向臺胞積極的啟示,讓他們都能興奮奔向祖國的懷抱,而政治的弊病也要及時改正,準備與民更始,使民樂于就范。”[19]該報刊登的另一篇評論文章則認為:我們對于“二·二八”事件采取的正確態度,應該是“警惕、反省,從中獲得一個教訓,而不是仇恨”;這次事件的嚴重性,“并不在于事件的發生,亦不在于這事件的如何解決、結束。而是在于今后臺人與國人之間的如何相處,因為解決、結束不過是表面的、消極的,如何使臺人與國人之間的前嫌冰釋、相然無間,那不是靠一紙命令,一個諾言所能收效,而是要看我們今后用何種態度以相處來決定的。”文章最后指出,“臺灣雖然是我們的同胞,但是他們淪亡異族之手五十一年,一切生活、文化與思想,實在有許多與我們不同,與生活文化不同的人相處,極易發生誤會,滋生隔膜。唯了解與同情,可以化解誤會與拆開隔膜。”因此,“我們應該用理智克服感情,用了解培養容忍”,來逐漸促進臺人與國人之間的融洽相處。[20]
(四)對“二·二八”事件的善后處理及日后治臺方針的建議
關于“二·二八”事件的善后處理,福建各報紛紛建議中央當局盡快追究責任,將陳儀撤職查辦,但同時要應本著寬大的原則處理此次事件。
對于日后的治臺方針,福建各報提出了不少具體的建議。《江聲報》的《臺變我觀》一文提出七點治臺方針:一是保持寬大的態度,徹底處置流氓及其武力;二是將公有土地分配給貧農以合作方式經營;三是由政府收置地主私有土地,實行徹底的平均地權;四是早日實行縣、市長民選;五是保持和發展日據時代的公營經濟事業;六是征選國內優良教師以教育臺胞;七是健全省級行政。[21]
《福建時報》在《今后怎樣治理臺灣》的社論中則提出今后治理臺灣應特別注意的有以下四點:第一,重視培養臺民的內向心力,取消一切特殊化制度,提前完成臺民自治;第二,消除臺民與內地人民的歧視;第三,推行中國本位的教育和公民訓練,徹底肅清日本教育的遺毒;第四,加強臺灣與整個國家經濟的聯系。[22]
泉州《福建日報》專門就這一問題發表了兩篇社論。4月24日的社論《今后的臺灣》,對今后的治臺方針提出了具體的建議。社論認為文人出身的魏道明應該以“寬猛互濟”的方法來治臺,才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蓋因“非猛不足以壓服一般暴亂成性的浪民,非寬不足以撫慰大多都善良而熱心祖國的臺胞”,建議地方當局今后應重視“安定民生”和“努力教育”兩方面的工作。[23]5月15日的社論《送魏主席往臺》則認為,“臺灣要治好,不是換了陳儀就會好的,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否擺脫一切因襲的官場風氣”,“要征集一大批好的教育人才、公務員、技術人員,甚至軍隊到臺灣去,配合臺胞來干一番。才有希望。”同時,更寄望于新任臺灣省政府主席魏道明:首先,“對此次事變善后,應本寬大為懷,賞罰分明之本旨,慎重處理,其已處分,而經人民控訴確系冤枉好人者,應予寬免。”其次,“應該更多注重教育”,作者覺得治臺的失敗在教育,“全省沒有幾位中學校長是足以為人師表的,難怪無校不潮,小學生看見‘阿山’都鄙視”;“我們缺乏工農業的一流人才無可怪,倘然,連一些優秀的教育人才也羅致不到,那才真是中國的恥辱,丟盡全民族的‘面子’。只好請日本再來了。”社論最后指出:“對魏氏我們未敢為賀,我們只希望他是司法家,能善于處理事變。他又是文人,能注意教育文化,則臺灣即使不會好,也可望不再變壞。”[24]
綜合上述福建各報對日后治臺方針的建議,主要包括幾個方面:政治上,改革不合理的省政,盡快實行縣市長民選,重用本省人;經濟上,廢除經濟統制政策,實行土地改革,重視安定民生,促進經濟發展,加強臺灣與內地的經濟聯系;文化教育上,加強對臺胞的教育,著重培養其祖國意識,消除臺灣人與內地人的隔閡等。這些建議,是針對陳儀治臺的弊病所提出的良藥,是極富遠見卓識的,體現了福建同胞對臺灣人民的殷切關懷和對臺灣局勢發展的美好期許,但在當時全國內戰的形勢下,除了改革臺灣省政、廢除經濟統制之外,上述建議大多未被當時腐朽的國民黨當局所采納。
二、“二·二八”事件之后,福建報紙對臺灣時局的評論
在全國各界和強大的民意壓力下,1947年4月,陳儀辭去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以示對“二·二八”事件負責。5月,魏道明受命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他在臺灣實行軍政分治,改組成立臺灣省政府;發展民營經濟,加大土改力度;寬釋“二·二八”事件人犯,吸納臺籍精英,緩和省籍矛盾。這一系列省政改革舉措,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廣大臺胞的訴求,得到了他們的支持與擁護,有助于臺灣社會恢復常態,穩定民心,使得臺灣的政局暫時穩定下來,重建工作在曲折中緩慢前行。[25]但隨著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節節敗退,國民黨政權在大陸自身難保的情況下,根本無力支持臺灣的發展,大陸的通貨膨脹波及到臺灣,加速物價飛漲,加上地方官員的貪腐問題依舊嚴重,臺灣的政治經濟形勢再度陷入了混亂,
福建各報繼續刊文揭露當時臺灣地方官員的貪污腐敗,報道臺灣經濟形勢惡化、通貨膨脹嚴重、物價飛漲、民生日益維艱的狀況。《福建日報》的評論就指出:“生活重壓下,環境特殊下,談效率,談計劃,似乎每個人都心頭黯然”,“今日臺灣是一片可怕的緘默。”[26]有的報道則重點關注由光復以后的臺灣人與外省人之間的隔閡,文中指出,外省人來到臺灣,一切的貪污、腐敗、無效率、糊涂、不遵守法紀和公共秩序等傳統的惡劣作法,都搬過海峽而來,引發了臺灣人強烈的不滿,在他們心目中,“中國人”三個字已經成為“貪婪無能”的代名詞。作者為此憂心忡忡:“‘中國人’與‘臺灣人’,是一個值得重視的裂痕,是需要迅速彌補起來啊。”[27]
1948年11、12月間,《江聲報》刊登了系列報道《臺灣行》,通過記者赴臺參觀博覽會及在臺灣各地參訪的所見所聞,深刻揭露了當時臺灣政治、經濟和社會上存在著的種種問題。系列報道涉及訪臺者在臺灣的吃住問題、貨幣兌換的不便,臺灣的物價飛漲、經濟狀況的惡化,臺灣人與外省人的隔閡,臺灣民眾對時局的不滿,日本統治對臺灣的影響,官方的新聞管制,政府官員的貪污腐化,臺灣婦女的地位和娼妓問題等方方面面,客觀的反映了當時臺灣社會的真實情況和臺灣人民生活的困苦。作者擔憂臺灣的前途,預感臺灣將要面臨更大的危機:“這里,陰霾處處,籠罩著這個不安的褪了色的島嶼,冷銳的風吹動我的寂寞的樓屋,我念著‘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詩句,知道更大的暴風雨就要來了,憂慮而且戰栗!”[28]
另一方面,“二·二八”事件以后,在國際上和極少數臺灣人中出現了一股尋求所謂“國際托管臺灣”、“臺灣自決”、“臺灣獨立”的聲音,妄圖將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此舉引起了國內各界的強烈不滿,以《江聲報》為代表的福建媒體也對這些分裂祖國的圖謀予以深刻地揭露和嚴厲地批評。早在1947年4月,《江聲報》的社論就指出,要警惕美國一些報章將臺灣“移交聯合國托管”的言論。[29]同年11月8日,針對美國人經營的菲律賓報紙和國內少數臺灣人主張的“以民族自決方式確定臺灣的政治地位”,“臺灣舉行公民投票,以確定臺灣自主,或由中國統治”的言論,《江聲報》專門刊發社論,剖析了臺灣的戰略地位,“臺灣自決”言論產生的背景,并對此予以駁斥和批判。社論認為,“臺灣曾鬧過‘二·二八’事件,我們不否認臺灣人民之痛苦,”但這是當政者的問題,不是國家不好,“當政者不好可以改革,大家同心改革,正如當家的不好,可以起家庭革命,總不好當家的不好,就不認祖宗,向外面‘賣身投靠’;鄰居也不好教唆利誘,叫‘賣到我這里來’。臺灣就像賣去贖回的孩子,老家里窮苦混亂,如合眾社五日上海電舉臺灣現在之痛苦,就有人教唆利誘這孩子了”;呼吁臺灣同胞應該與全國人民共同警惕某些國家分裂中國的陰謀。[30]1948年8月,該報的另一篇社論則針對在日本的“主張臺灣獨立”的地下組織提出的五點主張進行批判,也檢討了光復后中國政府在治臺方針上的種種失誤及其帶給臺灣人民的苦難,還深刻揭露了美、日等國扶持“臺獨”運動的險惡用心和巨大陰謀。社論最后希望,政府要好好反省,臺灣可以爭取自治,但不必自棄,更不應脫離中國,“對此陰謀,既授人以隙了,應速自弭:做哥哥的深自反省,做弟弟的可盡在家里吵,爭自治,切莫輕離家門給拐子拐了去!臺灣是中國依建國大綱唯一夠資格自治的省,可跑在哥哥的前頭,做全家有力的一房,很不必自棄。”[31]從上述評論的遣詞造句來看,《江聲報》用家人關系比喻臺灣與大陸的關系,用兄弟感情比喻兩岸同胞的親情,形象生動地描繪出臺灣之于祖國的重要性,頗具說服力,可以算是福建媒體的特色之一。福建媒體語重心長地提醒作為家長的國民黨當局要好好反省治臺政策,呼吁同為中華大家庭一份子的臺灣同胞警惕“臺獨”言論和分裂中國的陰謀,切莫“輕離家門”鬧“獨立”,字里行間流露出兩岸一家的民族情懷以及閩臺兩地血濃于水的同胞親情,讀來令人無限深思。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福建媒體,不但對臺灣之于中國的重要戰略地位有著清醒地認識,也熱衷于呼吁兩省攜手推動閩臺關系的發展。1947年,《福建時報》的一篇社論就專門探討了光復臺灣對于鞏固東南海防和發展閩臺關系的重要戰略意義,并希望福建“全省人士重視臺灣,效法臺灣,追隨臺灣,把福建的交通建設起來,福建的礦產開發起來,福建的海港建筑起來,繁榮福建,足以增加臺灣的力量,光復臺灣,足以鞏固福建的海防”;最后呼吁,“福建的同胞們,你們是臺灣的拓荒者,你們應該格外出力保衛臺灣,繁榮臺灣,臺灣的繁榮便是鞏固福建的門戶,也便是鞏固東南的海防。”[32]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當我們重溫這段歷史之時,再來細細品味當時福建媒體對于發展閩臺關系,共同促進閩臺繁榮的熱誠呼吁,仍不免令人感概萬千。
三、結語
綜上所述,大量見諸福建報端的有關“二·二八”事件及事件后臺灣時局的報道和評論,反映了福建各界對臺灣時局的密切關注以及閩臺人民之間真摯的同胞情誼。且由于閩臺兩省同根同文,風俗民情頗多相似之處,閩臺關系源遠流長,加之當時兩地各方面的交流合作又十分密切,福建報刊對“二·二八”事件和臺灣時局的分析與評論多半能鞭辟入里,容易觸及問題的癥結所在,為后人研究“二·二八”事件提供了豐富和寶貴的資料。
注釋:
[1]李祖基編:《“二·二八”事件報刊資料匯編》,臺灣:海峽學術出版社,2007年版。
[2]據《福建省志·新聞志》(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記載:根據現有資料統計,從民國元年(1912年)到1949年國民黨統治在福建垮臺為止的30多年間,福建先后創辦報紙共824種。參見福建省情資料庫——地方志之窗網站,網址:http://www. 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155&index=40&。
[3]《中央日報》福建版對“二·二八”事件進行了大量的報道,其中大多是轉載自中央社的消息,還刊發了記者采寫的事件經過與見聞,如《臺灣事變目擊記》(3與15日、16日)、《臺灣事變始末,中央社記者親歷驚險》(3月18日)等。福建其他報刊的報道也不少,如《淡水歸客談騷亂經過》(《福建時報》,1947年3月8日)、《由臺來廈難民口中詳述臺灣事變真相》(《江聲報》,1947年3月9日)、《訪問臺灣歸來人》(《福建時報》,1947年3月13日),《臺灣暴動的真相》——記二·二八事件》(《泉州日報》,3月26日至29日,3月31日)、《歷史的慘劇——臺灣騷亂中拾錄》(《泉州日報》,4月2日至4日)。
[4]《社評:臺灣“二·二八”事件》,廈門《江聲報》,1947年3月8日;《社評:臺灣事變的發展》,《江聲報》,1947年3月12日。
[5]“情意綜”,也稱為“情意結”(COMPLEX),即對某人某事不可抗拒的情感;在現代心理學中指:一群重要的潛意識組合,或是某種隱藏在個人的神秘的心理狀態中、無意識而又強烈的沖動。
[6]《社論:向臺胞懇切呼吁》,福州《福建時報》,1947年3月11日。
[7]非英:《臺變我觀》,廈門《江聲報》,1947年3月17日。[8]《臺北暴動前因后果》,廈門《星光日報》,1947年3月8日。
[9]《社論:臺灣民變正論》,廈門《星光日報》,1947年3月11日。
[10]《社評:臺灣善后處理中》,廈門《江聲報》,1947年4月12日。
[11]參見杜繼東:《臺灣“二·二八”事件研究綜述》,《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韓文琦:《臺灣“二·二八”事件研究述評——紀念“二·二八”六十周年》,《南京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
[12]1934年2月至1941年9月,陳儀擔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長達七年半之久,在福建采取了一些比較開明進步的措施,如鏟除軍閥割據、土匪禍患,革除官場弊病;興辦教育,重視人才,發展文化事業;積極備戰,抗擊日偽軍等,對福建抗戰和全省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起到某些積極作用;但他實行經濟統制,大搞糧食“公沽”,導致米荒嚴重,民不聊生。參見陳能南:《陳儀主閩期間功過述評》,《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2期。
[13]《社評:臺灣二·二八事件》,廈門《江聲報》,1947年3月8日。
[14]非英:《臺變我觀》,廈門《江聲報》,1947年3月17日。
[15]伊人:《陳儀究竟是怎樣的人物》,福州《福建時報》,1947年3月10日。
[16]《社論:送魏主席往臺》,泉州《福建日報》,1947年5月15日。
[17]國民黨CC系(由陳家兄弟陳果夫和陳立夫兄弟領導的)對陳儀的臺灣特殊化政策早已不滿,幾番攻擊未見效,“二·二八”事件發生后,CC系政客眼見陳儀在臺灣闖下大禍,總算找到發難的耙子,必欲去陳儀而后快。一些國民黨CC系控制的報紙如《正言報》、《新中華報》等紛紛發表文章,痛批陳儀在臺灣搞特殊化政策,直指長官公署的劣政導致了臺變,將“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歸咎于陳儀一人,認為陳儀是首惡必辦,應承擔全面責任,向天下謝罪;并建議南京國民政府槍決陳儀,以平臺胞之憤。參見褚靜濤:《全國媒體對臺灣“二·二八”事件的反應》,《南京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
[18]非英:《臺變我觀》,廈門《江聲報》,1947年3月17日。
[19]《社論:白部長兩句話》,泉州《福建日報》,1947年3月23日。
[20]李于右:《我對于臺灣事件的看法》,泉州《福建日報》,1947年3月26日;此文同時刊登于《中央日報》廈門分版,1947年3月27日,3月28日。
[21]非英:《臺變我觀》,廈門《江聲報》,1947年3月17日。
[22]《社論:今后怎樣治理臺灣》,福州《福建時報》,1947年4月25日。
[23]《社論:今后的臺灣》,泉州《福建日報》,1947年4月24日。
[24]《社論:送魏主席往臺》,泉州《福建日報》,1947年5月15日。
[25]參見褚靜濤:《魏道明與二二八事件善后》,《現代臺灣研究》,2007年第5期。
[26]《看今日臺灣,到處是可怕的緘默!》,泉州《福建日報》,1947年8月30日、31日。
[27]柯秋:《中國人與臺灣人,一個值得重視的裂痕》,泉州《福建日報》,1948年2月23日。
[28]伍郎:《臺灣行》,系列報道,廈門《江聲報》,1948年11月1日、12日、19日、20日、21日、28日、29日,12月3日、4日。
[29]《社論:臺灣善后處理中》,廈門《江聲報》,1947年4月12日。
[30]《社評:對琉球臺灣的陰謀,“司馬昭之心”希望不是全美國人的》,廈門《江聲報》,1947年11月8日。
[31]《社評:對臺灣的陰謀及授人以隙之由來》,廈門《江聲報》,1948年8月26日。
[32]《社論:臺灣光復與東南海防》,福州《福建時報》,1947年10月26日。
責編:蔡惠茹
作者單位:(福建省社科院現代臺灣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