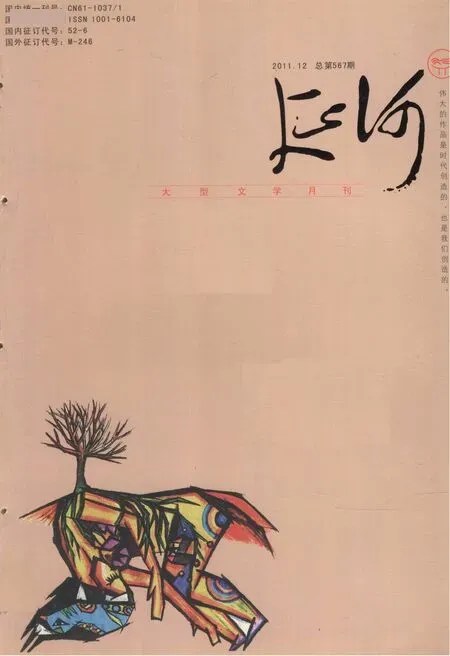得一個真字
第一次見到宗奇先生,是在古城西安的一次朋友聚會上。他告訴我,他是郃陽人,因郃字生僻,現改稱合陽,音一樣,字不同。見我仍疑惑,他又補充一句,就是詩經中產生了“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的那個合陽。立刻,我的記憶生動起來,溫馨起來。這記憶不為今日的合陽,而是因為在《詩經》中名列榜首的《關關雎鳩》。
我最早的關于淑女與君子的形象,就是來自于這首詩。而且,我總是遺憾,這淑女的溫柔與君子的儒雅,已沉入歷史的滄桑而不可覓回。宗奇又告訴我:其實這首詩講述的是周文王與他的愛妃太姒的故事。太姒的家就在古稱“莘國”的合陽,她被周文王看中后,入室一年,就生下了鑄造華夏煌煌史章的周武王。
如果把周文王稱作君子,那么在中國歷史中夠得上稱君子的人,實在是少之又少。幸虧在當今之世,最時髦的稱謂是“老板。”對當官的,做買賣的,甚至博士生稱他的導師,都叫老板。
可喜的是,居大不易的長安城中,沒有人稱宗奇先生為“老板。”盡管他半老且古板,仍不能獲得“老板”的職稱,何其樂乎?惟其樂也,宗奇先生才有可能成為我的朋友,在一起把盞而論“發乎情,止乎自娛”的文事。
一說到文事,仿佛就高雅,其實不然。蓋因為文之人,來路各不相同。有一肚皮不合時宜的高蹈尊者,有罵盡世相的自戀尊者,有把敲門磚的文章做到極致的聰明尊者,有皓首窮經的孤獨尊者……紛擾文壇,不一而是。那么,宗奇先生是何等樣的一個尊者呢?若讓鄙人下一判語,則是:宗奇先生根本就不是一個尊者。他的木訥,直如深山古寺的頭陀呢!
平直如拙,木訥近愚。這應該是君子的世相吧,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中國的第一個大君子周文王是宗奇故鄉合陽的女婿,僅此一點,世代的合陽人都會驕傲,也都會仿效。
宗奇先生工作之余,喜歡寫一點散文。讀他的散文,我像是聽到黃河之洲上的關關鳩鳴,世間所有叫聲好聽的鳥,據我考證,決沒有哪一只住過音樂學院。什么叫天籟?凡是學堂里學不到的東西,從生命的本然狀態中流露出來的東西,就叫天籟。
宗奇先生的散文,便有著天籟之音。
他的為數不多的散文,大致可分四類:一是談故鄉的人事,二是談親情,三是記述自己生活的經歷,四是對自然風物的觀察與欣賞。我說這些散文近似天籟,主要理由在于:
一、不矯情。無病呻吟者,故弄玄虛者,虛張聲勢者,狗扯羊腸者,在文人中不算太少。年輕時,我下鄉當知識青年,一位公社書記來我們隊動員搶收搶種,這是三分鐘就能說完的事,他偏偏講了大半夜尚未上題。他從亞非拉講到蘇聯修正主義,又從蘇修講到反修英雄恩維爾、霍查。并斷言,這位恩維爾是恩格斯的孫子,而且,為了和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確立戰友關系,這位恩格斯的孫子、馬克思的侄孫從此不喝咖啡,改成喝茶了。所以,他干脆就把名字改叫恩維爾?喝茶。他在臺上講得唾沫橫飛,臺下的社員聽眾漸漸溜走,最后只剩下三個人,一個是隊長,一個是民兵連長,還有一個是沒有任何官職的社員。公社書記對這位社員尤其看重,感動地問他“你為何喜歡聽我的形勢報告?”社員告訴他,不是喜歡聽,而是因為書記屁股底下坐著的板凳是他家里的,他是耐著性子在等板凳呢。
這位公社書記的大而無當的報告,同我們一些文人的大作,有異曲同工之妙。宗奇先生是有條件在大庭廣眾下作報告的人,我沒有聽過他的報告,但從他寫出的散文中,我敢斷言,他的報告一定是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說事兒丁是丁,卯是卯,說完就散會。
對于寫作者,把文章寫得很機智,不難,但把文章寫得質樸動人,卻是很難的事。這里頭首要的因素,是感情的真實。作為文人,宗奇先生可能欠缺許多看家本領,他惟一不缺的,大概就是這感情的真實了。
二、樸拙。人們常把這個詞用來形容人的性格,其實,它應該是一種境界。
宗奇先生的感情與文字,都是一色的樸拙。在他的文章中,你找不到一個華麗的詞藻,因此,你不能用豐瞻的文采來形容他。打個比方,他的語言,一如遠古的陶罐,而非明清的精瓷。平凹兄好陶,他的“上書房”中,有許多漢唐以前的陶器,我亦存此一點愛好。三天前在西安,我還與平凹兄探討這一問題,他說:“我不大喜歡瓷器,是因為他們太精美了。太精美的東西,近妖,近偽。陶不一樣,它可以讓我感受到泥土的存在。”這席話借而論之,亦可用之于宗奇的散文。
我有一位商界朋友,人很好,但長得太精明,每次談生意,客戶一看他的尊容,頓時就十二分的警惕,許多單買賣因此而告吹。我的朋友為此倍感苦惱,恨不能花巨款去做一次整容,借助科技手段創造出一副老實的面孔來。
宗奇先生卻沒有這個煩惱,他的長相,同他的文章一樣,古拙而樸實,一看就產生信任。
我想,當年的周文王之所以與太姒一見鐘情,大概就因為太姒不但水靈、漂亮,而且整個的精神氣象,讓人感到可靠,不是近妖、近偽那種人。
近妖近偽的人,一般都矯情;古拙樸實的人,行文都自然,這是規律。宗奇先生每每問我:“你看我這樣寫有何不妥?”我真的不好回答,這就像問“你覺得陜西的鍋盔是好吃食兒嗎”一樣。對于我,這是人間的真味,好吃。但在吃慣了燕窩魚翅的人中,恐怕就會嫌這鍋盔太尋常,難入廟堂。
在宗奇先生的散文中,有一篇《打井》,記述了他為家鄉打一口水井的故事。他的家在合陽縣金水河畔的嶺坎上,世代缺水。當地的民謠是“寧給一個饃,不給一口水”,可見其用水之難。宗奇到省城后,找各方面的執事者幫助,終于在他們村頭打了一口720米深的機井,解決了四個村人的吃水和2000畝地的澆灌。乍一看這篇文章,我便驚詫,一口井打到720米深,這在我居住的江南不可想象。我就想,在陜西的黃土高坡上,只有在七百米深的地心里,才能獲得甘泉,這是一種生命啟示。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既惜水如油,轉而為文,必定也就惜墨如金了。
宗奇先生藐拙氣古,為文如作事,愿意舍輕就重,從地心汲取甘泉,這本身就是君子之風。前面已講過,當今之世,老板多而君子少。宗奇先生似乎并不思考這樣的問題。某日,他請我為他題寫齋名,我問名何?他說“遲悟齋”。我一聽笑了,心想這人有后福。因為大凡早慧者,夭折者多,僥幸存活,必晚景凄涼。而遲悟之人,說雅一點,是大智若愚;俗一點,類似于江南的呆頭鵝,吃得、睡得,閑也閑得,虧也吃得。平居待人,守一個善字;率意為文,得一個真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