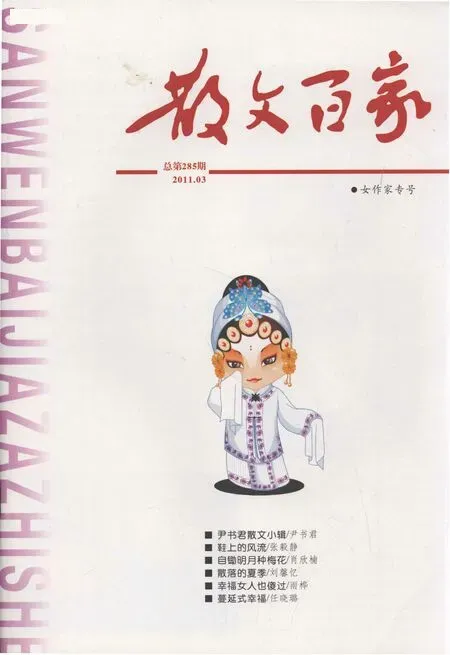寫作是一盞燈(創作談)
●尹書君
寫作是一盞燈(創作談)
●尹書君
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我會走上寫作的道路,就像從來沒想過我會遭遇車禍導致高位截癱,致使不能再行走終生“囚”在床上一樣,太多太多意外的背后,讓我在得與失中感悟命運之手“掠劫”過的五味人生。
如果說是一輛瘋狂的逆行轎車在我新婚不久將我瞬間打入人生的萬丈深淵,那么文字、寫作就是一盞燈,照亮并指引傷痕累累的我摸爬著慢慢走出深淵,重新尋回生命的軌跡和存活下去的力量。而且以后的日子里有了這盞燈的相伴,心靈深處多了些許光亮和溫暖。
不堪回首的黑暗深淵啊,愛情、青春和人生都失去蔥郁的顏色,至今想起來仍不寒而栗。多發粉碎性骨折的身軀在幾次手術修補后大傷元氣,奄奄一息的生命只能靠輸血、輸液及昂貴的白蛋白維持;脊髓嚴重損傷,完全喪失處理能力,僅僅剩下頭和雙手能夠活動,病床上一個翻身的動作都需有人幫助完成,而且伴隨截癱后的大小便失禁,尿布、尿墊成了日夜不離的必需品;右膝的開放性傷口幾經處理,反復地發炎、潰爛、清創,總也不見好;肺部感染,不停地霧化咳痰,差一點把我送往另一個世界;每天下午都要高燒,醫術在我面前好像束手無策……在這樣的狀態下,歸屬于生命的靈魂似被旋入龍卷風中,一圈一圈地掃過死神之門,一度飄搖不定,踉踉蹌蹌。
所有的語言、所有的安慰、所有的思想意念都失去了原本的意義,蒼白下的我變得異常沉默。我不想把悲痛帶給他人,隨聲附和來人的探視,學會了血淚往肚子里咽。更多的時候,是用沉默拒絕著一切,甚至想忘卻自己是誰。能怎樣?還能怎樣?誰能讓我站起來啊!勸人是一回事,自己真正做到又是一回事。我無論如何努力,仍然沒有“堅強”到對我自己的身體慘狀無動于衷。心情的反復、病痛的折磨、積極和消極的錯綜交織我常常無力擺脫。
有一天,為我重生奔波不停的哥哥拿來一個日記本、一支圓珠筆,語調平和地對我說:“筆和本先放在這里,實在憋屈得受不了了,可以寫出來。怨誰、恨誰、甚至罵誰都由你自己說了算。”一直忘不了哥哥說這些話時的表情,是艱難無力后強裝出來的輕松。哥哥是個作家,雖然瘦弱,卻有著頑強的意志,他是全家的支柱,撐起每個人的信心。
不管怎樣,多日后我真的對著日記本寫下一些文字時,在一字一句中梳理內心的感受時,無論現實狀況怎樣地糟糕,卻和文字似乎有了些許感應。那時,再加上親朋好友、認識的不認識的好心人對我無時無刻地呵護和關注,一個個觸動我心靈的人和事,用筆“說話”的同時,我仿佛又“活”過來了。
在這之前,我雖然沒有從事過寫作,但是無休止的劫難激發出連自己事后都不相信的思想火花和生命感悟。比如“不發燒真好”、“笑,原來也這么難”、“喊痛也是一種幸福”、“苦,要大口大口地吞咽;甜,才是需要慢慢品嘗的”、“不是我面對災難選擇堅強,而是在災難面前我別無選擇”、“我屬蛇,此時我寧愿是一條真蛇,每蛻一層皮就能獲得一次新生”等等,都是當時生命狀態的自然流露和迸發。
寫作,對我來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只能躺著,一只手把本子舉在胸前,一只手拿著筆在懸著的本子上寫。眼睛專注地盯著本子,寫幾行字眼睛就累得發花流淚,拿著筆和本的手就開始顫抖。不知為什么,僅有知覺的肩部麻痛難忍,如影隨形的痛,常常攪得我無心寫作。但我不想讓“慘兮兮”來裝扮人生,寫不成東西,就大聲誦讀,咬牙向疼痛宣戰。我寫作的事情被《牛城晚報》記者知曉后,在其周末版頭版頭條推出重頭報道《“截癱新娘”用日記書寫堅強》,許多媒體給予關注,網上也有很多的轉載。
雖然生命仍在反復掙扎中徘徊,但我卻沒有消沉下去。
在醫院的病榻上一手拿本、一手執筆,真正開始寫成形的文字,是我細讀過一些講述重病患者的勵志書籍之后。
讀的第一本勵志書籍是《搖著輪椅上北大》,書中主人公郭暉是一個小學未畢業的重殘人,完全依靠自學成為北京大學的博士生,在這座名校的百年歷史上還從未有過。這本書讓我明白:有和我一樣悲慘的人,她在我視線外的某一處,不但戰勝了病魔、戰勝了自己,還達到了健康人難以企及的高峰。心靈被震撼后,寫起了讀后感,數天后把寫好的幾頁紙拿給哥哥看,他遲疑了一下,語重心長地給出這樣的評語:“書你是認真看了,但拿書評的標準來看你的這篇讀后感,還遠沒達到標準。”然后,他以自己多年寫作的方法體會給我講述了一些寫作知識。
因為媒體的大力關注,社會上掀起拯救“截癱新娘”的愛心熱潮,到醫院看望我的好心人一直沒有間斷。在我幾度擦肩死神再次因感染骨髓炎而面臨高位截肢的生命節點時,北京志愿者高偉受“中國青年年度勵志人物”張云成和張云鵬所托,專程到河北邢臺礦業集團總醫院勉勵我堅強、做“人生的英雄”,并帶來云成的勵志著作《假如我能行走三天》。云成、云鵬都是重病肌無力患者,他們用嘴叼筆簽名的書籍和創作的國畫作品送到我病床前的那一刻,我感覺他們離我是那么近。用心讀完《假如我能行走三天》,以《咬緊牙,做人生的英雄》為題,寫就一篇自強隨筆。哥看后大加肯定,未改一字推薦給編輯,竟第一次變成鉛字,發表在《牛城晚報》“書林”版的頭條。后來,《邢臺日報》、《中國建材報》、《大眾閱讀報》、《河北日報》、《河北工人報》、《家庭健康》、《散文百家》、《公關世界》、中國作家網等媒體陸續發表了我不少散文作品,給我很大的鼓舞和信心,也帶給我在醫院里以灰色為基調的生活一抹光亮。
再后來,我的第一本勵志著作《“折翅天使”與生命對話》簽約出版。國際文化出版公司編輯部及市場部負責人葛宏峰在北京舉行的新書首發式上說,在書稿中看到了書君內心張揚著對生命的渴望,覺得是一本勵志好書,僅在很短時間內就完成了書籍的審批,比通常快了不只一倍。著名作家陸天明為書作序,陸老師坦言“我拒絕過很多要我寫序的邀請”,但是為書君作序卻是在第一瞬間就答應了,而且覺得是一種“榮幸”,是“需要戰戰兢兢地十分認真地去兌現的‘榮幸’”。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我們應該感謝書君,因為這個如此年輕的人讓我們再一次看到‘人’可以如此悲壯頑強,如此堅毅執著,如此無奈但同時又如此自信地去豐富、擴展、加厚和加固‘人’的本義。”
這個時候,我才感到寫作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需要寫出更多的東西,讓關心我的老師品評,給同樣處于生命沼澤中的人們以激勵。特別是我以全國關愛之心十大人物、“奧運志愿之星宣講團成員”的身份應邀到奧運會現場勵志奧運志愿者,同時帶著新書被中央電視臺邀請做客“心理訪談”錄制《折翅天使》兩期節目,更讓我感到我存活下去和創作的意義所在,更堅定了用生命寫作的信念。
寫作是一盞燈,指引我前行的路。
年近七旬的母親是我形影不離的堅強后盾,像原始部落人苦苦守著我的一息生命之火,像一位堅強的戰士陪著我轉戰南北求醫多地幾家醫院。我寫母親的文章多,引起的反響也大。一篇《那塊浸滿辛酸母愛的搓衣板》被新疆《老年康樂報》刊發,引起新疆一位病友的共鳴,找報社要到我的聯系方式,多次通過電話和我交流談心,給我的寫作賦予不一般的意義。
這份梳理自己思想,又能安撫他人心靈的寫作,被朋友當成手持燈光,照亮了每個同路人。這一層意義是我不曾想到的。我在網上建立了“與死神對決”博客,手機開通了“生命熱線”,河北、新疆、廣東、上海、北京、山東等地身患重癥和殘疾的朋友通過不同方式和我傾心交談,甚至在生活中遭遇不幸、失戀和巨大壓力的人也找到我汲取精神力量。
“活好自己”,無論遇見怎樣的境況,我們身上都有“活好自己”的神圣責任。殘酷的車禍限制了我的活動范圍,在閱讀思考后的寫作,卻拓寬了我的視野。
身體的不便、心靈上的痛、生活中的苦,不在其中的人,是很難想象的。能寫出來的可能永遠僅是冰山的一角。
對于寫作,我仍感是一個門外漢,并不是順風順水的。當被生活中某人某事觸動時,有想法,行之筆端時,卻似散落一地的珠子串不起來。如果半途擱淺,線是線,珠是珠,零散地跑出了頭腦以外再也拾不起來,頭腦一片空白。自感自己的能力嚴重不足,這時會像一個愛使性子的孩子,躲得遠遠的,省得被那些珠珠線線奚落,讓自己窺見到自己的無力和卑怯。
這幾年當中,得到不少前輩老師的指點和引導,從寫作,到生活,到人生的思考,給我很大的幫助,助我成長。苦悶中,常有良師益友建議:不要只寫自己那點事,放開思路也可以寫別人啊;多閱讀,多讀經典,厚實自己的文化底蘊;靜下心,沉淀下來,能寫出好文章的必是善于觀察的人……
曾經彷徨,猶豫不決,在拒絕中反思,又在反思中求索。但是無論我是怎樣的態度,寫作就在那里,像一盞燈固守在那里,接近它時便給我切身的光亮和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