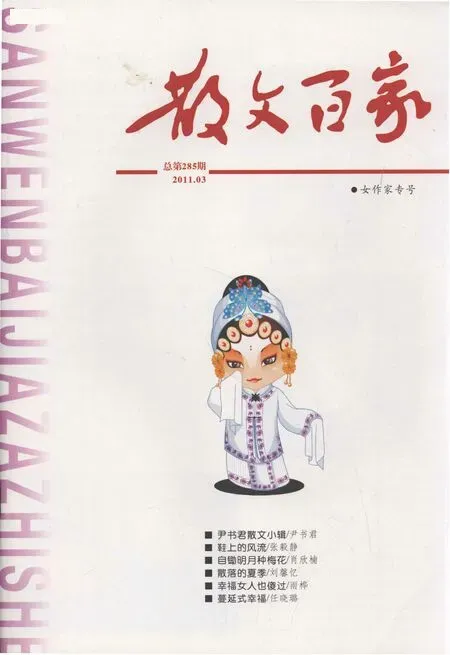西鄉女子
●彭曉玲
西鄉女子
●彭曉玲
在瀏陽,言談之間,人們時常會提起一句俗話:北鄉出布擔,西鄉出小旦。由此,可以推之,北鄉人勤勞舍得吃苦,而西鄉人愛唱戲戲唱得好。還可推之,西鄉的女子,長得耐看,擁有清秀脫俗的美。實際上,這種美,并不是指簡單的外在美,更多的是指一種群體性情之美。
在西鄉,倘說起誰家的女子美,只說長得清秀長得好看,不會說如何如何漂亮。因為受農耕文化的影響至深,西鄉人更看重家庭的穩定與日子的安穩,女子自然成了家庭的重要紐帶。于是,在西鄉,打小小年紀起,家中的長輩便會告誡自己的女兒,女孩要有女孩的樣,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要四處亂跑要學會守家。在舊時代,西鄉的女孩大多得學會績麻紡紗織布做鞋繡花,至于家務活就更不用說了。女子無才便是德,只需相夫教子,操持家務,圍著家轉就行。就是好女子,就是稱職的賢妻良母,就是做女人的本分。即便在新社會,西鄉的女孩,在上學之余,也得早早地跟在父母身后在田里地里干活,或留在家里靜靜地洗衣做飯,掃地抹灰,喂雞喂鴨喂豬,忙碌的身影在家里家外不時閃現。于好女子的標準,雖然有了時代的變遷,但當好賢妻良母卻一脈相承。
于是,行走在西鄉的村落屋場,便會驚奇地發現,西鄉的女孩并無驚艷之美,但面容清秀衣著清爽,說話輕言細語,眼神靈動而沉靜,于熱鬧場合中羞羞怯怯的模樣令人生憐,如鄉村池塘里沾滿晨露的白荷,又如田野間大片大片的草籽花。
西鄉女孩的婚姻,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由不得自己做主,得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了家的西鄉女子,自會自動自發地擔起為人妻為人母的職責,每天天未明即起,忙至夜深還舍不得歇息,全身心圍著家圍著丈夫圍著孩子轉。可很久以來,西鄉的女子更多地卑微如草籽花,沒有人過多關注其生死貴賤,生則生矣死則死矣。西鄉大多數女子的婚姻,即使一萬個不甘心卻只得認命,往往操勞一輩子,也得不到自己男人真正的疼惜。一輩子的操勞,辛勞猶可忍受,最不堪是沉重的孤獨與無助。也許她曾經有過生死相許的戀人,也許她才華出眾心氣也高,可既然命當如此,也就忍痛將一切埋在心底。此時,西鄉女子收起了少女時瑰麗的夢想,還有那些粉色的衣裳,風風光光的忙碌讓她看上去有些疲倦,依然閃亮的雙眸卻洋溢著母性的光輝,溫和而動人,緩緩撫平了兒女們的失落與挫折。
當一個新的社會已然來臨,西鄉女孩的婚事,雖依然傳承了媒妁之言,依然靠媒婆穿針引線,但漸漸地不再全由父母包辦。于是,西鄉女孩擁有了一定的自主選擇,甚至有人大膽地自由戀愛。當然,西鄉女子依然勤勞,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只知道起早摸黑地忙碌,只要一家人和和睦睦地過日子,就心滿意足了就覺得值得了。實在是太累了,男人又不太顧家,無奈之下西鄉女子也會潑辣起來,與男人吵鬧與男人打架,直至男人俯首稱臣,方才罷休。但轉眼之間,她又喜笑連連,風風火火地忙活去了。在西鄉,倘一個家庭沒有女人,就像木桶少了箍籮筐少了系,了無生機。
而進入新時代,越來越多的西鄉女孩,隨著洶涌的經濟大潮涌入城市,驚喜地發現了自身價值煥發了自身價值。當她們反觀自己的婚姻家庭時,便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也因此,在時代浪潮里載沉載浮,西鄉女孩不再被動地接受強加于自己的婚姻,在關乎自身命運的婚姻大事上,更多的是看對方有沒有頭腦舍不舍得吃苦。西鄉女孩不僅擁有了沖破媒妁之言的勇氣,且已然學會了規避婚姻風險,執著地去追尋幸福的婚姻。
其實,西鄉女孩,與鄉村草籽花何其相似,無論時空如何改變,根依然在鄉村。西鄉女孩,也許已在都市擁有自己的天空,可每望一眼遙遠的故園,及故園女孩曾經的生命歷程,便會更加懂得婚姻的可貴與神圣。可無論如何,西鄉女孩都相信神圣的愛情,不會過多看重男人錢財的多少,也不會一味地委曲求全。不堪重負之時,也會毅然逃離婚姻的圍城,再苦再累也不愿失卻自己的尊嚴。這是西鄉女孩集體的超越,盡管為此付出了至少三代人沉重的代價與教訓,依然值得慶幸與欣慰。
縱其一生,西鄉女子勤勞與質樸,從容與忍讓,詮釋著一種母性的平凡與偉大,一如春天田野里的草籽花,也曾有過純凈絢麗的青春色彩,孕育過平凡而又充實的果實。又如夏天原野上白色的紫薇花,靜默而又美好。正是西鄉女子的任勞任怨,西鄉女子的善解人意,西鄉女子的純樸與浪漫,使得西鄉大地及西鄉人更加多姿多彩。
在歲月的流逝中,已然白發蒼蒼的西鄉女子,看上去依然清爽整潔,依然在為兒孫們忙碌,或忙忙家務或帶帶小孩,動作從容,神情淡定。天氣晴好之日,干脆搬了張靠背椅,坐在自家大門口,靜靜地張望著門前人來人往的大路,及蒼翠的青山,神情卻迷離溫和,是在閉目養神,還是已然沉入往事的懷想中?偶爾有亮色自臉上一閃而過,隨即又陷于沉靜與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