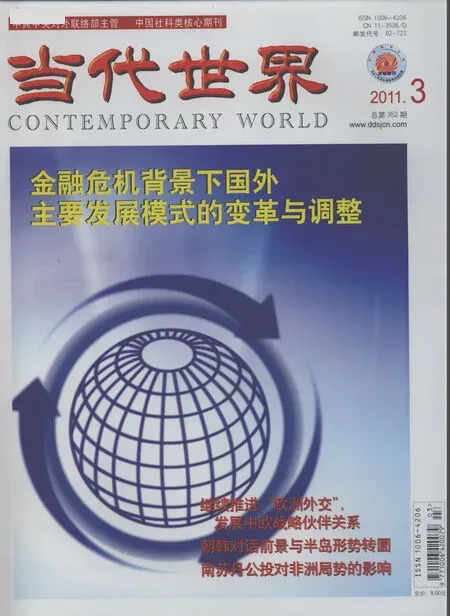評析“中國模式”
■ 王友明/文
評析“中國模式”
■ 王友明/文
隨著中國成功應對金融危機,“中國模式”再度成為熱點,其中關于“中國模式”的界定、特點、教訓等問題的爭論異常激烈,對此,本文對一些常見問題陳述己見。
“中國模式”究竟是否存在?
在眾多熱炒“中國模式”輿論聲中,有一類聲音更是激起千層浪——“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中國模式’”、“現在提‘中國模式’為時過早,至多可稱為‘中國經驗’或‘中國特色’”等。對此觀點,我們可以從概念的基本定義出發,探討“中國模式”的存在與否。
何謂模式:模式是可供效仿的模型或范例,是事物發展特點的匯集,是該類事物典型特征的反映和示范。成為模式必須具備兩個基本要素:一是該事物在與同類事物的比較中具有自身獨特而鮮明的特點;二是這些特點具有恒定性,能構成穩定成型的體系。
何謂發展模式:發展模式是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進而形成的具有鮮明特征的經濟社會發展體制。它是國家基本制度在不同的政治文化、歷史傳統和社會框架條件下建立與發展的產物。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圍繞國家與市場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國家與社會之間關系的不斷調整,產生了不同的發展模式。以西方國家為例,其發展模式大致可以分為政府導向型的“日本模式”、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美國模式”、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為代表的“萊茵模式”。
從上述定義的基本要素來看,“中國模式”還是客觀存在的。
首先,中國的發展方式與其他發展方式相比,具有自身獨特而鮮明的特點。中國發展方式最吸引世人關注的莫過于它的自身特色,這也是中國發展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30年來,中國立足國情制定適合自身特點的發展方略,而不是在全球化潮流中“移植”發達國家模式。對于盛行全球的西方發展模式,中國并不一味拒絕,而是吸收其經驗為我所用,汲取其教訓為我所鑒,并結合自身歷史文化背景和政治社會制度,在改革實踐中,“摸著石頭過河”,最終探索出一條信息化時代發展中國家后發式、加速崛起的發展道路。正如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撰文指出,“中國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中國沒有全盤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努力建設符合自身特點的經濟政治制度。”
其次,中國發展方式已初步具備穩定成型的體系。在長達30年的改革摸索中,中國發展已經形成了模式成型體系所具備的基本要素,即“指導理論、發展目標、中心任務、發展步驟、發展手段”等。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作指導,以經濟建設作為執政的中心任務,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改革目標,著力改革舊有經濟體制,由點到面,逐步推進,全方位、多層次地實施興國戰略,與此同時,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不斷完善和調整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中國的發展方式是其執政黨在總結國內建設出現的失誤甚至嚴重錯誤的基礎上,汲取蘇聯模式的失敗教訓,尊重群眾智慧,大膽開拓,經過艱辛探索,最終由一系列發展經驗逐步上升為理論體系的發展模式。
再次,發展模式的存在與否并不以其實踐的時間長短而定。國外一些國家的發展戰略實施不久,其模式名稱便已出現,隨著實踐的不斷豐富,發展戰略逐步得到補充、完善,最終成為定型模式,并為世人熟知。瑞典模式、德國模式便是其中典型。中國的發展方式歷經三十多年,無論是理論體系還是實踐經驗均不斷豐富而日臻成熟,初步形成獨具特色的模式體系。
總之,中國發展方式雖然離“模式”所要求的恒定性和典范性還有一定距離,但“中國模式”畢竟已客觀存在,它已經超出“中國經驗”范疇。不能出于冷靜、謙遜的心態而否認“中國模式”的存在,當務之急的是對中國模式加以規范而科學地界定以消弭各種誤解和歪讀。
“中國模式”有何特點?
“中國模式”究竟有何內涵和特點?中國的成功之路究竟有何秘訣?這是近年來國外政界、學術界常談及的熱門話題。一些國家指定專門機構研究“中國模式”,一些政要也親自撰文闡述對于“中國模式”的看法。
越南對“中國模式”頗有研究,該國領導人總結了“中國模式”的基本特點:以穩定作為改革的基本前提條件;實施從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逐步推進改革;經濟改革優先,政治改革緊跟其后;以對外開放服務國內改革。[1]
新加坡學者鄭永年認為,“中國模式”區別于前蘇聯模式的一大特點是:“中國模式”不像前蘇聯那樣具有高度的意識形態性,中國基本上不再過分強調意識形態,尤其是和西方對抗的意識形態。
俄羅斯共產黨主席久加諾夫認為,“中國模式”是“社會主義+中國民族特色+國家調控+現代技術管理”。
中國學者也對“中國模式”的本質與特點作出總結,有的認為,中國模式在本質上是“一個追趕模式,即作為工業化與現代化的后來者、落伍者,它的基本目標和基本任務就是追趕現行的、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所以,它的特點與經驗“首先是一個學習模式、其次是一個競爭模式。再次是一個創新模式”。[2]
也有中國學者認為,“中國模式”的特色在于兩點:一是與傳統市場經濟理論不同,中國成功地實現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相結合;二是中國實行“先增量、后存量”式的改革,即在國有經濟體制外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以市場經濟的“增量”來加速推動市場主體的形成和市場機制的發育,使市場力量從體制外向體制內滲透,由表及里,由淺入深,最終導向產權制度改革。[3]
筆者認為,上述論斷基本反映了“中國模式”的一些特征。實際上,“中國模式”具有諸多豐富的內涵與特點,較為顯著的特點有:
1、以發展作為執政的第一要務,同時穩妥而慎重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始終高度重視“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系。
2、以市場配置資源作為經濟運行的基本機制,同時以國家宏觀調控作為掌控國民經濟發展方向的重要手段,“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成為經濟運行的常態方式。
3、重點突破與穩步推進相結合,力避全國性的“休克療法”,以“特區”作為試驗田,大膽試行各項創新舉措,成功后,逐步多點推進。
4、以公有制作為主體把握國民經濟命脈,同時推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5、根據發展的不同時期,科學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在改革開放初期階段將效率置于優先地位,同時兼顧公平。當改革進入深層次階段,當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生態保護出現失衡時,適時調整發展戰略,推出以“五個統籌”為內涵的科學發展觀。
“中國模式”有何教訓?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模式具有諸多的成功經驗,但也包含許多“中國教訓”。它是“中國經驗”與“中國教訓”的結合體。隨著我國現代化建設向市場化、全球化方向的進一步深入,改革過程中的經濟與社會、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發展模式的某些弊端也顯露出來,主要表現在:
1、 發展目標的不平衡性。舊的發展目標偏重于經濟增長目標,以物質財富的增加作為衡量發展成就的主要標尺,將發展等同于經濟增長,又將經濟增長等同于物質財富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人的全面發展目標與社會進步目標。
2、發展方式的粗放性。多年來,一些地方的經濟高速增長是建立在能源高消耗、環境污染、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基礎之上,屬于效益低、成本高、創新性少、不可持續的粗放擴張型發展。
3、發展結構的失衡性。發展思維停留在“工業文明觀”上,以國家的工業增長作為社會進步的標志,片面追求城市化和單純的GDP產值,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在區域發展上,沿海發達地區和老工業地區、中西部地區的差距拉大,由此引發的社會不穩定因素時有表現。
4、 發展手段的失衡性。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并未并駕齊驅,過分依賴出口和投資拉動,內生性消費長期不足。外部一旦有風吹草動,國內經濟便受到很大影響。
針對缺陷與教訓,“科學發展觀”賦予“中國模式”全新內涵。科學發展觀就是改變發展思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注重統籌發展,提高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包容性、創新性,實行可持續發展。
外界因何熱炒“中國模式”?
隨著“中國模式”熱的升溫,國外介紹和稱贊“中國模式”的文章頻繁見諸報端,其中不乏溢美之詞,諸如,“中國模式吸引全球目光,成為許多國家羨慕和效仿的對象”;又如,“在‘華盛頓共識’分崩離析之際,‘北京共識’為世界帶來了希望。”
外界為何如此熱捧“中國模式”?這與美國模式的風光不再有關。上世紀90年代以來,“華盛頓共識”所推行的美國新自由主義模式在全球化過程中大行其道,風光無限,然而,拉美等一批發展中國家效仿該模式以失敗而告終,不但未能解決經濟發展的痼疾,反而付出了兩極分化的沉重代價。美國模式遭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與此同時,中國走自身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關注“中國模式”,希望從中借鑒經驗。發達國家的政要和學者也開始反思,“為什么美國模式光芒日漸黯淡,而中國模式的魅力卻與日俱增?”金融危機后,美國模式更是遭到全世界的詬病。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史迪格力茲有感而發地說,“由于此次危機,沒人再對美式資本主義表現出絲毫興趣,世人都因為美國的過錯而遭罪”。因此,金融危機后,世界掀起了新一輪“中國模式”熱。
客觀來說,在外界對于“中國模式”種種“美譽”背后,隱藏著不同目的:有別有用心歪曲的;有“捧殺”的;有希望借鑒“中國模式”、盼望中國帶頭的;有好奇、跟風的。而西方國家熱炒“中國模式”,多少都帶點鼓吹“中國模式威脅論”目的,有的誣稱,“中國模式”是“政治集權體制下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是“國家管制主義和經濟實用主義相結合的‘混合模式’”。
如何正確面對熱炒的“中國模式”?
面對“熱捧”,中國需要保持清醒頭腦,正確認識和定位“中國模式”。為此必須解決好如下幾個問題:[4]
1、“中國模式”迄今尚未有一個科學而規范的界定。目前國內外對“中國模式”的稱謂不僅五花八門,諸如:“北京共識”、“北京經驗”、“中國道路”、“中國特色”等等,而且大多按照西方理論體系、邏輯思維和分析框架進行詮釋與界定。對此,中國應從提升“軟國力”的高度來解釋和宣傳自己,盡早對“中國模式”的概念進行統一、科學、規范地界定和宣傳。在結合中國國情的基礎上,盡量從經濟學而不是意識形態的角度定義“ 中國模式”。
2、加強對中國自身發展模式的研究。目前的狀況是,國外學者對“中國模式”的研究與探討熱鬧非凡,而國內對自身模式的研究成果甚少,現有的研究大都是著眼于對國外研究的評價。
3、中國自身發展模式是發展中國家在探索本國經濟社會發展道路中形成的模式,需要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去認識和定位“中國模式”,而不能以西方發達國家模式的要求和標準來界定和規劃“中國模式”的發展構架和未來方向。
4、中國自身發展模式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經濟社會的發展以構建發達的生產力和公正和諧的生產關系為目標,這是“中國模式”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模式的主要區別,因而不能以中國自身發展模式的標準來評判其他國家發展模式的成敗得失。
5、謹慎對待所謂“北京共識”概念,不要高估中國自身發展模式對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示范效應,應始終堅持認為,世界上并沒有所謂發展模式的“共識”,只有符合各自國情的發展模式,更不能附和所謂的“以‘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的論調。
6、“中國模式”尚處于探索發展的早期階段,模式特征尚未完全定型。目前,中國發展還面臨來自國內外諸多現實問題的挑戰,發展模式需要在探索與創新過程中獲得進一步的充實與完善。
綜上,“中國模式”在世界發展史上將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它的核心要素諸如“根據自身國情制定發展道路”、“緊緊抓住現代技術革命的戰略機遇”、“市場與政府缺一不可”等基本經驗將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具有重要啟示作用。“中國模式”也必然要在總結“中國經驗”和“中國教訓”過程中逐步成為全面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作者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部副主任)
(責任編輯:丁云)
[1] 宿景祥.越南經濟緊跟“中國模式”[J].望東方周刊: 2004,6.
[2] 黃平、崔之元.中國與全球化: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153、175.
[3] 劉偉.市場化29年:“中國奇跡”是怎么創造的?[J].時事報告: 2007,11.
[4] 王友明.尊重發展模式多樣性,建設和諧世界[M]//郭震遠.建設和諧世界理論與實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