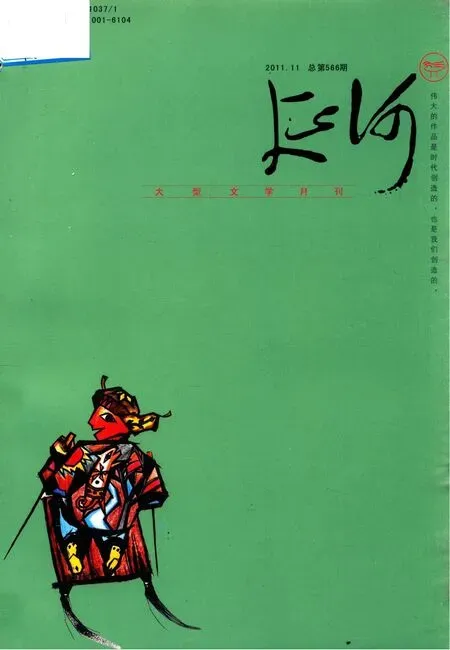夢 (節選)
伊 沙
大夢誰先覺?
平生我無知!
——題記
夢(130)
我在對一個人說話
此人
一會兒像現實中的A
一會兒像現實中的B
一會兒像現實中的C
一會兒像不存在的D
可是為什么
我對他說的話
卻一貫到底
毫無變化
夢(131)
乍暖還寒的春天
一位年輕的詩人
蒸發于江南
他的妻子
到處找他
在網上發布尋人啟事
于是他托夢
給他的妻子
說他想要扶橋回家
他的妻子
趕赴江南
就在那一天
他的尸體
在一條河中
浮出水面
夢(132)
咖啡館
窗明幾凈
典雅溫馨
可以看電視
還可以上網
我就一邊上網
一邊看電視
電視在放送
日本大地震
的即時新聞
地震引發海嘯的畫面
觸目驚心
我通過QQ
和一位女網友聊天
我問她:你長神馬樣子?
她回答:我長得像海嘯
夢(133)
父親在叢林深處
講課
背景是軍用帳篷
和一塊黑板
底下滿坐著
穿草綠色軍裝的
紅色高棉的戰士
坐著我
懷抱一把中國造的
沖鋒槍
一眨眼——
父親變成了波爾布特
夢(134)
在幽暗的城堡內部
他的嘴
尋覓著
她的嘴
結果是
唇找到唇
吻找到吻
舌找到舌
井找到井
火找到火
兩朵喇叭花的自焚
夢(135)
恍若一部韓劇
他與她
從一輛紅色雙層巴士上
走下來
這是一對
柏拉圖式的精神戀人
在多年后的邂逅
他吻了她
這是他們平生第一次
親密接觸
她問他:“啥感覺?”
他回答:“菊花香!”
他隨之去了她住處
那是一座花園
菊花開滿園
一個老園丁
在伺候著那些菊花
一邊伺候一邊夸她
他想:“她真是
對所有人都好!”
恍若一部韓劇
她是原小說作者
一名言情女作家
他是她的讀者
夢(136)
在童年的向陽院
露天水龍頭
母親般洗衣服的
是我的妻
我站在她面前說:
“你昨晚三點才回來”
她不說話
“你總該告訴我
你人在哪兒吧?”
“在XX家”
她頭也不抬地回答
繼續在搓衣板上
洗衣服
我知道XX
是她的閨蜜
不久以前
離家出走
我說:“她人都不在
你是和她老公在一起吧?”
“是又怎么樣?”
“我打不死你!”
“那就打吧!來!”
四周半黑不明
像是黑不到底的夜晚
又像亮不起來的白天
夢(137)
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
在一座空空如也的城里
只有我和我的兒子
從城市的兩端
跑向中心廣場
在廣場正中
一根光禿禿的旗桿下
兒子從地上抓起一把雪:
“爸爸,這雪是假的呀
全都是石灰!”
夢(138)
北師大的北門
與北影廠斜對
我站在北影廠門口
像是在等誰
看見葛存壯老頭
走出來了
老觀眾還記得
他是“馬尾巴的功能”
新觀眾只知道
他是葛優他爸
我與看大門的老嫗
聊起天來
她對我的詩
提了諸多問題
全寫在一張紙上
像考卷一樣
我懷著耐心一一解答
像傳說中的白居易
對著老嫗讀詩
看她能否聽懂
夢(139)
一名少女
赤裸上體
在我房間
晃來蕩去
我被嚇壞了
妄圖奪門而逃
卻被她堵個正著
我清醒地記得
她是我朋友的女兒
(哪位朋友并未想起)
朋友妻不可欺
朋友之女
不可欺我
夢(140)
一個沒長臉的人
準確點說
是長了臉
但是臉上
沒長五官的人
被五花大綁在
我大學時代
男生宿舍
架子床的
鐵架上
被我好一通
拳擊暴揍
有一點
在夢里
比在現實中
更加清晰
我之所以
毫無道理
濫用暴力
是出于恐懼
這張白板臉
帶給我的
深深的恐懼
夢(141)
我中學那會兒的教室
破舊的木地板
踩起來又響又軟
那是英國人當年辦的
一所教會中學
遺留下來的老樓
下課時分
同學們紛紛起立
背起書包
朝外走去
我的女同桌
悄悄對我說:
“別急呀
讓他們先走……”
我嗅到一絲
香水的誘惑
側目而視
大吃一驚
是已故臺灣女作家三毛
披散著一頭三毛式長發
脖子上還胡亂纏繞著
吊死她的長筒絲襪
夢(142)
我家院子里
垃圾堆成山
堆成八卦陣
年輕美麗的母親
迎風而立
在房頂上
為我指點迷津
夢(143)
森林之夜
鬼哭狼嗥
并未令我
感到恐懼
這時傳來
人腳步聲
咚咚咚咚
我聽到了
自己心跳
并嘔出了
一顆紅心
夢(144)
密室里
女巫在布道
在場聽眾
有三人
侯馬、中島和我
另有一人
遲到了
黑暗中
看不清其臉
我發問:“徐江?”
遲到者無應答
“你是徐江嗎?”
侯馬高聲問道
仍不作聲
看不清臉
我朝下看
發現這個黑影
有細小的腳踝
女人才有的腳踝
或小馬駒
恐怖
看不見
仿佛泄露的核燃料
污染了此間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