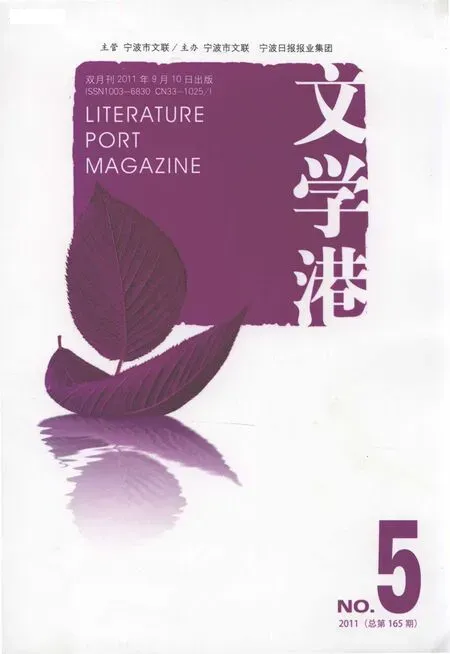我的文學恩師
王信厚
原 《寧波文藝》負責人趙林泉的不幸病逝勾起我綿綿的追思,腦海中反反復復縈回著趙老師的形象,耳畔仿佛又響起了他那不緊不慢帶著濃厚山東口音的寧波話……趙老師是改變我命運的人,如果沒有他,我的人生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市文聯和市文化館是兩塊牌子一個班子,趙老師是文聯唯一的專職干部,又是文化館唯一的創作輔導老師,當初受趙老師指導的業余作者有干部、工人、農民,還有就是像我這樣的待業青年,那年代政治運動不斷,文藝界是重災區,然而我們這個文學小圈子,由于趙老師的人格魅力影響,大家卻和諧相處,猶如世外桃源。趙老師是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又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南下干部,在他身上有山東人的厚道耿直,又有南方人的細膩善感。他對作者的關心不僅僅是在創作上,更多的是在生活上,在做人上,他本人不僅僅是言傳,更多的是身教。
然而好景不長,文革風暴來了。趙老師在解放前就讀山東濟南的華東大學,和所有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一樣,也有所謂的出身問題,我是在文革初期看大字報后才知道,說他反動階級立場不改,居然培養反動階級的孝子賢孫。我不禁打了一個寒顫,天啊,對黨忠心耿耿的趙老師居然出身反動階級,而這個反動階級的孝子賢孫正是我。我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認識趙老師的。那時我初中畢業,因出身不好待業在家,喜歡文藝的我在文化館辦的油印刊物上投稿,得到了趙老師的幫助,其中一個小戲,他幫我修改并向當時唯一的省級文學刊物 《東海》推薦 (此小戲也得到蘇立聲老師的幫助),結果居然發表了,這使我創作信心大增。后來他又推薦我到市戲曲訓練班甬劇班當編劇,從此我走上了戲劇創作道路。面對這張在趙林泉名字上打上大紅叉的大字報,我又驚又怕。處事謹慎的趙老師難道不知道我的家庭出身?不可能,那時連發表一篇豆腐干文章也要填個人履歷,可趙老師在我面前從來不提不問,當大字報上街后他見到我也繞道而走閉口不談。更令人感動的是,文革后期他從 “牛棚”里解放出來,我向他為我的出身而遭受牽累表示歉意時,他竟連連擺手,說是他的問題牽累了我,他要我相信黨的政策,寫出更多好作品。他自己打了多次入黨報告,黨組織也終于在1983年為他敞開了大門。
其實,受趙老師幫助的遠遠不止我一個。去年,一位從外系統調入文化部門的領導,上任不久就約我去拜訪趙老師,其實趙老師僅僅在他年輕時幫他修改發表過兩篇作品,為什么時隔幾十年還記得一位早已退休在家的老人?他說當初自已是個普通的農家子弟,趙老師熱情待人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很想去看看他。文革前,市郊有個姓勵的青年因 “言論不當”冒犯領導失學在家,是趙老師發現了他的文藝才能,幫助他編寫演唱作品下鄉演出,使他重新拾起希望。兩年后他參軍入伍,在部隊能說會寫、工作踏實,進步很快,如今已被授予少將軍銜,成為軍隊高級干部。
在與同事相處中,趙老師總是見利就讓,在《寧波文藝》工作期間,他兩次主動將工資提升名額讓給同事。后來領導要將他從副主編提為主編,他考慮到可能要挫傷另一個副主編的積極性,又主動向領導要求取消對自已的任命。難怪當我將趙老師病逝的噩耗告訴如今已在外地成為著名學者的那位同事時,他在電話里泣不成聲地說,像趙老師這樣的好人,世上真不多啊!
趙老師有大學文化程度,解放初曾任市機關學校語文教研組長,有扎實的文學功底,完全有條件自已創作,可他卻把全部精力撲在輔導培養業余作者身上,對大家的作品總是熱情鼓勵,悉心指導,在當時形勢下,他將文藝思想與文藝創作的普遍規律巧妙結合,使一些業余作者既學到了寫作本領,又免受了那時的極左思潮傷害。這些特殊的創作經歷是當今一些文學青年所無法理解的。
趙老師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業余作者,不論你地位高低、作品發表多少,他都能記得住你的名字及概況,即使是在他晚年記憶力嚴重衰退的時候,也念念不忘。但他卻希望大家忘了他,他是一個為人低調、淡泊名利、不愿麻煩人的人,在生命最后的歲月里,他甚至謝絕親友去探望他。在他心臟停止跳動的前幾分鐘,我趕到醫院去與他告別,他兒子湊在他耳邊說: “爸爸,王叔叔來看你了,你知道的話眨一下眼。”然而他竟眨不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