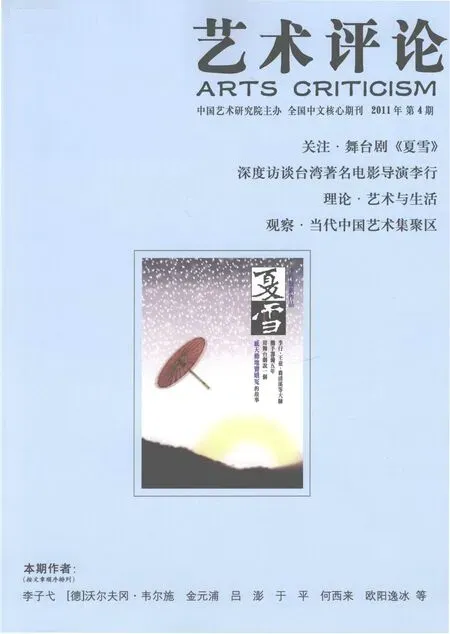燈籠高掛別樣紅——晉劇《大紅燈籠》對“大院”的深層解讀
王 馗
由小說《妻妾成群》衍生而出的“大紅燈籠”,在電影、電視、舞劇等多個領域,已然成為理解傳統生活的文化符號。人們解讀“大紅燈籠”的文化涵義,往往會將山西大院相提并論。毫不夸張地說,巍峨森嚴的明清晉商大院,讓小說原著中的傳統家族生活,平添了幾許冷峻詭秘的色彩,乃至很多觀眾真以為蘇童筆下的人物竟然生活在山西的大院之中了。晉劇《大紅燈籠》正是沿著這個思維脈絡,將人們已經熟悉了的小說故事,完全置換成大院中的恩愛情仇,只不過,晉劇的藝術家們所理解的“大院”,不再是富庶與財富積累起來的晉商大院,而是毀滅人性的“充滿死氣的大宅院”。
舞臺上的“在中堂”,還如原來電影電視中的沉郁凜然;舞臺上的大紅燈籠,還如原來電影戲劇舞臺上的詭秘熾烈,但是這次演出卻將小說和電影中隱沒了出處的大院,真正地與晉風晉韻實現了交融。蘇童筆下頗具江南陰郁色彩的人物和場景,被徹底置換成了山西大院中的人事糾葛。難得的是,晉劇《大紅燈籠》在蹈襲小說和電影中的基本情節之時,始終圍繞著女主人公——頌蓮的命運流轉和心靈浮沉,來構建情節,并且為這部作品賦予了更多超越小說和電影之外的意蘊。例如通過一批女性群像,展現封建男權制度對于女性的戕害和毀滅;例如通過頌蓮的心靈悸動,展現封建大院中無法滅絕的女性自覺,等等。即如該劇的節目單上赫然標識的“謹以此劇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這已然在妻妾爭風的婚姻悲劇中,試圖發現時代與文化的癥結。當人們已經津津樂道于山西晉商文明,流連于山西大院旅游的時候,當反映山西大院的影視戲劇作品不斷地引發人們對物欲財富的討論之時,晉劇的藝術家們卻大膽地選擇了更加冷靜的反省和超越,從“大院”中透視出傳統文化的卑陋之處,從“大紅燈籠”中發現時代變遷中的暗昧所在,這一點在主題上的刻意,正成為這部新創戲曲最令人欽敬的地方。
如果說,小說原著用成功的人物典型,細膩地描摹出了妻妾制度下的家庭悲劇;影視劇創作則用獨特的鏡頭語言和色彩表現,渲染了悲劇家庭的糜爛和悲劇人物的性格必然;那么晉劇的這種重新敷衍,卻試圖在此基礎上,用戲曲的舞蹈程式和劇詩吟唱,努力拓展出人性沉淪和覺醒的辯證。在劇中有一句唱詞說:“她陌生得好像不認識,洋學生怎么也會這樣扭曲”,這應該比較契合故事的原初主旨,通過人的扭曲和沉淪,來暗示時代新風無法吹拂的黑暗隱微。“大院”顯然成了一個時代污垢的藏納之地,儼然成了封建強權的典型象征,任何一個流連其間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成為“大院”的囚徒,那種從社會制度上帶來的“風不止、樹難靜,暗潮洶涌”,成了大院陰霾和悲劇的真正制造者。但是晉劇《大紅燈籠》卻并不止于此,透過女主人公的大段宣敘:“大汗淋漓卻冷冰冰,燕兒因我喪性命;這手兒洗不凈,染的竟然是血紅;雖然她被人利用也可憎,我仍然愧悔難止揪心疼”,那種與生俱來的人性之善,真實地流露出來,被命運束縛了手腳并且不斷走向麻木不仁的頌蓮,在人性惻隱的牽帶下,一次次地在“沒有愛來只有恨,只有冰冷無溫馨”的大院中,展現出人性的溫暖和內心的反思。雖然全劇的故事,始終在展現“妻妾們可悲可憫復可恨,為爭寵踐踏撕咬人吃人”的冷酷,但是,從頌蓮被迫無奈之下的屈從、孤苦失意之后的抗爭,以及失誤致人慘死之后的慚愧,仍能夠強烈地感到被扼殺于“大院”的必然,和突破這個“大院”的必然。因此,該劇改變了小說和電影中對于“大少爺”的性格定位,將其作為全劇最為純潔的角色,并通過他的口,斷然唱出“這老宅必須毅然走出去,若不然也會沉淪我自己”,這個“自尊自愛更自惜”的人物形象,似乎成了女主人公頌蓮的一面鏡子,自始自終地映照出不能泯滅的人性反思。
晉劇《大紅燈籠》在展現妻妾爭風的情節時,消減了場次變化帶來的故事敘述方式,借助“大紅燈籠”這一舞臺意象,勾連出女主人的心路歷程,為舞臺呈現出更多靈性的律動和詩性的境界。特別是借用舞劇、歌劇、音樂劇、話劇的表現手法,例如頌蓮初入陳府時的燈籠群舞,頌蓮與大公子吹簫解憂時的舞臺調度,以及頻繁使用的對唱、輪唱乃至混聲合唱等等,雖然在晉劇中能夠大略找到相似的表現方式,但卻顯示出突破晉劇傳統表演程式的諸多新意。這種在音樂、表演上的創新,甚至在舞臺語言上的普通話化,確實弱化了晉劇的傳統韻味,但卻貼近了與其他音樂戲劇形式的聯系,或許這正是晉劇的藝術家們試圖更近密地走入當下、面向青年觀眾的用心所在吧。
對于一部從創作到上演不足半年的新創戲曲而言,晉劇《大紅燈籠》已經為其藝術形象,展現出較為豐滿的個性肌理,比如三太太梅珊在劇中唱詞極少,反復吟唱的一句“畢竟男兒多薄幸,把個情字看得輕”,卻很深入地呈現出她的身份背景和閱歷眼光。再如二太太卓云的舞臺動作略帶夸張,卻很生動地表現出這個角色的造作和虛偽,等等。這顯然為進一步的藝術提升,提供了很好的平臺和基礎。可以預期的是,劇中的陳佐千、大公子等能夠彰顯劇作主旨的人物形象,應該會有更加豐滿的個性再現,這是需要這批晉劇藝術家們在不斷的演出之后逐漸完備起來的。
需要提出的是,戲曲音樂對于角色形象的塑造,往往能夠將人物內心幽微,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頌蓮的扮演者史佳花,廣泛吸納民族音樂精髓,在高亢清亮的“愛愛腔”基礎上,拓展出更加流暢清雅的藝術風格,為頌蓮這個被封建勢力壓迫毀滅的形象,賦予了更多人性的亮色。她的演唱,飽滿熱情,與舞臺背景中黑暗陰沉的大院形成強烈對比,舞臺上的頌蓮最終被家族制度“封燈”殘害,但是那響徹舞臺內外的控訴反抗,卻通過史佳花嫻熟而獨特的唱腔藝術,成了女主人公心靈的外化。雖然目前的《大紅燈籠》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還需要更加流動自然,頌蓮的許多個性氣質還需要在情節結構中更加有層次地展現,但是,史佳花已經用自己的聲腔藝術和表演藝術,塑造出了與電影、電視、芭蕾舞劇等藝術形式很不相同的頌蓮。這是晉劇《大紅燈籠》的成功所在。
多少年來,以史佳花、胡嫦娥、武凌云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晉劇藝術家,在戲曲轉型改制的當代,一直堅持著戲曲向更大范圍觀眾的推廣。在傳統戲曲底蘊深厚的山西,這些晉劇藝術家們都以扎實的唱做功夫和各具特色的經典表現,在晉劇流布區擁有廣泛的影響。而他們在尋求戲曲生存的發展之路上,也始終不忘用一個又一個新創劇目引領晉劇發展的潮流,始終不忘用貼近觀眾的經營模式來打造觀眾喜聞樂見的藝術精品。特別如史佳花,作為新時代晉劇藝術的領軍人物,多年以來一直在傳統深厚的晉劇流布區內,努力走出一條貼近生活、貼近時代的藝術創作道路,現代戲《石角凹》,秧歌音樂劇《西域桃花》,晉劇音樂電視劇《塞北婆姨》以及此次層樓更上的《大紅燈籠》,一再地展現了她對戲曲藝術的探索心路。這種精神確實已經讓她走到了晉劇發展的最前沿。這是晉劇的希望,也是源遠流長的山西戲曲的希望,當然,這才是大紅燈籠映照下的山西大院中本身具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