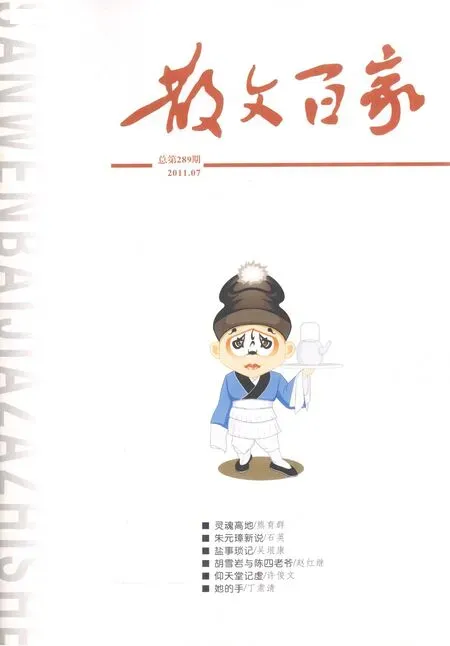母親的氣味
●李光彪
在我看來,世間辨別氣味的方法不外乎兩種:一種是用嘴親口嘗一嘗,便知其中酸甜苦辣的味道;另一種是用鼻子的嗅覺聞一聞,便知是香是臭。
在我熟悉的事物中,要數狗的嗅覺最靈敏,不管走多遠,只要撒泡尿作個記號,就能沿途返回,不會迷路。若有陌生的人登門,狗也能用嗅覺區分出來者的氣味,發出“汪、汪、汪”的叫聲,提醒主人防范。尤其是彝家人馴養的那些攆山狗,總是能嗅到各種獵物的氣味,引領主人朝著獵物逃跑的方向追攆,捕獲到獵物。
其實,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不論是動物,還是植物,甚至是空氣、陽光、泥土,都有著本身的氣味,只是由于世界太大,認知有限,自己不可能一一認識,全都了解而已。
而母親身上那些與身俱來特有的氣味,是我最熟悉不過的味道了。
我來到世上,大概最先就是從感知母親的氣味開始的。那時,我還是個吃奶的嬰兒,對事物的認識也一片空白,卻會“認生”,只要離開母親的懷抱,就會亂蹭亂哭,放回母親的手心,立即就會悄無聲息。后來長大以后,我才明白自己戀娘的原因,是母親身上有一種特殊的狐臭味和奶的腥氣味,我就是靠嗅覺感知,分辨出誰是自己的母親,戀戀不舍于母親氣味里的。
年幼的我像只嘴殼上蛋黃未掉的小鳥,還分不清人間善惡美丑,只知道“有奶便是娘”,整天像條毛毛蟲盯在母親身上,仿佛是頭未斷奶的小牛犢,寸步離不開母親。一天天長大以后,我才發現母親身上有很多怪怪的氣味。也正是那些怪怪的氣味,讓我開始產生了逃離母親的念頭。
身為農家婦女的母親,整天到晚都要與苦 活臟活打交道。一方面由于農村洗浴條件差, 不能經常洗澡;另一方面可換洗的衣物較少; 再加上母親本身固有的“夾汗臭”,起早貪黑 勞累一天歸來的母親氣味就更濃了。尤其是夏 天,天熱氣悶,再寬的院子,再寬的家,不管 母親的身影移動到哪里,都會彌流著母親特殊 的氣味。無知的我總是暗自躲開,生怕母親的 那種氣味傳染給自己,長大后成個“臭漢 子”,挨不上伴,當兵無人要,甚至娶不到媳 婦……惟有那些嗅到母親氣味的豬、雞、貓、 狗,立即就會接到通知似的,鳴叫著朝母親擁 來……
馬不停蹄,忙碌不休的母親除從事生產勞 動外,還要種菜園,全家人一年到頭才有菜 吃。可是,那時沒有化肥,要天天有菜吃,有 菜喂豬養雞,從菜籽下地,糞便就是蔬菜成長 必不可少的營養。所以,我家的廁所是個大茅 坑,專門用來裝人解溲的大便和我撿回家的 糞。就連屋里睡覺的床下,也藏著個尿罐,供 人起夜撒尿,積存起來澆菜。我經常看到母親 有時挑著尿罐,有時挑著臭哄哄的大糞,前往 菜園與水兌勻,有選擇地澆那些缺肥待長的蔬 菜。等母親澆完尿糞回家時,盡管尿罐、糞桶 已在小河里漂洗過,身上或多或少仍藏有尿糞 的臭味。直到后來,吃著母親種的那些胖墩墩 的蔬菜、圓溜溜的瓜,母親身上的尿糞味才漸 漸淡完。
當一天天撿糞長大的我,轉眼有母親的肩 頭高時,常被母親叫上,一同去挑尿、挑糞澆 菜園。悶悶不樂的我總是找借口抱怨母親,為 什么要讓我干那臟吧啦屎的活計。而身為農家子弟的我,雖然母親可以寬容自己,但生存的現實始終無法回避,挑尿、挑糞澆菜園的臟活必干無疑。特別是出豬圈、牛圈、羊圈,少不了要兩個人配合,用釘耙挖的挖、上的上,把糞草一筐筐挑出圈門,壘成個大糞堆,發酵后再運送到田地里施給莊稼、果樹。一格牛圈出完,母親和我滿身都濺滿了牛糞沫,甚至鼻孔里、五臟六腑里都鉆進了糞的身影。從此,和母親臭味相同的我,對母親氣味的認識開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對母親忍辱負重的敬意也由然而生。
油菜花開了,蠶豆花開了,菜園里的螟蟲多了,只見母親拎著瓶“樂果”或“敵敵畏”農藥,行走在花蕾吐艷的田間地頭、菜園邊,逐一為那些莊稼、蔬菜噴灑農藥。回家時,又是滿身的農藥味。每次噴灑過農藥的母親,盡管換去衣服,身上仍會虼蚤叮咬一般發癢,又搔又抓,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康復。可到了下一茬莊稼、蔬菜需要噴藥滅蟲時,那些與劇毒農藥打交道的活計,還是離不開母親那雙手。只見母親又穿上羊皮褂,身背噴霧器,嘴捂頭巾,走向莊稼,走向菜園,不停地噴藥殺蟲……
母親身上的氣味何止這些,還有碾米、磨 面帶回的糠麩味,下田插秧帶回的泥巴味,上 山砍柴帶回的茗油味,以及各種各樣蘑菇味、 青草味、蔬菜味、瓜果味……母親每次回家, 氣味就是最好的預報。
終于有一天,嗅著母親氣味長大的我,外 出求學,直至工作,離開了家,離開了母親, 也離開了母親身上那些朝夕相處的氣味,總是 不習慣。后來,我結婚成家有了孩子,母親從 又臟又臭的農活中徹底獲得了“解放”,進城 來幫我帶孩子,隔三差五洗洗澡。從此,母親 像變了個人似的,身上那些雜七雜八的氣味也 越來越少,越來越淡。
如今,年近九十的母親告老還鄉已經好幾 年了。我除了每年為數不多的幾次回家,能嗅 到一丁點母親的氣味外,已經離母親的氣味越 來越遠了。
歲月無情,看著一天天步入風燭殘年的母 親,我已經意識到,母親身上那些氣味一旦消 失,惟一能代替的,只有和血緣一起凝固在自 己心中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