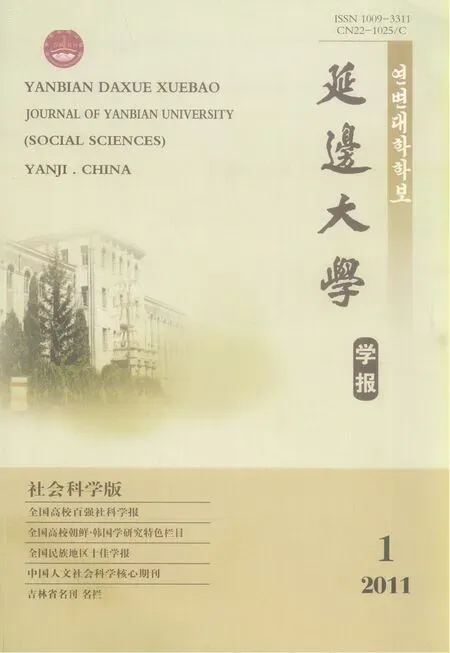姜敬愛與蕭紅小說語言描寫藝術之比較
劉 艷 萍
(延邊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吉林延吉133002)
姜敬愛(1906—1944年)和蕭紅(1911—1942年)分別是20世紀30年代朝鮮和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頗有影響的女作家,她們在其短暫的生命旅程中都創作出了豐碩而有價值的作品。姜敬愛的代表作《人間問題》被譽為殖民地時期的“現實主義文學杰作”,[1]而蕭紅的《生死場》更是“給上海文壇一個不小的新奇和驚動”,[2]蕭紅由此被魯迅稱贊為“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3]兩位作家無論在生活時代、個人經歷,還是在創作道路、命運結局上都呈現出驚人的相似性,具有極大的可比性。不僅如此,姜敬愛與蕭紅對語言藝術都有著細膩的感知,善于用質樸清新和極具色調的形象化詞語描寫現實生活的情態,并表現出個性化。讀者閱讀姜敬愛的小說,仿佛在欣賞一幅輕柔、淡雅的人物素描,會深深地被畫中人那幽怨、痛楚的眸子所震懾;而拜讀蕭紅的小說,讀者則像是觀賞一幅古樸、本色的水墨山水畫,心靈不由得為之顫動而凈化。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在《禮記·表記》里強調言辭表達的重要性:“情欲信,辭欲巧”。西晉著名文學家陸機在《文賦》中進一步提出:“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4]他認為,文章要寫得美,就得立意精巧,文辭妍麗,還應有聲音之美。可見,語言描寫藝術也是文學創作至關重要的一環,能夠顯露出作家的創作個性和美學追求。基于此,本文擬對姜敬愛和蕭紅小說的語言描寫藝術之比較略陳己見。
一、擬聲疊詞與奇語散句
在遣詞造句上,姜敬愛與蕭紅都擅長運用民間方言俚語,但是前者更酷愛使用擬聲或擬態的疊詞,目的是真實地反映人民生活的辛酸與苦難。據不完全統計,姜敬愛小說中擬聲擬態詞約有近千個之多。從語法結構上看,它們多呈偏正結構,既有名詞性偏正結構(“嘎吱嘎吱的聲音”),也有動詞性偏正結構(“卜楞起來”、“咯咯地叫”)。從構詞上分析,既有單聲疊詞(“嗚嗚地哭”、“啵啵顫動的嘴”),也有雙聲疊詞(“咕嘟咕嘟地冒起泡來”);既有雙聲疊韻詞(“咔嚓閂上門”、“嘎巴一響”),也有雙聲異韻詞(“撲通一聲摔倒”、“噗哧一笑”)。從重疊的方式看,既有ABAB式(“咕嘟咕嘟地冒起泡來”、“哧溜哧溜地喝起米湯來”),也有AABB式(“嘰嘰喳喳的麻雀聲”、“窸窸窣窣地起身”);既有ABB式有規則的詞語搭配(“叮鈴鈴的響聲”、“撲棱棱地飛走”),也有ABCD式雖不規則而隔字同聲的詞語搭配(“噼哩啪啦地掉下來”、“滴里嘟嚕的茄子”)。而從模擬的對象看,既有模擬聲響的,也有模擬動作的。模擬聲響的包括模擬自然界的風聲(“呼呼刮過的山風”)、雨聲(“雨嘩嘩地下著”)、流水聲(“潺潺的流水聲”)、鳥鳴聲(“鳥啾啾的凄涼的叫聲”),模擬人的哭泣聲(“抽抽嗒嗒地哭”)、嘆息聲(“嘑嘑地嘆著氣”)、腳步聲(“嚓嚓的腳步聲”)等。模擬動作的包括模擬心理動作(“怦怦跳動的心”)、情態動作(“嘚嘚地顫抖著”)、動態動作(“吧噠吧噠地抽著煙”)等。
從這些擬聲擬態詞的感情色彩和使用的效果看,它們很少被用于洋溢著幸福快樂和情緒高昂的場合和氣氛里,就連傳達笑意、安樂、歡快的擬聲詞也少得可憐。“風”、“雨”、“哭泣”、“嘆息”更多地表達著消極和貶義的色彩,易使人聯想起天氣惡劣、環境惡化和小說人物心緒敗壞的場合與氛圍,從而形象生動地為讀者勾勒出一幅苦難的生活圖景:在風聲鶴唳、暴雨瓢潑或者風雪肆虐的惡劣天氣里,姜敬愛筆下的主人公們蜷縮在漏雨潮濕的破屋里,他們肚子咕咕地叫著,咳咳地咳嗽著,咯吱咯吱地咬著牙,咕嘟咕嘟地喝著冷水,嚼著難以下咽的橡子面,或者去撿食人家扔掉的爛魚頭和餿飯。他們的痛苦呻吟改變不了悲慘的現實,一些人凄然死去。孩子們也因營養不良,不是餓死,就是病死。姜敬愛之所以在創作中大量使用擬聲擬態的疊詞,除了朝鮮語描寫的特色因素之外,主要是因為作者根據豐厚的底層受難體驗,細心地觀察并模擬生活的原生態,并借此表達自己同情弱小、鞭撻罪惡與黑暗之感情的結果。
蕭紅有時也采用這種方法寫作,譬如,“村前火車經過河橋,看不見火車,聽見隆隆的聲響”,[5]“一刮起風來,這房子就喳喳的山響……”,[6]但是擬聲詞多用于寫景句里,且具有偶然性,并不成規模。相反,蕭紅在遣詞造句上能夠另辟蹊徑,大量使用個性化極強的奇語散句,堪與姜敬愛小說所使用的擬聲疊詞相媲美。所謂奇語散句,是指蕭紅在遣詞造句時故意偏離傳統而規范的詞法、句法,發揮大膽的想象,憑借細心的觀察和敏銳的感覺,使用一些生動活潑并頗具直觀化和情緒化的詞語準確地把握事物的特征。在某些文學家和語法學家看來,有些是名詞帶賓語等詞性錯誤,有些是詞語間搭配不合理,有些是比喻的牽強,很難讓人接受,正如胡風坦言的“語法句法太特別了”。譬如,“紳士是高雅的,哪能夠不清不白的,哪能夠不分長幼地去存心朋友的女兒,像那般下等人似的”,[6]“雪地好像碎玻璃似的,越遠那閃光就越剛強”。[7]“存心”本是不及物動詞,不能帶受事賓語,而在此卻帶上了受事賓語“朋友的女兒”,動賓搭配顯然不當。如果換用“覬覦”一詞,又顯得過于嚴肅,無法傳達出作者揶揄的口吻。可見“存心”雖然不合語法規范,卻更能言傳作者諷刺揶揄的態度。在第二例中,雪地在陽光的輝映下折射出的閃光是很刺眼的,這是生活常識,而作者卻用了表現人之性格的“剛強”來形容這閃光,顯得不甚貼切。可是若聯系上下文,就會感覺這一詞用得非常形象,充滿動態感。王亞明由于一雙黑手和學習成績差被學校勒令退學,她的理想仿佛一塊晶瑩透明的玻璃破碎在雪地上,刺痛了目送她離去的“我”的眼睛,同時也回送給她“我”希望她剛強的祝愿。這一特點同樣體現在蕭紅小說大量而富有韻律的散句中。散句與整句相對,是指結構不整齊、長短不一,卻散而不亂,富于節奏和變化的句子。例如,“曠野,遠方,大平原上,看也看不見的地方,聽也聽不清的地方,狗叫聲,人聲,風聲,土地聲,山林聲,一切喧嘩,一切好像落在火焰里的那種暴亂,在黃昏的晚霞之后,完全停息了”。[8]這里長短句交替使用,韻腳鮮明,節奏鏗鏘,仿佛讀一首優美的詩。可見,蕭紅并不拘泥于白描式的鋪寫,而善于選擇富于變化、音樂感強和韻腳和諧的散句寫景狀物,細膩地展示人物心靈的感受。讀者初閱讀這類奇語散句時,往往有生僻滯澀之感,可仔細品讀之后反倒體味出形神兼備、渾然天成和搔癢止渴的蘊味,從而更能激發內心情感,與之共鳴,并產生無限的聯想。這實際上是詩化的語言,是作家打破常規,將人生世事進行感性、渾然的組合,對事物和對象進行印象式的、直觀的摹寫,借以傳達生活感受的結果。
二、五覺與通感
語言既有敘述功能,也有感覺功能,而表現形式各異的感覺可以為小說營造獨特的情境氛圍,進而對現實生活進行詩意化的擴張,使不同層次的讀者產生共鳴。人的感覺由視覺、觸覺、味覺、嗅覺、聽覺五覺器官構成,本是基于人的生理感覺而言,然而作為獨特的審美體驗,它早已被應用于藝術實踐中。在五覺的運用上,姜敬愛與蕭紅都廣泛運用視覺、聽覺和嗅覺來寫景狀物、展示人物心理,而味覺和觸覺則較少使用。
首先,視覺描寫。“他避雨的這家好像是有錢的殷實人家,白灰墻,黑瓦頂,木板門寬大敞亮,上面釘著有錢人家才用的那種宛若拳頭的大鐵釘。”[9]“翠姨墳頭的草籽已經發芽了,一掀一掀地和土粘成了一片,墳頭顯出淡淡的青色,常常會有白色的山羊跑過。”[10]姜敬愛和蕭紅小說中的這兩段視覺描寫都揭示了某種特定背景下的場景和人物特征,粗看起來沒有什么不同,但是前者是從主人公七星的視角觀看院子里的景物和有錢人家住房的,后者則站在作家的立場來感知小環的處境和翠姨的死;前者是心平氣和地敘述,后者是滿懷悲情地描述;前者表現出客觀的傾向,后者洋溢著主觀的議論。由此可見她們在創作上的不同特點,姜敬愛遵循傳統的人物塑造原則,借助客觀環境與背景來映襯主人公此時此地的心理,作者本人很少在作品中發表看法;而蕭紅總是打破人物塑造的邏輯,主動跳出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或評價。
其次,聽覺描寫。“背水的支架聲、賣肉賣白菜的聲音、操著不熟練的朝鮮話叫賣的中國人的洪亮聲音此起彼伏,回蕩在胡同里。”[11]運用聽覺描寫,目的是烘托和渲染環境與氛圍,該句通過各種聲音的交錯組合活現出日常生活的繁鬧圖景。又如,“風吹動高粱的聲音在頭上嗚嗚地響著,她似乎隱隱聽到孩子的哭聲”。[12]這是通過凄厲風聲的渲染,傳達保得媽對兒子的擔憂之情。這些都是通過主人公(瑪麗婭、保得媽)的視角表現的,可視作姜敬愛五覺描寫始終一貫的作風。而在蕭紅小說里,作家始終站在自己的立場觀察與評判現實景象。“晚間河邊蛙聲震耳。蚊子從河邊的草叢出發,嗡聲喧鬧的隊伍彌漫著每個家庭。”[5]震耳的蛙聲、嗡聲喧鬧的蚊子反襯出死一般寂寞冷落的生死場,透露出作家無以排解的鄉愁。又如,“屋子的右半部不知是架什么機器噠噠的響。什么聲音都給機器切斷了。芹的嘆息聲聽不見,老木匠咳嗽聲也聽不見,只是抖著他那年老快不中用的胳臂”。[13]在此,噠噠鳴響的機器被作家作了夸張性的渲染,以便遮掩住芹的嘆息聲和老木匠的咳嗽聲,窮人的可憐與疲于奔命昭然若揭,由此表達出作家“含淚的笑”。
再次,嗅覺描寫。與蕭紅不同,姜敬愛描寫得最豐富、最細膩、最有活力的感覺是嗅覺。它幾乎涵蓋了自然界和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全部氣味,如松香、草香、飯香、油香、奶香;汗味、煙味、餿味、腥味、糞臭味等,足見作家觀察生活的細膩與獨到之處。譬如,“密密實實、筆挺的松樹散發出的新鮮而又濃郁的松香”,[14]“大丫家還點著蚊火,清新的艾蒿味一陣陣地飄過來……”,[9]“沐浴在清晨炊煙中的龍井小街市充斥著豆油和豬油味”,[11]“媽媽衣服上散發著炊煙的味兒,隨著她的呼吸又帶過來一股飯香”,[9]“病人用手背抹著額頭上流出來的汗,拄著拐杖起身出去,帶起一股汗味中摻雜著好像頭發餿了的濃濃的味兒”,[15]“漁場的腥味撲鼻而來……”,[16]“車里的水果味和廁所味不堪忍聞,車也好像載滿了憂郁……”。[17]從這些描寫中可以看到,姜敬愛對自然清新并充滿濃郁芳香的自然界和溫馨幸福的家庭生活是神往的,力圖以之來映襯苦難的現實和骯臟齷齪的人生。特別是其筆下反復出現的象征性意象——松林更是作家魂牽夢繞的精神寄托。因為“松林”不僅是陪伴她生長的故土,每當她受到委屈,感到害怕、孤獨和寂寞時,她就會走入松林中,撫摸著松樹,向它傾訴,于是心靈便獲得了慰籍,而且松林也象征著她的精神家園。她喜愛嗅那清新濃郁的松脂香,也喜歡聞麩草的清香和充滿甜味的飯香,這些正是作家和貧苦人家所缺乏并渴望得到的東西。而汗味、臊味、糞味、腥味等難聞之味,則進一步凸現了貧富對立的現實差別,含蓄地表達了作家期冀改變現實苦難的理想和愿望。
蕭紅也描寫嗅覺之感,如“艾蒿的氣味漸漸織入一些疲乏的夢魂去”,[5]卻不普遍,也不單純地使用它。她更擅長打通五覺之間的界限,運用通感技法將其融會貫通,使詞語描述的主體事物蘊含著關于色彩、音響、氣味等多種感覺的意義,從而達到語句內容具體豐實、形象鮮活生動、效果強烈感人的目的。譬如,“葉子們交結著響,有時刺痛著皮膚。那里綠色的甜味的世界,顯然涼爽一些”,[5]“日光透過窗簾針般刺在床的一角和半壁墻,墻上照片少了幾張”,[18]“雞蛋開始爆裂的時候,母親的喊聲在尖利的刺著紙窗了”,[19]“清早起,嘉陵江邊上的風是涼爽的,帶著甜味的朝陽的光輝涼爽得可以摸到的微黃的紙片似的,混著朝露向這個四周都是山而中間這三個小鎮蒙下來”。[20]這些例句均采用通感的表現技巧。“綠色”是通過視覺感知到的色彩,而“甜味”則由味覺感知,“綠色的甜味的世界”是由視覺而引起的味覺之美,它是二里半的兒子羅圈腿渴望找到老山羊的希望所在,同時也是為躲避太陽的毒熱而故意鉆進去的。因為生著青穗的高粱地帶給他涼爽而又甜絲絲的感覺,由此反襯出天氣的炎熱和他找山羊的辛苦。“日光”透過窗簾瀉在床角和半面墻上,這是視覺之感,而“針般刺在”訴諸的是觸覺之感,這就形象地揭示出老齊此時此刻失落孤獨的心境。因為他不相信與女友逸影短暫的別離之后迎來的卻是她的無情背叛,而且是在自己腿部受傷急需她的照料之際,但這畢竟是冷酷的事實。于是他將自己反鎖在屋內,連平日感覺那么明媚的陽光現在都覺得刺眼,好像在嘲笑他無能似的。在此,“日光”刺痛的不是床和墻,而是老齊的心。同樣,“母親的喊聲”是聽覺感知的,“尖利的刺著紙窗”是一種觸覺,此句也是由聽覺而引發的觸覺之痛,它一方面昭示出母親的聲音之高和兇悍的表情,另一方面也傳達出小主人公“我”對強悍母親的恐懼心理,感覺自己的惡作劇(偷雞蛋)若被母親發現將又要面臨一頓毒打。最后的例句是味覺、觸覺和視覺三種感覺雜糅在一起的典型的通感表現。“帶著甜味的朝陽的光輝”是味覺感知到的,“可以摸到”是觸覺感知,“微黃的紙片”是由視覺感知的色彩,但是作為一個完整的句子,觸覺和味覺的作用是為了有力地表現視覺的效果而服務的。“甜味的朝陽的光輝”凸現的是陽光的清柔,“可以摸到的微黃的紙片”渲染的仍是柔和的光線之美。清早的柔和的陽光灑向三個小鎮,象征著新的希望降臨到偏僻寂寞、貧窮落后的小鎮,降臨到座落在山下的林姑娘家,這就為后文描寫林姑娘到下江人家里幫傭而改善家庭生活埋下了伏筆。可見,蕭紅小說的五覺通感絕不是心血來潮的沖動描寫,而是精心醞釀后才下筆鑄就的,是其獨特創作個性的充分發揮。
三、修辭手法的妙用
姜敬愛與蕭紅都擅長使用比喻、擬人和排比等修辭手法,借此增強語言的表達效果,但是在具體運用時又有差異。
首先,比喻。姜敬愛善于使用喻體與本體極為貼切形象的敘述語體來寫人狀物,給人以真實生動的美感。例如,“火車呼哧呼哧開進來了,好像蟲子般密集蠕動的人流開始晃動起來”,[14]“南山朝鮮神宮前面寬闊地帶閃爍著的燈火更凸顯了冬天的陣陣寒意,穿過光線紛紛揚揚飄落的雪花,宛若夏夜里撲進燈火走向死亡之路的浮游”。[21]這兩例都屬于語氣和緩、比喻貼切的敘述語體,將急于擠車的人流爭搶蜂擁的場面比喻成密集蠕動的蟲子,是以動植物或物與人互為喻本體的。而“穿過光線紛紛揚揚飄落的雪花”被比喻為“夏夜里撲進燈火走向死亡之路的浮游”,則是用自然現象作比喻,很是形象貼切。
蕭紅則多采用表情達意的抒情語體。這類比喻許多喻體與本體都不相似,甚至背離語法邏輯。這是因為作家運用比喻并非單純描繪客觀事物,而是形象地傳達某些難以言表的情緒和感受,這比敘述語體顯得更加生動傳神、蕩人心魄。例如,“那粉坊里的歌聲,就像一朵紅花開在了墻頭上。越鮮明,就越覺得荒涼”,[6]“從磨房看園子,這園子更不知鮮明了多少倍,簡直是金屬的了,簡直像在火里邊燒著那么熱烈”。[22]悲涼的“歌聲”與鮮艷的“紅花”、園子的熱鬧與火里燒著的金屬都是用無形喻有形,用抽象表形象,將兩個互不相容沒有任何邏輯關系的異質事物搭配在一起,從而擴充了想象的空間,極大地增強了讀者對于生命的情感體驗。
其次,擬人,即賦予自然界的物體以人的生命和思想感情,使之人格化,用以渲染氣氛,烘托性格,抒發感情或寄寓理想等。在姜敬愛筆下,不管是有生命的、靜止不動的物體,還是無生命的、抽象的事物,都被賦予了人的感情特征,產生了人的行為方式。例如,“漆黑的松林也嫉妒起來,旁邊的胡桃地里紅紅的胡桃和辣椒一個個地跳出來”,[14]“嘰嘰喳喳的麻雀聲在她聽來,仿佛高唱贊美她年輕的歌一樣,她的全身也感到一陣波浪起伏的快感”。[11]“松林”本是自然界的生命體,卻具有了人的感情——嫉妒,“胡桃和辣椒”本是靜止不動的,卻像人或動物似的“一個個地跳出來”。麻雀的叫聲“仿佛高唱贊美她年輕的歌一樣”,這既是比喻也是擬人。總之,姜敬愛使用擬人手法比較嚴格,她總是選擇那些最貼切最形象的修飾性詞語來傳達人的感情色彩和言談舉止。
蕭紅比姜敬愛更酷愛擬人手法,甚至有時將比喻、擬人和排比手法糅合在一起綜合使用,仿佛一幅立體圖畫,透著鮮活與動感。例如,“這些花從不澆水,任著風吹,任著太陽曬,可是卻越開越紅,越開越旺盛,把園子炫耀得閃眼,把六月夸獎得和水滾著那么熱”,[22]“磚頭曬太陽,就有泥土來陪著。有破壇子,就有破大缸。有豬槽子就有鐵犁頭。像是它們都配了對,結了婚。而且各自都有新生命送到世界上來”。[6]“炫耀”和“夸獎”的施事主體應該是人,而在此卻說明“花”的行為,這就形象地揭示出后花園子里的花開得盛、開得艷。“磚頭”、“泥土”、“壇子”、“大缸”、“豬槽子”、“鐵犁頭”等物體都像人一樣配對結婚,并且繁衍出了新的生命。如果說姜敬愛小說的擬人手法給人以莊重與素雅的感覺,那么蕭紅小說則給人以童真和純美的感受。
再次,排比。姜敬愛小說偶爾也使用排比的修辭手法,但是不普遍。例如,“七星時而走著走著突然停下,嗅著山野里的濃郁味道,時而邊走邊側耳傾聽潺潺的流水聲,時而嗅著撲鼻而來的稻香,伴隨著山鳥啾啾”。[9]這突出表現出七星熱愛大自然的感情。只有陶醉于大自然的山香水美中,他才暫時忘記現實生活的貧窮。排比句式可以增強語言氣勢,深化人物情感,在節奏上也能造成紛繁復沓、一唱三嘆之效果。蕭紅在小說中卻大量運用排比句式,而且運用得很巧妙。譬如,“霧氣像云煙一樣蒙蔽了野花、小河、房屋,蒙蔽了一切生息,蒙蔽了遠近的山崗”,[23]“除了我家的后園,還有街道。除了街道,還有大河。除了大河,還有柳條林。除了柳條林,還有更遠的,什么也沒有的地方,什么也看不見的地方,什么聲音也聽不見的地方”。[6]從例句中可以看到,作家在一段句群中一層套一層地連續使用排比句式,使得文本語句韻律和諧,極富音樂的節奏感,讀之也朗朗上口。
此外,姜敬愛和蕭紅偶爾也使用反復、對偶和“回環復沓”等修辭手法,借此增強語言的感染力和氣勢。有些句子已成為讀者耳熟能詳的經典語句,譬如,“我不管什么時候都是同情她的”,[24]“我家的院子是很荒涼的”[6]等。
綜上所述,姜敬愛與蕭紅同處于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文化語境,民族受難、個體受苦是其親歷的生存體驗,因此,她們對社會弱勢群體——底層民眾傾注了最大的同情和描寫。盡管她們都如實而形象地描寫了民眾的苦難生活與悲慘命運,語言質樸、細膩而傳神,但在遣詞造句、景物描寫和修辭手法等方面呈現出差異:1.姜敬愛酷愛擬聲疊詞,蕭紅善用奇語散句;2.姜敬愛“情以物興”,蕭紅“物以情睹”;3.姜敬愛擅長嗅覺描寫,蕭紅妙用通感。這種差異一是受民族文化心理習慣使然,即朝鮮語語匯中形象化的擬聲詞特別是擬態詞極其豐富,這些詞語成為朝鮮民族語言表達的基本詞匯,而象聲詞并不構成漢語的基本詞匯。二是源于作家創作個性的不同。姜敬愛具有真誠穩重的個性,善于運用樸實、貼切的形象化詞語;蕭紅具有單純率真的個性,擅長使用新穎、別致的陌生化語詞。三是源于作家對小說美學的不同追求。姜敬愛遵循傳統小說創作的規則,力圖使小說語言能夠傳達人物的真情實感;蕭紅則極力超越傳統小說美學,追求語言的傳神和意境之美,正因為如此,其小說語言風格被魯迅贊為“越軌的筆致”,能夠“力透紙背”。
[1] [韓]全容浩.《人間問題》的文體研究[A].金仁煥,等.時代與文學[M].漢城:自由之家,2004.116.
[2] 王觀泉.懷念蕭紅[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17.
[3] 張正華.論蕭紅創作中的女性意識[J].鄭州大學學報,2004,(4):2.
[4] 王運熙,顧易生.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上冊)[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81.
[5] 蕭紅.生死場[A].姜德銘.蕭紅卷(上)[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1.11,54,20,1.
[6] 蕭紅.呼蘭河傳[A].姜德銘.蕭紅卷(上)[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1.174,136,173,169,162,176.
[7] 蕭紅.手[A].姜德銘.蕭紅卷(上)[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1.311.
[8] 蕭紅.曠野的呼喊[A].姜德銘.蕭紅卷(上)[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1.331.
[9] [朝]姜敬愛.地下村[A].[朝]李相慶.姜敬愛全集[M].漢城:昭明出版社,1999.622,602,611,621.
[10] 蕭紅.小城三月[A].姜德銘.蕭紅卷(上)[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1.287-288.
[11] [朝]姜敬愛.其女[A].[朝]李相慶.姜敬愛全集[M].漢城:昭明出版社,1999.436,436,431.
[12] [朝]姜敬愛.鴉片[A].[朝]李相慶.姜敬愛全集[M].漢城:昭明出版社,1999.683.
[13] 蕭紅.廣告副手[A].姜德銘.蕭紅卷(下)[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1.272.
[14] [朝]姜敬愛.母與女[A].[朝]李相慶.姜敬愛全集[M].漢城:昭明出版社,1999.25,49,27.
[15] [朝]姜敬愛.黑暗[A].[朝]李相慶.姜敬愛全集[M].漢城:昭明出版社,1999.664.
[16] [朝]姜敬愛.長山串[A].[朝]李相慶.姜敬愛全集[M].漢城:昭明出版社,1999.650.
[17] [朝]姜敬愛.山男[A].[朝]李相慶.姜敬愛全集[M].漢城:昭明出版社,1999.639.
[18] 蕭紅.腿上的繃帶[A].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蕭紅小說全集(上)[M].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5.96.
[19] 蕭紅.家族以外的人[A].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蕭紅小說全集(上)[M].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5.154.
[20] 蕭紅.山下[A].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蕭紅小說全集(上)[M].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5.221.
[21] [朝]姜敬愛.破琴[A].[朝]李相慶.姜敬愛全集[M].漢城:昭明出版社,1999.425.
[22] 蕭紅.后花園[A].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蕭紅小說全集(上)[M].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5.323,323.
[23] 蕭紅.王阿嫂的死[A].姜德銘.蕭紅卷(下)[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1.262.
[24] [朝]姜敬愛.同情[A].[朝]李相慶.姜敬愛全集[M].漢城:昭明出版社,1999.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