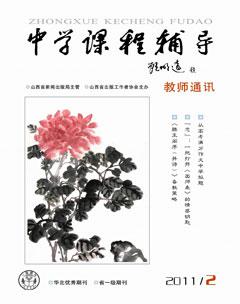談一堂好語文課認定的標準
張治平
新一輪課程改革對課堂教學創新的訴求,引領人們超越傳統的語文教學,逐步超脫了凱洛夫的“五步教學法”,直面千姿百態的新穎教學實踐。毋庸置疑,課堂教學是課改精神的直接體現,是課改精神的具體化。而對一堂好課的認定又關系到課改精神的真切解讀。對好課的認定實際上是對學科教學的一種評價。這種評價一旦形成共識,往往會成為一種潮流和時尚。可能正因為如此,所以自2001年,新課改起動以來,尚未有人具文論述好語文課的評定標準。
標準者,衡量事物的準則也。這個準則實在是不好定奪的,或者說是不能定奪的。不同的語文老師上課,會因為種種原因,風格迥異。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歷來的語文公開課的優劣就不好評價。因為不好評價,所以評課時,不少教師就喜歡跟在后面“和稀泥”,生怕說得不妥而得罪人。前不久到一所中學隨堂聽了十多節語文課,課后在一起評課的時候就碰到了這樣的情況。在大家唱了一陣贊歌之后,我具言道出了一位有著十多年教齡的老師課堂教學的不足。這節課他精心準備了,用了多媒體,但華而不實,學生實在是稀里糊涂地跟在后面熱鬧了一節課。正是見其誠,我才說出了真話。可是有幾位老師并不買賬,連說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讓我打心里不知道再說什么好。
事實上,新課改九年來,語文教學上的有些問題一直懸而不決,原因正在于課堂教學的評定問題把握不了,導致在類似于“工具性還是人文性”的問題上大造文章,使得一些本來淺顯的問題,給搞得復雜了,最后讓一線的語文教師不知道語文課該怎么上,只好穿新鞋走老路。其結果可想而知,不知害了多少人。
語文課堂教學無論怎樣改革,我想都有個本真的問題存在,也即是語文課堂教學要達到什么訓練目標的問題。錢理群先生認為,語文教學要把握住三點:一是情感,教學生熱愛母語,理解、感悟漢語言文字的特點;二是能力,運用母語的聽、說、讀、寫的能力;三是習慣,學習語文的習慣、良好學習的習慣、語言文明的習慣。這個本真的問題,我想是評定一堂好語文課的首要標準,也是根本標準。語文老師在課堂上到底做了什么,做得好不好,一般情況下,只要聽聽班上的學生說幾句話,寫幾句話,就能夠見其端倪。好的語文老師,教不出好的學生,再好也不叫好;再不好的語文老師,教出的學生呱呱叫,不好也好。
所以,我們評定一堂語文課好還是不好,這應是第一要考慮的。在這堂語文課上,學生學到了什么,掌握了什么,老師是怎樣引導學生掌握,如何進行有效訓練的,是不是一些淺顯易懂的方法,是不是一些輕松易學的道理。這些都要納入我們評課人的的標準之內,作為本真的問題來考慮。
《語文課程標準》上要求,課程目標要根據知識和能力、過程和方法、情感態度和價值觀三個維度設計。我看不少語文老師備課的時候,仿照市面上的有些教學參考書,備課時關于教學目標的文字寫得很多,有知識和能力目標,過程和方法目標,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目標,而如何達到這些目標,并沒有寫。這樣的備課不知道意義何在。我在想,我們的語文老師到底知不知道一堂45分鐘的語文課,能達到多少教學目標。實際上,一堂語文課能達成一個教學目標就很不錯了。在有限的時間里,我們語文老師能做的,就是圍繞這個目標不斷地設置障礙,讓學生進行“闖關”。年級不同,文本不同,教師設置的課堂教學目標應該不同。有些專家學者在討論語文學科的基本特點時,連這個問題都沒有搞清楚,就武斷地強調人文性重要抑或工具性重要。我想這是不對的。比如說《風箏》(人教版七上第21課)一文,那么多生字,作為語文老師就要把識字作為一個課時來學習,不僅要讓學生查字典注音,弄懂意思,還要訓練學生寫,用鋼筆寫出漂亮的方塊字來,為了檢驗掌握的情況,還要隨堂布置填詞和根據詞語寫話練習。好笑的是,現在的中學語文寫字沒有了任務,課本后面附錄上的書寫設置形同虛設,我們好多語文老師視而不見,反過來還說現在的學生寫字都寫不來。我不知道這個責任到底歸誰?如果上的是這一課,我們的老師不問生字詞,都像孫紹振老師一樣搞“文本細讀”,這樣的語文課好嗎?
顯然是行不通的。造房子是要打牢基礎的,學習又何嘗不是這樣。課程目標設計的三個維度并不等于每篇課文的教學目標。課程目標設計的三個維度里面,只有知識、過程與方法是顯性的,其它的是隱性的,針對不同的文本,我們的教學目標要有所不同,教師要根據學生的“最近發展區”不斷設置障礙,讓學生“學得”。這就要因時制宜,與時俱進。接受先進的教學理念,采用適切的教學方法,給予學生發展以個性教育和創造性教育。這是評定一堂好的語文課的標準之二。
接受先進的教學理念,采用適切的教學方法,這要由時代的發展所決定。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原理和方法。何謂“先進”?何謂“適切”?這都要根據課堂效率來取舍。用上某種方法,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好。比如上《荷塘月色》(人教版高中必修二第1課),文中有兩個句子:“微風過去,送來縷縷清香,仿佛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勻;但光與影有著和諧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著的名曲。”這是兩個運用通感的句子。通感,指感覺的轉化、遷移,如“你笑得真甜”,是將視覺轉化到了味覺,就是通感的用法。作為學生,這樣的句子,教師不點出來,可能還不曾注意,點出來一讀,就會覺得怪怪的,又覺得美美的。作為教師,要不要運用更多一些例子幫助學生理解和記憶?為了讓學生恰當靈活地掌握運用,要不要讓其品味、讓其仿寫呢?不僅要,而且還要讓學生終生不忘。能放手讓學生寫與評,這是教學理念的“先進”;通過舉例讓學生通曉和模仿,這是教學方法的“適切”。在45分鐘內,讓學生清楚領悟通感是什么,徹底掌握通感怎么用,難道這不好嗎?比起我們有些語文老師一節課,天上地上,洋里海里的,能扯上的都扯上,結果學生都是云里霧里,仿若隔靴搔癢不是更好嗎?語文課的聽說讀寫四個字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可并不簡單。比如聽話能力、說話能力。有多少語文教師敢說自己的學生“能說會道”。不能,為什么不能?給過學生機會了嗎?有些道理其實說起來就這么簡單,老師自己一味地在課堂上大講特講,回過頭來還非要說自己的學生沒有一個愿意舉手回答問題,甚至還要扯上其它的一些理由。試問,遇上這樣的語文課,我們是認為好呢,還是不好?
如果說標準一是需要“學得”哪些內容的問題,那么標準二就是“學得”這些內容的形式問題。一堂語文課上,學生不敢舉手回答問題,或者雖然是舉手站了起來,但聲若蚊蟲,而教師置若罔聞,這樣的課能不能說好?學生記筆記的時候,龍飛鳳舞,隨意圈涂,而教師視而不見,這樣的語文課算不算好?學生坐得筆直,一雙滴水的眸子緊盯老師的手勢,紋絲不動,這樣的語文課是不是好課?可是實際中,這樣的語文課堂占了大部分,而我們的語文老師還真是像我所寫的一樣,試問,我們備課中的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目標在哪里體現了出來?又在哪里達成了?
語文教學的綜合性非常明顯,比其它學科要突出,顯性的一面與隱性的一面常相伴相生。好的語文課要求教師能夠熟練地駕馭這一切。為達到上面兩條標準,教師的教學語言要求精煉簡潔、親和有力,富有磁性;教師的非教學語言,包括手勢和身姿要因需而為,與教學內容相一致。此謂教學的基本功。實際上,是一堂好課的前提。沒有這個前提條件,對上述兩點標準把握得再好,怕也是茶壺里煮餃子——道不出。這是另一個問題,此處不敘。
綜上所述,可以粗略地認為,一堂好的語文課的認定需要把握兩條標準:一是有無語文教學的本真存在,即是否把握住了語文課堂教學要達到的訓練目標;二是有無貫徹先進的理念、原則、方法,即是否把握住了個體發展的個性教育和創造性教育。
(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