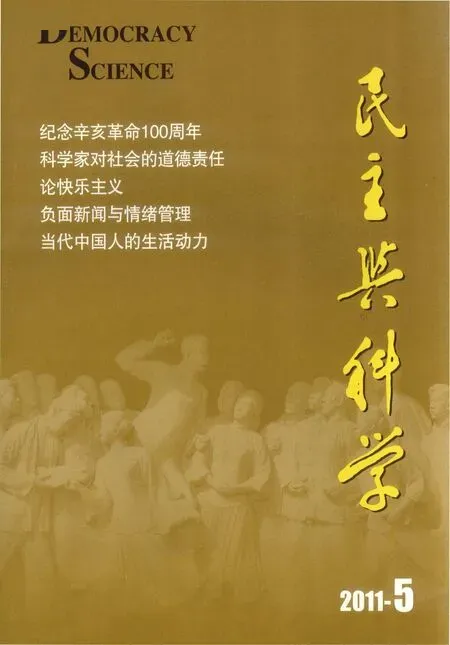“快”與“慢”的迷茫
■劉文寧
“中國 ,請停下你飛奔的腳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靈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讓列車脫軌,不要讓橋梁坍塌,不要讓道路成陷阱,不要讓房屋成危樓。慢點走,讓每一個生命都有自由和尊嚴,每一個人都不被‘時代’拋下,每一個人都順利平安地抵達終點。”
知名媒體人童大煥在“7·23”動車追尾事故后發出的微博,被網友海量轉發,并被引用于《紐約時報》報道中。
動車追尾,僅僅是一個爆發點。
快還是慢?今天,成了中國人思考的一個問題。
時光倒退幾十年,這一話題肯定被譏笑為癡人說夢——那時,我們沒這個資格。那時,我們的口號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19世紀末,美國人雅瑟·史密斯在《中國人的性格》一書中,用一個章節來寫中國人“漠視時間”。書中寫道:“無論如何,要讓一個中國人感到行動迅速敏捷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難的。”
再看一組人類出行速度提升的數字:18世紀,人類速度可達每小時6英里(約為9.6公里)左右,步行或乘馬車;19世紀,這一速度達到每小時60英里(約為96公里),因為有了火車;20世紀,噴氣式飛機讓我們實現了600英里(約為965公里)的時速——一個世紀跑快10倍,不可謂不驚人。
因此,超越時空的議論,會很天真,很滑稽。
一直加速前行的社會腳步,不是誰想叫停就能停下來的。在米蘭·昆德拉的筆下,“慢”是指沒有汽車電話的18世紀,出門要靠晃晃悠悠的馬車,信息要靠磨磨蹭蹭的信件,那時候有“古時候閑蕩的人”,“游手好閑的英雄”。而到了20世紀,那些悠閑“隨著鄉間小道草原、林間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
英國一項研究稱,世界都在進入“快生活”,全球城市人走路速度比10年前平均加快了10%,其中位居前列的幾個國家都是發展迅速的亞洲國家。
看看我們周圍,人人熱衷趕時間,到處都需要快節奏——手機在響,電話在催;最愛“快進”,狂點“刷新”;評論要搶“沙發”;寄信要特快專遞;拍照要立等可取;坐車選擇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做事最好名利雙收;理財最好一夜暴富;結婚要有房有車……人人風風火火,把每一天的日子過得如同打仗一般。只有快,才能賺到更多的錢,才能抓住機會,才不會被社會拋離。
于是,生產上,超強度、超能力、超定員;運輸上,超載、超速、超員;基建項目上,搶工期、趕進度、忙竣工。有些官員們,急于出“政績”,放松安全,大干快上,對非法違法和瞞報謊報行為視而不見……
這是一個受“快”裹挾的國家。
一位中國學者說,緊張的快生活是中國這代人避免不了的命運。中國就像正在快速成長的青少年,出現一些問題不完全是快速成長的錯,而是營養失去了平衡。中國的近鄰日本幾十年前也經歷過快速度帶來的“生長痛”,但真正令日本人擔心甚至絕望的卻是“失速的20年”。
雖然,“快”并不是這個世界惟一的尺度和標準。但哲學層面的問題放入現實中,其復雜程度超出人們的想象。
中國地域之大,人群貧富之不均,遠不是一個“快”或“慢”即可解決所有地區、所有人問題的。當“富二代”們為購置奢侈品而奔向國外的同時,“貧二代”們頭疼的則是如何“奮斗十八年與城里人一起喝咖啡”。
快還是慢?確實是個令人糾結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