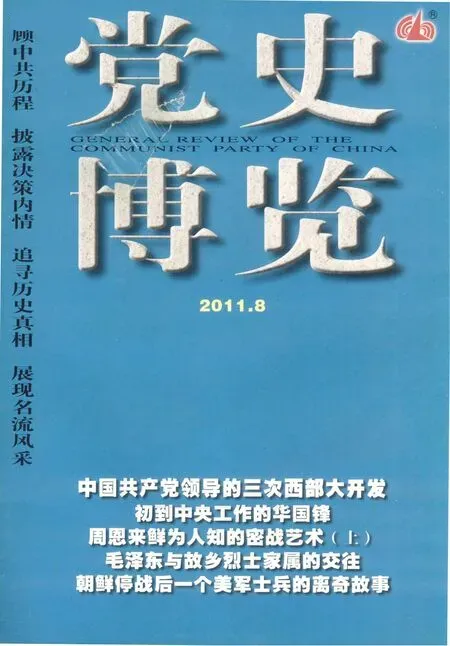中國海軍第一代國產艦艦導彈誕生始末
○吳殿卿
作為現代海戰中主要攻擊武器的導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誕生的。早在20世紀50年代,蘇聯、美國等技術先進的國家,多型導彈已廣泛裝備海軍部隊。而中國海軍,在差不多過了10年后才裝備了國產艦對艦導彈——“上游1號”。
艦對艦導彈,現通稱“艦艦導彈”,即水面艦艇裝備的巡航式反艦導彈,是艦艇的主要攻擊武器之一。為使海防擁有中國人自己的艦艦導彈,中國科研、軍工戰線的專家、職工和海軍試驗部隊官兵,走過了近八年的艱苦奮斗的歷程。
中蘇簽訂“二四”協定,將海軍導彈技術引入中國
1958年,人民海軍經過9年建設,水面、潛艇、航空、岸防等各兵種已陸續成軍,但在裝備上仍相當落后:繳獲、接收的原國民黨海軍的裝備不必說,即使新從蘇聯引進的護衛艦、掃雷艦等幾種型號的艦艇和裝備,也大都是蘇聯部隊已有了替代產品而基本停止生產的東西。
熟悉國外海軍發展情況的蕭勁光、劉道生等海軍首長清醒地意識到,要完成保衛海防、抗擊強敵入侵的任務,憑這些裝備是難以做到的。1958年4月,蕭勁光、蘇振華等海軍領導聯名上書國防部、中央軍委,建議由政府出面向蘇聯謀求海軍裝備新技術。其中特別提出,要爭取獲得核動力潛艇(時稱原子動力潛艇)技術和海軍導彈技術。
周恩來等軍委領導很快批準了海軍的建議,并出面與蘇聯政府聯系。在征得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同意后,中國政府于1958年10月派出了一個以海軍政委蘇振華為團長、多名國務院工業部門領導參加的專家代表團赴蘇會談。
當時中蘇兩國關系非常好,但談判并非一帆風順。關于引進核潛艇、導彈驅逐艦制造技術的請求,一開始便被斷然拒絕;關于海軍導彈及裝備導彈的幾種小型艦艇的制造技術,雙方各層次經過3個多月的反復會談、磋商,最后達成協議。
1959年2月4日,蘇振華和蘇聯部長會議對外聯絡委員會副主席阿爾希波夫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關于蘇聯政府給予中國海軍制造艦艇方面新技術援助的協定》(史稱“二四”協定)上簽字。
這一協定規定,蘇聯政府向中國海軍提供“629”型導彈潛艇、“205”型導彈快艇等5種型號的艦艇制造技術資料及部分建造材料、設備,同時提供兩種型號的海軍導彈,即“629”型導彈潛艇用P-11фM彈道式導彈(潛地)、“205”型和“183P”型導彈快艇用п-15飛航式導彈(艦艦)的制造技術資料、導彈樣品,及相關的技術陣地設備、工藝測試設備。
“二四”協定簽署后,海軍首長非常高興。大家清楚,蘇聯提供的艦艇技術雖不是最先進的,但裝有導彈發射系統,國內短期內難以研制生產。提供的兩種導彈技術,則毋庸置疑屬尖端武器裝備范疇,是非常難得的。1959年6月,海軍黨委便作出決定:在海軍裝備建設方面,主要抓“二四”協定項目,以便在消化、掌握此前引進的幾種型號艦艇技術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和發展;海軍武器裝備系統建設,以發展導彈為主。
困境中被列為國家重點項目,進行非同尋常的“仿制”
1959年11月,按照中蘇“二四”協定引進的導彈樣機運抵北京。此前,為集中抓“兩彈”,即潛地、艦艦導彈仿制而成立的直屬海軍首長領導的海軍技術部,業已正式成立。導彈仿制準備工作遂逐步展開。
鑒于當時尚沒有專門的海軍導彈研制、生產單位,軍委、國務院領導指示,集全國科研技術力量搞好兩種型號的海軍導彈仿制。在分管國防科委的副總理聶榮臻和分管國防工業的副總理賀龍的參與協調下,對海軍導彈仿制進行了責任劃分。整個仿制工程,以海軍、國務院第三機械工業部和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等單位為主進行。具體分工,海軍負責樣機、資料的引進及提出仿制意見和建議;五院、三機部分別負責仿制生產設計研究,解決技術難題和安排生產。此外,海軍還負責了解掌握全面情況,組織協調工廠和科研單位間的協作,并派出駐廠軍代表進行仿制監造等工作。
1960年3月,潛地、艦艦兩種導彈仿制工程先后正式啟動。按照“二四”協定的規定,蘇聯在提供相應資料、技術圖紙的同時,還要派出專家、技術人員對關鍵性生產、使用環節給予技術指導。據此,海軍技術部聘請了以施烈米爾為首的6名蘇聯專家,分別擔任導彈裝備的戰斗使用、射擊指揮儀、彈體、火工品及地面設備等方面的技術顧問。研究院所、生產廠家也分別聘請了相關技術人員。
仿制開始時,各方面的蘇聯專家、顧問均已到位。這些專家、顧問,大都是從事導彈研制工作的技術骨干或軍隊中有實際工作經驗的軍官。他們技術熟練,工作熱情高,且非常負責任。在他們的幫助指導下,導彈仿制工作進展很快,短短幾個月的時間,科研院所、軍工廠、海軍部隊等各單位,就按照各自的職責任務形成了從仿制研究、部件生產到飛行試驗等一套系統的組織機構。
但是不久,由于中蘇兩黨政治分歧等原因,蘇聯政府于1960年8月單方面撕毀了兩國所有援建項目的合同,召回了全部在華工作的專家、技術人員。軍隊和地方參與海軍導彈仿制的技術人員,也先后撤回。同時,“二四”協定停止履行,很大一部分重要的技術資料,蘇方不再提供。加之連年自然災害等原因造成的經濟困難,使需要大量經費支撐的武器裝備研仿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
困難面前,國防工業委員會根據中央關于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決定對國防工業采取“縮短戰線、保證重點”的政策,暫停和削減一部分科研生產項目。
根據這一精神,海軍黨委對導彈仿制任務進行了慎重的研究,決定暫停潛地導彈和先行開始的岸艦導彈的研仿,集中力量完成艦艦導彈,即“п-15”飛航式導彈的仿制任務。
國防工委接受了海軍的意見,同時,考慮到資料和技術人員的不足,批準了三機部關于延長國產艦艦導彈交付部隊期限的報告,將國產艦艦導彈交付時間,由原定的1963年推遲至1968年。
調整后,艦艦導彈仿制被列為國家重點項目,生產代號為“5081”工程,仿制定型的國產艦艦導彈命名為“上游1號”。
項目保留下來了,但由于蘇聯專家、技術人員撤走,圖紙、資料不全,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仿制了,許多東西需“研制”、“創制”。
在科研院所、軍工廠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下,軍地雙方參研人員不分晝夜地跑圖書館、下車間,查找資料,集體攻關,解決仿制中的技術難題。通用資料,分頭在國內相關單位查找;查找不到,有些專用資料也不可能有,則按實物測繪,照樣機進行“反設計”。
不少單位把技術人員組織起來,通過消化已有的資料,上專業課,反復拆裝進口樣機及對成件、全彈進行單元和綜合測試等方法,解決技術難題,培訓技術骨干。
解決圖紙不易,把圖紙變成部件更難。由于沒有專門生產廠,艦艦導彈仿制生產是由航空、兵器、電子設備等幾十家工廠分頭承擔的。“反設計”的圖紙有的難免有誤差,加上缺少專用設備、特需材料,技術、工藝也要邊干邊摸索,每一個部件的生產都可謂“難題重重”。為了攻克這些難題,做到既節約材料、節省時間,又保證進度,各生產廠普遍采取了科研、生產、使用三結合,車間設計員、工藝員、工人三結合的方式,本著先易后難、循序漸進的原則,一步步攻關。有的問題一個廠解決不了,就打破廠際界限,幾個廠的技術人員攜手攻關。結構復雜、要求精密的艦艦導彈的每一個成件生產,都經過由不同尺度的縮比到1∶1的反復試驗。有的部件經過上百次、幾百次甚至上千次試驗,歷時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最后才試制出符合設計要求的成品。
40多年過去了,參與過“上游1號”艦艦導彈仿制生產的技術人員、老工人,講起當年的情景,依然激動不已:“那時,為了搞出一個合格的部件,通宵達旦是常事。有時忙起來,沒有上下班的界限。領導的工作不是動員加班而是勸大家休息,好多同志是夜里偷偷干。”“連續十天八天加班,沒有一個人叫苦說累,只是為浪費材料心痛,為不能提前進度心焦。國家窮啊!”
海軍技術部牽頭組織人員深入工廠“一學、二幫、三監督”
海軍機關對“5081”工程高度重視。1961年初,為加強對艦艦導彈研仿的領導、管理,海軍專門發了指示。文件在要求機關業務部門加強導彈知識學習,積極主動配合做好導彈研仿和試驗工作的同時,要求海軍技術部牽頭組織人員深入工廠,對承擔仿制任務的單位實行“一學、二幫、三監督”。
在征得國防工委、國防科委批準后,由海軍技術部、訓練基地、炮兵學校等單位抽調的174人組成工作隊,分別深入到承擔生產任務的26個工廠,一邊進行專業學習,一邊協助落實生產任務。
這批工作隊成員在廠里學習、工作大都半年左右的時間。他們發現好的經驗和做法,幫助總結推廣;了解到完成任務有困難,及時向上級反映,協助解決,深受工廠歡迎。
海軍技術部處長張毅民等人在某廠學習工作期間,通過對裝備仿制研究及試驗靶場建設等情況的調研,寫出了《關于“5081”艦對艦導彈仿制程序的建議》,具體提出艦艦導彈仿制分三步走:
由于農民知識技能少,紅寺堡區農業新技術的轉化與應用困難, 技術問題成為制約一些優勢特色產業快速發展的瓶頸。此外,由于人力資本存量低,很多扶貧資金由于操作、開發不當,不僅沒有產生遞增效應,反而使這些投資損失殆盡,有些甚至還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陷入了“人力資本水平低—素質技能不強,難以進入資本市場,沒有創新精神—貧困”的惡性循環之中。
第一步,以國內現有設備條件生產模型彈。即導彈的殼體,用以同導彈快艇和進口導彈成件進行協調,促進導彈成件的仿制。且可用模型彈發射,檢驗快艇甲板及其上層建筑的強度和對人體安全的影響。
第二步,生產混裝彈。即將國產件和進口成件、設備互相混裝,以檢驗國產件并和進口件對比校驗,同時為國產的關鍵成件攻關贏得時間。
第三步,生產國產導彈,達到定型標準。
海軍技術部對這一建議很重視,專門派人向國防工辦(1961年11月成立)、國防科委和三機部領導作了匯報。 1964年6月20日,國防工辦以《“上游1號”艦對艦導彈仿制程序》為題批轉各相關單位,要求據此實施。
經過三年多邊試邊干,到1963年底,各承制廠生產出了第一批零、組件。翌年3月,艦艦導彈總裝生產和總體歸口單位320廠開始組裝。與此同時,三機部在320廠召開各承制廠廠際協調會,明確了各廠生產進度具體安排及其對使用單位的要求,各廠之間進行了技術協調。
按照蘇聯技術資料要求,所有成件(含火工品)全部交總裝廠,再由總裝廠負責交付使用單位。這樣做,使用單位簡單、省力,但從整體上增加了中間環節和儲運費用。
聽取相關各廠意見后,海軍技術部提出,助推器(含藥柱、藥盒)、引信等易爆危險品和其他部分質量有保證,互換性能好的成品,經所在廠軍代表驗收合格后不必交總裝廠,可以由承制廠直接發往部隊。這樣可以減少中轉環節,節約時間、經費,且有利于保障安全。這一提議得到與會人員的一致贊同。
后來,這種交付方式也被海軍其他型號導彈采用,一直沿用下來。
審慎、嚴格的飛行試驗,三個階段試驗均獲一次性成功
至1964年,艦艦導彈生產中關鍵環節的技術難題,已基本上被攻克,接踵而來的是飛行試驗問題。
模型彈飛行試驗
第一階段試驗是模型彈飛行試驗。為方便具體了解掌握各項試驗參數,試驗分陸上、海上兩次進行。首先“以沙代海”,在陸地試驗,然后再在海上試驗。
陸地試驗,于1964年12月在西北戈壁灘上國防科委某試驗基地進行。試驗前,在發射場地安裝了固定發射架和模擬快艇甲板及艇面設備,在發射架周圍和“艙室”不同部位放置了羊、狗、豬等動物,配置了有線測量和光測設備。12月7日上午9時,隨著指揮員“發射”口令發出,第一發模型彈拖著火光和濃煙滑出軌道,銀白色的彈體在金色陽光照耀下按預定彈道飛去。發射結束,察看發射架周圍被助推器火煙考驗過的動物,因距發射架距離不同而死傷各異。模擬艙室內的動物,均安然無恙。設計人員和各生產單位領導還一起察看了模型彈的落點:戈壁灘上沖擊出一個直徑數米的大坑。破碎的彈片四處飛濺,最遠處達數百米。
11日上午9時,又發射了第二發。按試驗大綱收集各種結果、數據,情況與第一發基本相同。
兩發試驗結果證明,模型彈助推器工作正常,彈體結構強度符合要求,各種參數符合試驗大綱要求。
海上模型彈飛行試驗,于1965年10月由海軍試驗基地組織在渤海某海區進行。試驗場設在基地試驗靶場,以快艇某支隊的國產“6621”、“6623”型快艇各一艘參加試驗。
艦對艦,即從艦上發射打擊敵艦,是“上游1號”導彈的“使命”。海上試驗才是真正的試驗。試驗前,專門成立了“上游1號”導彈定型飛行試驗臨時黨委。相關科研單位、工業部門和海軍機關、部隊,分別派人參加,海軍試驗基地司令員鄭國仲任書記。臨時黨委遵照周恩來關于新武器試驗必須做到“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指示精神,多次召開會議,研究模型彈海上試驗準備工作。各單位主要領導深入試驗第一線,嚴格按技術要求抓試驗每一個環節工作落實,確保不帶著問題上天,不帶著疑問發射。
試驗于10月15日正式開始。
首先是停泊(又稱系泊)試驗,即將發射艇固定在一定方向上,艇上不上人,在艇上應有人操作的地方放置猴子等動物,由操縱人員在另外一艘艇上遙控發射。第一發模型彈發射后,臨時黨委仔細研究了隨艇試驗的動物,發現除驚恐外沒有一只受外傷。于是,臨時黨委決定發射第二發模型彈時派一個人上艇,具體了解模型彈發射的噪音和沖擊波對人的神經系統和精神上的影響。
親臨發射艇感受發射試驗,危險是明顯的。但現場的官兵們毫無畏懼,共產黨員、技術骨干紛紛報名,請求上艇參加試驗。臨時黨委經過慎重研究確定,基地試驗部干部王照奉留在艇上。
經過認真細致的準備,再次發射試驗開始了。隨著一聲巨響,模型彈騰空而起,呼嘯著沖云破霧向海上的目標艦飛去。“直接命中了!”遙控發射艇上的人們高興地喊出聲來。稍頃,大家想到了留在艇上的王照奉的安全,迅即操艇向發射艇靠去。未等靠近,便見有人從艙內沖出來,伸開雙臂高呼:“成功了!我們勝利了!”大家一看,不是一人而是三個人——除了王照奉外,還有基地試驗部政委申愛華,參謀朱耀洲。原來,申、朱兩人要求上艇參試臨時黨委沒有批準,他們便在上發射艇作試驗準備時趁人不注意偷偷藏在艇上,直到大家都離開發射艇時,王照奉才發現他們。王照奉強烈要求他們離開,申愛華堅決制止了他:“不要嚷了,我們決心留下,再說船也開了。我是你的領導,你要聽我的。”
兩次停泊試驗后,又進行了航行發射試驗,即在艦艇正常航行狀態下發射模型彈3發,也取得圓滿成功。
11月15日,整個模型彈飛行試驗結束。
通過停泊、航行先后兩次發射5發模型彈試驗表明,模型彈在導軌上滑行順利,助推段飛行正常,彈體結構完整,艇體強度和艙室防護可靠,艇上官兵安全。
混裝彈飛行試驗
模型彈飛行試驗成功后,艦對艦導彈仿制試驗就順利進入第二個階段,即混裝遙測彈飛行試驗。
所謂混裝彈,即導彈各部的國產件和進口的成品件、設備,相互交叉混合裝配,每發彈中都裝有多少不一的國產件。通過發射這些混裝彈,將國產件與進口件對比,檢驗國產件的質量和效能。
試驗于1966年4月開始,7月初結束。試驗也分兩個步驟進行,先在陸上對海上目標發射,后在快艇上發射。
在準備發射的混裝彈中,有一發彈原來只有自動駕駛儀一個部件是進口成件,其余均為國產件。連續發射幾發混裝彈后,臨時黨委現場決定,將這發彈的自動駕駛儀也換上國產件,使其成為完全的國產彈,進行發射試驗。
1966年6月26日,這發彈發射升空,直接命中了目標。這一結果明白無誤地宣告:中國第一枚國產艦艦導彈仿制成功了!“上游1號”成功了!現場參試人員無不欣喜異常。大家歡呼、跳躍、握手、擁抱,不少同志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混裝彈飛行試驗,共發射6發,5發命中目標。特別是其中的國產彈直接命中目標,實際上已經給艦艦導彈仿制畫上了圓滿的句號。但科學試驗容不得半點馬虎,艦艦導彈飛行試驗第三階段,即國產彈定型飛行試驗依然按計劃進行。當然,準備工作步伐大大加快了。
國產彈定型飛行試驗
國產彈定型飛行試驗,于混裝彈飛行試驗4個月后,即1966年11月在某部海上試驗靶場舉行。10月中旬,導彈發射艇和觀察照相的直升機進駐試驗靶場,試驗彈也相繼運到。定型飛行試驗,是全面檢驗國產導彈性能是否符合戰術要求,能否裝備部隊的最后一關。整個試驗均按照實戰的要求進行。為確保試驗 “萬無一失”,試驗基地司令員鄭國仲、副司令員楊國宇等各級領導都到了試驗場,與專家和參試部隊一起現場解決問題。海軍參謀長張學思在試驗發射前一天趕到試驗部隊,檢查了試驗準備工作,參加了定型試驗的全過程。
11月9日,風和日麗,能見度高,是飛行試驗難得的好天氣。下午2時,第一發彈準時發射。觀測證明,理論命中。這一效果堅定了參試人員的信心。接下來,從11月14日至29日上午,又發射了6發。為了檢驗發射艇的承載能力和對導彈的影響,29日下午,兩舷同時發射。雙彈齊射,巨大沖擊力掀起的氣浪,沖破了快艇厚厚的玻璃窗,濃煙灌進駕駛室,艇上人員除輪機兵頭部負輕傷、標圖員被震昏迷外,其他人多無大礙,而兩發導彈全部命中目標,靶船被打沉。至此,“上游1號”艦艦導彈定型試驗,以9發8中的優異成績宣告結束。
試驗報告中,詳細記述了整個定型試驗的過程,對每發彈飛行的觀察、測量和試驗結果,進行了詳盡的分析。最后結論:“上游1號”艦對艦導彈設計方案是正確的,仿制生產質量是好的;試驗基地技術陣地、發射艇準備細致周到,各種測量和時統設備工作良好,組織指揮嚴密;各參試單位團結協作,配合密切。國產艦艦導彈“上游1號”質量、性能可靠。
“上游1號”定型生產、裝備部隊,成為一代海防武器裝備的中堅
按照試驗程序,完成模型彈、混裝彈和國產彈三個階段試驗后,“上游1號”導彈仿制進入最后一個環節——定型生產。
此前,在著手準備定型飛行試驗的同時,另一項試驗,即全彈和成件運輸試驗也在進行。
導彈的各個部件由分布全國的若干廠家分別生產。各部件從這些廠到總裝廠,成品導彈從總裝廠到戰斗部隊,須經過公路、鐵路、水上等多種環境條件的長途運輸。運輸中對部件、全彈質量、性能有無影響?安全與否?只有通過運輸試驗才能掌握第一手資料,了解其在各種運輸環境中的適應能力。這一試驗于1966年夏季開始,直到翌年夏結束,進行了整整一年的時間。這是一項非常艱苦而又默默無聞的工作。廣大參試人員為保護“特運”、掌握第一手資料,頂酷暑烈日,冒嚴冬風雪,有時連飯都吃不上,水都喝不上,但都圓滿完成了試驗任務。
1967年6月28日至7月1日,“上游1號” 艦艦導彈定型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由海防導彈臨時定型委員會主任、海軍副司令員趙啟民主持,定委會副主任錢學森、鄭國仲、來光祖、黃志才及全體委員出席會議。會議聽取了三機部、海軍關于“上游1號”艦艦導彈的仿制生產報告和飛行試驗報告,充分肯定了“上游1號”艦艦導彈仿制生產和飛行試驗中的成績,討論了設計、生產中應當改進、解決的問題。會議認為,“上游1號”艦艦導彈設計方案正確,二類產品(各成件)符合設計要求;一類產品(全彈、整個武器系統)性能良好。國產“上游1號”導彈質量、性能可靠,可以批量生產,裝備部隊。大家一致通過了上報國務院特種武器定型委員會的 “上游1號”導彈生產定型申請報告。國務院特委也很快批復,同意批量生產。
“上游1號”導彈定型投產后,首先裝備了海軍快艇部隊。接著,又對在役的護衛艦和驅逐艦加裝“上游1號”導彈武器系統。一段時間里,國產艦艦導彈“上游1號”,成為新中國海軍部隊海上攻擊武器的中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