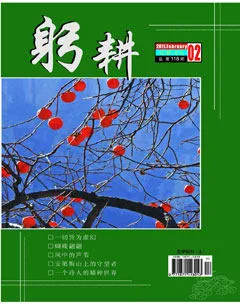蝴蝶翩翩
1
勤務兵小黑子來的時候,我看到他的肩上站著一只蝴蝶。我說,你肩上有只蝴蝶。他回過頭看了看,說,沒有啊。我眨了眨眼,蝴蝶不見了。我充滿疑惑地看著他瘦得冬天的樹皮一樣的臉,也許我眼睛看花了?
小黑子的聲音里充滿丟失已久的喜悅,說:“連長,太陽出來了!”
我出來一看,太陽果然出來了。金色的陽光像一層層蚊蠓密密麻麻地飛過來,我把眼睛閉上的同時,朝著浸泡在戰(zhàn)壕里的弟兄們吼了一聲:“準備戰(zhàn)斗!”
天氣一晴,仗就會接著打了。硝煙會爬滿我們的身體,從眼睛、嘴巴鉆進五臟六腑,把我們的血肉噬光,只剩下慘白的骨頭,與泥土和荒草混在一起,在月夜里散發(fā)著磷火。我看過地方志,大牛山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這地方晚上總是有凄慘的磷火閃爍,有無名的幽靈在地下哭泣。開進大牛山的第一個晚上,小黑子看到滿山的磷火時,居然嚇得哭了。我給他講了很多次,沒有一點用,他總說那是鬼火。
我告訴他說,我們遲早都會變成那樣的。從前他都不信,但這一次,看到山下一層層解放軍把大牛山嚴嚴實實地包圍了,他信了。不過,他又說,他不想在大牛山做鬼,他想回到老家黃地,他就是死了,骨頭也要回去。我笑著安慰他說,沒事的,你只是一個小兵,解放軍不會怎么著你的,應該擔心的倒是我們這些軍官。他的眼睛淚光閃爍,嘴巴抽搐兩下,低低地說,連長,那我就和你死在一起。
我笑笑說他真傻。那是一支和我們一樣的正規(guī)軍,怎么會殺俘虜呢?何況,我根本就沒想過被他們俘虜。我希望解放軍能說話算話,愿意回家的就給路費。這樣的話,如果我戰(zhàn)死了,小黑子就可以把我的尸骨帶回老家,埋在父親的墳旁,也許有一天,妹妹會撥開墳前的萋萋荒草來看我。
解放軍開始進攻了。他們吹著沖鋒號,高聲地叫喊著,從四面八方向大牛山?jīng)_鋒。在那些把云彩撕得破破爛爛的吶喊聲中,夾雜著一些稚嫩的帶著哭腔的聲音。他們當然也是害怕的,所以,他們要在沖鋒時故意扯著嗓子吼著,讓我們以為他們不害怕。實際上大家都怕得要死。我們每個人都沒動,但被淹在水里的雙腿卻在一個勁地顫抖著,戰(zhàn)壕里的水像是即將煮開的水一樣劇烈地晃蕩著。他們都在咬牙控制著,臉上肌肉抽搐,汗水像灰色的蚯蚓一樣爬著,可能是因為天氣太熱,也可能那是比死亡更冷的冷汗。
解放軍已經(jīng)接近陣地了,他們急促的腳步落在地上,像無數(shù)只狗啃咬著大地,震得戰(zhàn)壕上的土簌簌地往下掉,就像在水里扔了一層的鈉,水真的就要沸騰了。信號彈突然升向半空,像拖曳著尾巴的花朵一樣在空中盛開。我用盡全身力氣吼了一聲:“打!”嘴巴里有股咸味,也許是把喉嚨撕破了。所有的士兵都從水中站起來,所有的槍都架在了戰(zhàn)壕上,所有的槍都開火了。那些解放軍就在不到百米的距離上,就像豎在田野里的麥捆,前面的一倒,后面的也跟著倒了,有些是被我們擊中了,有些是有意臥倒的,有些還沒反應過來,還悶著頭往前沖,身上被子彈啃出一個又一個洞,他們雙手在空中亂抓,跳著怪異的舞蹈。
那些瘋狂奔跑著的麥捆消失了,所有的解放軍都臥倒在地上向我們匍匐過來。這很討厭,我們要想打中他們,不得不把自己的身子更多地探出來,這樣很容易被他們的子彈找到我們的心臟。很快,不斷地有人栽倒在戰(zhàn)壕里,身上的手榴彈和子彈袋把他們拖進水里,他們還不甘心地往外吐著血,很快就把水也染紅了。我趴在機槍手旁邊,指揮著他往人群密集的地方射擊。他抱著機槍,就像抱著他的老婆,機槍的后坐力把他的身子弄得不停地抖動著,他咬著牙一聲不吭,就像和女人做愛一樣既投入又吃力。我剛要夸獎他一下,一顆子彈呼嘯著撲到他臉上,紅色的鮮血從眼睛里飛出來,帶著黑色的瞳仁,掉在機槍上,就像上面落了一只紅色黑色白色相間的蝴蝶。我剛要把他拉過來包扎一下,他卻像到了高潮一樣身子猛地向上一躥,更多的子彈打過來,他臉上的碎肉都濺到了我的臉上,像鐵匠鋪里濺出來的火星一樣燙燙的。我把他拔拉到一邊,正要準備自己抱著機槍打時,小黑子竄過來,搶著趴在那里,說:“連長,讓我來打!”
我知道他這是為我好,機槍手在戰(zhàn)場上總是引人注目,好多的子彈都像發(fā)情的少婦一樣想往他懷里鉆。我退到一邊,心想,等這仗打完了,我要給小黑子找個對象成家。他年齡不小了。說起來,我倆其實都是一起在黃地長大的。我父親是老爺,他父親是佃戶。不過,向老天發(fā)誓,我早就把他當做自己的親兄弟了。
將近五十米左右的距離,更加刺耳的沖鋒號響了。解放軍從地上跳起來,像海水一樣洶涌地吶喊著沖過來,大地像蝴蝶的翅膀在微微顫動,他們腳上帶起來的泥巴像花朵一樣盛開。士兵們沖出戰(zhàn)壕,雙方短兵相接。子彈從四面八方飛過來,手榴彈跳來跳去地在周圍不停地爆炸。我的一排長倒很勇敢,一直沖在我前面,我剛要叫他注意點,他猛地竄了起來,飛到了半空。我低頭一看,他原來踩著了一捆集束手榴彈。我剛跑兩步,有東西絆住我的腳,低頭一看,一排長的上半身就在我的腳下。他臉朝下,一動不動。我正猶豫著怎么辦時,一個小個子解放軍撲過來,把我摔在地上。我的衣服上濺滿血跡,血水滴滴答答地往下掉,衣服貼在身上粘糊糊地難受,脖子上也是血,他的手卡在上面很滑,雖然把我卡得直翻白眼,但還不至于喘不過來氣。他扼不死我,這讓他很委屈,眼睛里淚水都快出來了。我本來以為自己要死了,沒想到他力氣這么小,還當什么兵啊?我掙扎著抓起一把泥巴,掙扎著糊在他眼上,他手一松,我就翻過身來,把他壓在身下,雙手卡住他的脖子。他的脖子那么細,還那么白,這哪里像個士兵,簡直是個女人嘛。他的雙手在空中亂抓,甚至還抓到了我的臉,我感到臉上火辣辣的疼。這個像女人一樣的士兵徹底激怒我了,我把全身的力氣用在手上,他的臉憋得通紅,腦袋使勁地晃著,洗得發(fā)白的軍帽被他甩在一邊,露出長長的頭發(fā)。這真是個女人!我的嘴巴大大地張著,兩只手還卡在她的喉嚨上,但與其說是要扼死她,不如說是在撫摸著她。手上的血液凝固了,軟軟地耷拉在那里,蒼白得像死去的士兵的臉。我從她身上爬起來,猶豫著要不要伸出手把她拉起來。我看清了,她長得并不漂亮,臉盤子很大,涂滿亂七八糟的黃色泥巴黑色硝煙,而不是像我妹妹,臉像涂了奶油,又白又有香味,小時候,我總是趁她不備,把嘴巴猛地湊到她臉上去聞那香味。為了這事,我沒少挨媽媽的罵、父親的打,但我從來都沒有后悔過,一直到她長大了,我才改掉這個壞毛病。這個解放軍女兵不可能是我的妹妹。但在那一刻,我的確是把她當做了妹妹。我也許是被他們的槍聲和吶喊聲震昏頭了,我伸出手,把她拉了起來,喃喃地說:“你怎么在這里?”
那個解放軍女兵瞪著眼睛看著我,好像我是個怪物。我的目光柔軟,仿佛她不是一個敵人,而是一朵可以吃的花。雖然她裝作不認識我,但我還是認出她來了,這是我的妹妹!這么多年不見了,她的變化這么大,身子胖了,臉也圓了,也黑了很多,眼角邊還有了蒼老的魚尾紋。真不知道她是怎么過來的。我緊緊地拉著她的手,再也舍不得丟開了,我怕一丟開,她又不見了。
但她還是掙開了我的手,往旁邊一跳,臉轉(zhuǎn)向我,沖著我大聲地喊著什么,但她的聲音被戰(zhàn)場上的硝煙和劃過頭頂?shù)臉屄暋⒋踢M肉體的刺刀聲擊得破破爛爛。她很著急,使勁地沖我揮舞著胳膊。我終于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是想讓我趕緊逃跑。我也想跑,但泥巴纏著腳,一點力氣都沒有,整個身子軟軟的。她搖了搖頭,轉(zhuǎn)身消失在了硝煙中。整個戰(zhàn)場模糊不清,槍聲炮聲仍然在濃重的空氣中顫動,后來變得越來越遠了,我聽到蝴蝶扇動翅膀劃過空氣的沙沙聲,聽到遠處樹上傳來咕咕的鳥叫聲。陽光從黏稠的硝煙中鉆出來,當它照在我的額前,我突然想起她的容顏,她像我的妹妹,似乎又不像。那么,她為什么要沖著我揮舞著胳膊,而不是丟過來一顆手榴彈呢?她認識我嗎?她是誰?她為什么要這樣做?
一顆子彈擦著耳朵飛過,熾熱的火藥灼得耳根發(fā)麻,但路過我的耳邊時,它又變成一道閃電劃過我的腦袋。我突然想起,這個解放軍女兵,會不會就是半年前我遇到的那個娟子呢?戰(zhàn)場上子彈與硝煙消失了,娟子的臉龐從歲月的水里浮上來,那么清晰,我甚至能看到她眼睫上掛著的晶瑩的淚珠,聽到她埋在心里的哭泣……
2
半年前的時候,我們部隊一直在到處尋找解放軍主力決戰(zhàn),但他們像夏天的一顆水滴落在水里,怎么也找不到他們。在崎嶇的山區(qū)里轉(zhuǎn)悠一個多月,我們最大的收獲就是抓到幾個掉隊的解放軍士兵,但毫無用處,他們和我們一樣也在尋找他們的大部隊。
那是一個黃昏,我們來到一個破爛的村莊。我們連隊作為先頭連,第一個進入村莊,并且找到了一座高大的磚瓦房子。玫瑰色的天空下,這座古老的宅院安靜而又美麗。這一家人和我們家一樣,應該是村里的大戶人家,能讓疲勞的士兵在這樣的房子里度過一個夜晚,我這個當連長的當然很高興。我讓小黑子上去敲門,他抓著閃亮的門環(huán)拍了半天,那扇門像死去了一樣毫無反應。士兵們等不及了,他們把門板摘下來,院里站著一個老太太,瞪著眼睛吃驚地看著我們。我忙安慰她說:“老大娘,你別怕,我們是國軍,不是共匪,在這住一晚上就走,會給你錢的。”老太太皺巴巴的臉上立刻露出笑容,恐懼與驚慌被笑容擠掉在地上,滲進土里,沒有一點痕跡。她充滿喜悅地說:“長官好,長官好……我兒子也是國軍!”
我一下子覺得這個老太太無比親切起來,甚至覺得她像我的奶奶一樣慈祥。我好奇地問她,你兒子在哪個部隊?她告訴了我,我有點失望,她兒子是地方保安團的,雖然還是個大隊長,但我們正規(guī)軍是從來都沒正眼看過他們的。那就是一幫烏合之眾,像骯臟的虱子一樣令人討厭。老太太把我讓進屋里,屋里正中間是一個用土坯壘起的臺子,上面放著一些點心盒子什么的。奇怪的是,臺子和墻之間的角落里蜷縮著一個婦女,她蹲在地上,頭埋在膝蓋上,頭發(fā)像堆雜草一樣,整個身子在簌簌發(fā)抖。老太太走過去踢她一腳,惡狠狠地說:“死到一邊去!”她慌慌地抬起頭,臉色比陰天的天空還要灰暗,比旱災到來的土地還要干枯。她怯怯地看看那個老太太,又愣愣地看著我,目光落在我戴的鋼盔上,上面有青天白日帽徽,目光又滑到我的衣領,上面綴著閃亮的中尉軍銜,她不像別人那樣目光躲閃,相反,干癟的眼睛里閃過一絲微弱的亮光,像無邊的夜色里一只孤獨的螢火蟲若隱若現(xiàn),她的嘴唇神經(jīng)質(zhì)地哆嗦著,聲音比蜘蛛絲還要細小虛弱:“救我……救救我……”
老太太立即沖過去又狠狠地踢她一腳,嗓子像破鑼一樣叫道:“你別做美夢了,你看看,這可是國軍!”
她的行為讓我厭惡。我把她撥拉到一邊,彎下身子問那個婦女,這是怎么回事?她抬頭看著我,像朵枯萎的花一樣的眼睛突然有了生機,小心翼翼地試探著是否要綻放。她伸出枯瘦的手抓住我的胳膊,好像用盡了全身的力氣,幾乎要把我?guī)У乖诘厣狭恕N颐Π阉饋怼K纳碜訐u搖晃晃,就像屋頂上營養(yǎng)不良瘦弱的樹苗,一陣風吹來就可以把它吹折了。我扶著她坐在椅子上,在她顫抖的聲音里,在老太太兇惡的叫喊聲中,我終于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叫娟子,是一名解放軍女兵,一個月前跟隨工作隊在鄉(xiāng)村土改時,被保安團襲擊,隊員全部犧牲,她被抓到后,這個老太太的兒子,也就是保安團的大隊長,強迫她當了他的小老婆。
老太太討好地看了看我,然后又撇著嘴充滿鄙夷地看著她,惡狠狠地說:“你別做美夢了,國軍會救你?哼哼,我看他們還會殺了你呢……”
我皺著眉頭,充滿厭惡地看著這個鄉(xiāng)村的老太太,她再也不像我的奶奶了。我的奶奶不會這樣的。娟子雖然是個解放軍,但她還是一個女人啊,不,甚至只是一個姑娘。我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上去柔和一些,問她:“你多大了?”
她的手還在神經(jīng)質(zhì)地抖動著,聲音里仍然充滿顫抖:“22歲。”
我扭過頭去,院里那棵槐樹的影子在殘陽下拖得很長,大地呈現(xiàn)出一片腐爛的鐵銹味。我突然感到一陣惡心,有種想要嘔吐的感覺。她只有22歲,一個月的時間,已經(jīng)被摧殘得像個三四十歲的婦女了。她要經(jīng)歷多少噩夢才會變成這樣?我突然想起我的妹妹,如果她現(xiàn)在還活著,也是22歲了。她真像我的妹妹。士兵們正在院子里忙忙碌碌地準備著過夜的稻草,我忙定了定神,對自己說,周法五,你是個男人,是個國軍的中尉連長,千萬不能流淚。我其實多么想安慰安慰她,告訴她,你別害怕,我雖然是個國軍,我們在戰(zhàn)場上也許是敵人,但現(xiàn)在不是的,你只是我的妹妹,一個被傷害和侮辱的姑娘。我甚至還想讓她趴在我的肩上好好地哭一場。
那天傍晚,我把她帶到了村口。一切都很順利,那個老太太瞠目結(jié)舌地看著我們走出她家的院子,一句話都不敢說。別說是她,就是他那個當大隊長的兒子來了,對國軍同樣不敢有半點不恭。我看著她,她臉上有了些紅暈,眼睛像受傷的蝴蝶,有種掙扎著要向天空中飛去的小小喜悅。她甚至還有點害羞,低著頭喃喃地說:“謝謝你,可如果你的長官知道了……你怎么給他們交代?”
我苦澀地笑了一下,搖了搖頭,說:“我們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樣壞,我們其實都一樣……你一直向東走,也許會遇到你們零星的游擊隊。”
她的淚水在眼里打著轉(zhuǎn)兒,像夢一樣的目光飄過我的頭頂,看著不遠處的山頭,喃喃地說:“我們是敵人,可你、可你為什么要救我?”
我再也忍不住了,淚水終于洶涌而出,我把臉扭向一邊,喃喃地說:“我妹妹也是解放軍……”
3
我沒騙她,我妹妹的確是名解放軍。
我知道妹妹當了解放軍那段時間里,總是做夢,常常哭泣著從夢中醒來。那都是一些奇怪的夢。我經(jīng)常夢到自己變成一只鳥,從我家的窗戶里飛出去,飛到外面的樹上唱歌,好像唱的是《義勇軍進行曲》。那是和日本鬼子打仗時,一個叫田漢的詞作家寫的歌,不管是八路軍,還是國軍,都喜歡這支砍向日本鬼子頭上的歌。那時我們都是一家人。后來把日本鬼子打跑了,就開始打仗了。他們還把我父親也槍斃了,說他是地主惡霸。我想不明白,他們殺了父親,妹妹為什么還要當解放軍呢?說到底,她從來沒拿我們一家當自己的親人啊。我感到很委屈,向老天爺發(fā)誓,我從來都是把她當做親妹妹的。
妹妹是父親撿來的。她剛出生就被扔在一條山溝里。那是我出生后的第二天。父親那天正好從鎮(zhèn)上回來,他把妹妹從蒼蠅和螞蟻那里奪了回來,塞進衣服里抱回了家。父親給她起了個名字叫麥子。
每次回憶往事,我總是禁不住流淚。父親是個好人。他雖然早就死了,但我還是很懷念他,在共產(chǎn)黨沒有來到黃地以前,他整天臉上都洋溢著天高氣爽的笑容。共產(chǎn)黨來了,他就成為惡霸地主被槍斃了。后來,我遇到黃地的一個鄉(xiāng)親,他給我說過父親被槍斃時的情景,他跪在村子西邊許河的沙灘上,很不爭氣地尿了一褲子。我沒有覺得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只是一個農(nóng)民,一個有很多地的農(nóng)民,一個天天起得很早挎著筐子撿糞的農(nóng)民。我們當兵的都怕挨槍子,何況他呢?
在父親死掉之前,我就有很多年沒有見過他了。準確地說,有7年了。我是15歲那年離家的。那年,我和妹妹都在縣城上完了中學,父親說,到省城上大學吧。我們就去了,我上的是軍校,妹妹上的是女子師范學院,她沒上完,就參加了共產(chǎn)黨,然后就跑出去當了解放軍。我以后就只能在夢里見到她了。我很想她。我小時候根本不可能知道,這個躺在我身邊,經(jīng)常和我一起爭奪我媽乳房的小家伙并不是我的親生妹妹。那時我不但不喜歡她,相反還恨她,她總是讓我吃不飽,我嗷嗷地叫著,把母親的乳頭咬得很疼,有時母親嘴里喊著“小祖宗”,但手卻毫不客氣地在我的小屁股上來上一巴掌。我長大以后讀了很多書,按照書上的說法,我在潛意識里應該恨我妹妹,把她從小恨到大,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我相反愛上了我妹妹。父親一直對我的婚事放心不下,曾經(jīng)托了很多人給我說媒,他們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喜歡的是妹妹。如果我能找到她,我寧愿不當這個軍官了,帶著她遠走高飛,遠離戰(zhàn)爭,和她安靜地過完這一生。
那天,我把那個叫娟子的解放軍女兵送走了,我告訴她,我妹妹叫周法玲,如果你見到她,請告訴她,他的哥哥一直在找她。我甚至冒著泄密的危險,把我們部隊番號也告訴她了。后來我就再也沒做過自己變成一只鳥的夢了,總是夢到長大以后的妹妹。她站在我面前,笑嘻嘻地淘氣地看著我,陽光在她黑油油的頭發(fā)上跳躍,她穿著英姿颯爽的軍裝,像一棵美麗的樹。
惟一讓我遺憾的是,我總是看不清她穿的是解放軍軍裝,還是我們國軍的。
4
過了幾天,解放軍的又一波進攻像漲潮的海水一樣漫延到了整座大牛山。
我們無法扼殺解放軍的凌厲攻勢,越來越多的國軍士兵崩潰了,像一只只受驚的兔子一樣扔掉步槍,抱著腦袋四處奔逃。那些解放軍士兵狂吼著,吶喊著,憤怒地朝遠處的敵人射擊著,朝近處的敵人掄起槍托,在空中劃了一個圓圈,狠狠地砸下來。那些國軍士兵來不及哼叫半聲,腦袋就被砸碎了,腦漿迸濺出來。解放軍士兵臉上充滿堅毅的殺氣,他們向一切阻擋他們前進的敵人掃射、砍殺,他們自己生產(chǎn)的那種一炸就成兩瓣的手榴彈再次發(fā)揮了威力,一排排手榴彈蓋天鋪地飛過來,像蝗災時期的飛蝗一樣,幾乎要把陽光遮住了。到處是紛飛的碎肉和鮮血,他們跳過壕溝,踩著鮮血和地上的斷胳膊斷腿,沖進人群,只要是活的,他們就要把他消滅掉,讓他成為一具冰冷的尸體。殘余的國軍只能邊打邊撤往山頂上的第二道防線。解放軍尾隨而來,他們從硝煙里沖出來,端著寒光閃閃的步槍,吶喊著沖上陣地。
父親的亡靈在天上看著我,我只能把他們殺死,或者讓他們把我殺死。從我聽說父親被他們槍斃的那一天起,這就是我注定的命運。如果遇到妹妹,我最想問她的是,她如何能做到?jīng)]有仇恨的,如何去愛他們的。她如果能愛他們,為什么不能愛我們的父親?她的愛是怎么回事?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恨我的妹妹,還是愛她。愛與恨折磨得我快要發(fā)瘋了。我多么想見見她啊!她是什么模樣?容顏是蒼老的,還是年輕的?是茁壯成長的樹,還是含苞欲放的花朵?是我的敵人,還是我的親人?是一個陌生人,還是我的愛人?
在血肉橫飛的殺戮中,我揮舞著上了刺刀的步槍,感覺殺死了很多人,有時是把刺刀捅到他們的脖子上,有時是捅到肚子上,拔出刺刀時,他們的鮮血噴出來,我的軍裝上都是血,我的臉上也是血,分不清是我的,還是他們的。它們甚至從額頭上流到了下巴,滴滴答答地往下掉著。
我甚至都不知道捅死的是解放軍還是國軍,只要眼前有活動的影子,我都會撲上去。所有會呼吸的人都是可怕的,同樣的面孔,同樣的表情,我無法分辨,也無需分辨,我們都一樣是群瘋子。
一個鐵疙瘩滾到我的腳下,很奇怪地冒著一股濃煙。我吸了一下鼻子,聞到了硫磺的味道。我瞪大眼睛,那是顆手榴彈!我的腦袋嗡嗡地叫了起來,就像被手榴彈砸了一下,眼前發(fā)黑,鼻涕、眼淚都流出來了。我不想死,我現(xiàn)在不想死啊,可我就要死了,妹妹……
有個黑影突然躥過來,使勁地把我撞到一邊,猛地撲上去壓在那顆冒煙的手榴彈上。我重重地摔在地上,當我抬起頭來,一聲悶響,泥土和血肉碎片朝我飛過來。它們雖然都很柔軟,但打在臉上,還是有點疼,臉上像是爬滿螞蟻,癢癢的。我抹了一下臉,把那些泥巴和碎肉末子甩掉,把那個人的身子翻開。他的胸口被炸了一個洞,醬紫色的腸子掛在身上,就像纏著一條條可笑的繩子。他的眼睛雖然緊緊地閉著,臉也被火藥熏黑了,但我還是看出來了,他是我的勤務兵小黑子。他是我當了軍官后,他父親把他送到我身邊的,說是想跟著我出息出息。我感到很難過,胸口像被人狠狠地擂了一拳。我如果再回黃地了,他父親如果要問我,我怎么說呢?他跟著我不但沒有出息,反而死了。我怎么給他說呢?
我抬起頭來,突然又看到了那個解放軍女兵。她咬著吃驚的嘴唇,愣愣地站在那里。她的手里端著支步槍,槍刺上還滴著鮮血。她把刺刀指向我,但她既沒有刺向我,也沒有開槍射擊,就那么呆呆地看著我,整個身子僵硬在那里,就像用泥巴捏出的塑像一樣。我眼睛被血和汗水遮住。我用袖子擦了擦臉,再睜開眼時,她已經(jīng)到了我跟前,那支步槍扔在腳下,刺刀溫柔得像只貓。她低下頭,從挎著的背包里抽出一條繃帶,把我的胳膊抬起來,上面有條刺刀劃過的長長的傷口。她大口大口地喘著氣,少女的清香穿過刺鼻的硝煙彌漫過來。她的影子在我面前亂晃。我想用手撥開她長長的秀發(fā),看看她是誰。但我的淚水又不爭氣地流了出來,模糊了雙眼。她仰著臉看著我,我卻看不清她。她也許是我妹妹,也許是娟子,也許是我前幾天遇到的那個女兵,也許都不是……
一顆炮彈呼嘯著飛過來,像個迷人的少女,遠遠地拋著媚眼。我張開雙臂,緊緊地抱住她,想再次把她壓在身下,讓她躲開那些像蝴蝶一樣的彈片。但她還是把我重重地推開了,我看到她向天空伸著手跳動起來,舞姿優(yōu)美,像盛開的花朵。接著,我就看到我的腿和胳膊飛起來,在半空中翻著跟頭,呯地砸在地上黏稠的鮮血上。我重重地仰面倒下,鮮血四濺,就像躺在一朵花里。
我站了起來。小黑子也站了起來。他垂著頭,傷心地看著被炸開的胸膛,慌慌地把腸子往肚子里塞著。那個解放軍女兵也站了起來,她的身體上布滿彈孔,陽光穿過彈孔射過來,晃得我眼睛總想流淚。她看著我,笑了一下。我忙也笑了一下。后來,我們就坐在陽光下,周圍的槍聲與吶喊聲砸在地上,大地仍在顫動,但這已經(jīng)和我們沒有關系了。我們坐的那塊地上,非常干凈,沒有鮮血和破碎的肢體,綠草夾雜著無名的野花,蝴蝶翩翩起舞。她躺在我懷里,我撥開她的頭發(fā),用袖子擦去她臉上的鮮血和泥巴。她睜開明亮的眼睛,眼睛里盛開著紅色的玫瑰花。我的淚水像家鄉(xiāng)黃地的蝴蝶,落了一臉。陽光穿過厚厚的硝煙,她用手擦著我的淚水,微笑地看著我,喃喃地說:“哥哥,哥哥,我愛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