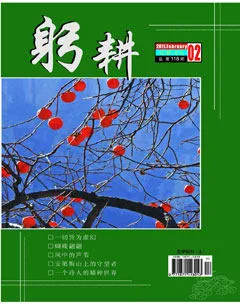詩意寒冷
冬日賞讀宋代文彥博的題畫詩:“梁園深雪里,更看范寬山……云愁萬木老,漁罷一蓑還。此景堪延客,擁爐傾小蠻。”古人親歷而又描摹下來的詩情畫意,啟發筆者聯想到,歷代那些“詩”諸造化的篇章,就像書寫在大自然這幅畫面上的題畫詩,將遙遠年代的寒冬詩意彰顯天地間。
《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四序更迭,暑往寒來,“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較之陶潛這一觀察角度有變的秦觀,卻于山山寒色中細膩地觀察到“草上霜花勻似剪”的美象。楊萬里的目光則投向了人:“輕寒正是可人天”。詩眼之“可”,是天地人的和諧。
苦寒之時,詩人又于看上去很無詩意的景象中吟出了極具詩味的文字。精采之作有魏武帝北上太行山的《苦寒行》:“艱哉何巍巍……悠悠使我哀”,有孟郊“凍吟成此章”的《苦寒吟》:“天寒色青蒼,北風叫枯桑。厚冰無裂文,短日有冷光。”若細細檢索,詩人筆下雖然呈現著周天寒徹的冷峭之色,但也不乏宋詩描述的“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之暖人景象。
迨至三陽開泰,“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兩岸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杯。”轉眼之間,便是七九河凍開,八九燕子來,九盡楊花滿路飛……的一幅幅欣欣向榮圖了。這些與時俱進的詩篇,歷經歲月磨洗,愈見光彩熠熠,獨樹一幟的唐代邊塞詩,是矚目的亮點。
很具代表性的岑參于輪臺送往詩中描繪了“瀚海闌干百丈冰,愁云慘淡萬里凝”的大景觀,并于時空大視角中捕捉到“劍河風急雪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的特寫鏡頭。活躍于大歷間的才子盧綸,那首雄壯豪放的《塞下曲》:“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歷代相傳,極負盛名。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卻提出了“北方大雪時,群雁早南歸。月黑天高處,怎得見雁飛”的質疑。值此開發大西北之時,旅人走邊入塞,不妨親臨體驗,或許能解華老之疑。
細品如此多彩的寒冬詩意,無不掩映著詩人那分濃濃的感情色彩。有例可證。賈島倚杖晚望雪晴后,“溪云幾萬重”,“寒日下危峰”,“卻回山寺路,聞打暮天鐘”。讓后人“wf0RVDzdQ7uA1klWjy8dgQ==推敲”出來的是少年為僧、后又還俗、屢試不第、仕途偃蹇而頓萌的詩人歸念之情。白居易的“夜深知雪重,時間折竹聲”,看似隨手拈來的大雪冬夜之靜寂,實在著意地透露出謫居江州的孤寂心情。戰亂中回居長安的杜甫,在“亂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風”中,《對雪》愁坐愁吟愁書空,則隱現著詩人的憂國憂民之情。
若置換以“氣之動物,物之感人《詩品》的角度,解讀寒冬詩意,又可發現嚴寒中特有的萬“物”,就像對于人類有著特殊效應的“激素”,激活了詩人的激情,也激化出有別于春花秋月的寒冬特殊美。
典型的是與松、竹并稱“歲寒三友”的梅。百花凋謝的隆冬季節,“萬花敢向雪中開”,鐵干虬枝,傲然挺立,枝頭怒放,燦爛芬芳,“個個團冰雪”的“花魁”,“冰枝不怕雪霜侵”、“凌厲冰霜節愈堅”,“雪虐風饕愈凜然”。明麗的詩情畫意,暗喻也贊譽著“不要人夸好顏色,只流清氣滿乾坤”的“高標逸韻君知否”?
走筆至此,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天寒地凍中,歡喜漫天大雪的梅花似乎與雪結下了奇緣:或雪中競開,或雪后綻放,或雪海一片,“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和不似都奇絕。”雖然,“梅湏遜雪三分白,雪卻輸梅一段香”。但對于“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的雪,詩人卻另有一番情愛。
愛其潔,愛其白,愛其瑞兆豐年,愛其“天地無私玉萬家”。生花妙筆下也就描出了“六出飛花入戶時,坐看青竹變瓊枝”、“最愛東山晴后雪,軟紅光里涌銀山”的觀雪圖。而陳羽的那首“紅旗直上天山雪”,儼然一幅壯美的風雪行軍圖,讓人不由不想起革命戰爭年代中,“紅旗漫卷西風”的六盤高峰和“更喜岷山千里雪”的偉人詠雪詩。
毛澤東愛雪,一生中的七十來首詩詞,就有六首寫到了雪。而寫于一九三六年,經傳抄后,發表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重慶《新民報晚刊》的《沁園春》──上片寫景,下片抒情,情景交融,氣韻兼備,氣象雄渾,大氣磅礴的壯麗畫卷,將“紅妝素裹,分外妖嬈”、“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雪”,推向了至高境界──“江山如此多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