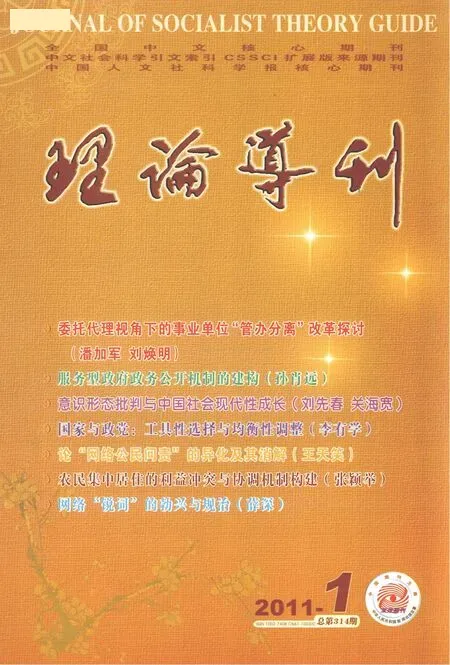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研究
姜濤
(江蘇大學法學院,江蘇鎮江212013)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研究
姜濤
(江蘇大學法學院,江蘇鎮江212013)
司法化既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實施中的重要一極,又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貫徹落實的必要路徑。對此路徑的認識缺乏以及規劃錯位,必然會影響到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之制度績效的發揮,進而直接影響到國家犯罪控制的效果與人權保障的程度,因此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就必須科學規劃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的道路。就其未來實現而言,應該讓最高司法機關承擔刑事政策解釋之重任,并把刑事政策解釋作為各級司法機關的行動指南,違者必究。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政策解釋;能動司法;司法化;立法化
刑事政策不僅是刑法立法發展的助推器,而且是刑事司法運行的矯正器。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制定之后,如何科學地、有效地實施這一基本刑事政策,就成為當下各級司法機關必須慎重思考的重大問題,因為它關系著刑事立法的發展與刑事司法的成敗。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作為黨和國家控制犯罪的策略有其自身的實施機制,如果不靠這種機制發揮作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照樣會成為一紙具文,徒有口號意義。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解釋的研究比較發達,至于這一基本刑事政策如何有效地作用于刑事立法與刑事司法,則鮮有研究。這就不能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貫徹落實開辟理論通道,以至于出現了刑事立法與刑事司法違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之亂象,并最終影響到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之制度績效的發揮。本文以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為主線展開理論闡釋,旨在力促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科學、有效地實施。
一、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的認知
刑事政策的屬性決定我們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走立法化與司法化之路,這是一種必然選擇。通過刑事政策立法化和司法化開辟寬嚴相濟刑事的實施途徑,把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適用起來,把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作用發揮起來,把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權的價值體現出來,把人們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只是犯罪控制策略而不是控制規則的認識和觀念轉變過來,[1]對于正確處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之間的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立法化與司法化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實施中的兩極,其猶如車之雙輪、鳥之雙翼,兩者皆不可偏廢。其中,立法化是將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理念與內容,以政策法律化的方式,變成刑事立法,在社會生活中強制實施。有了立法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實施就不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但是,實現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立法化后,只能算是完成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實施“作業”的一半。之后,在司法實踐中如何以抽象的刑事立法合理應對具體生動的刑事案件,仍是一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實施問題,因為當立法的抽象性遭遇案件的鮮活性之時,能實現“無縫對接”的畢竟數量有限,不少案件需要借助法官自由裁量權來決定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既是定罪政策,又是量刑政策,而后者顯然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核心。因此司法實踐中,在刑法規定的法定刑幅度內,如何對被告人量刑——重或輕,則須以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理念和內容為基準做出。這都使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成為一個繞不過去的主題,有給予特別研究的必要。那么,什么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呢?
很顯然,這是一個全新提問,學術界尚無人論及。筆者認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是最高司法機關以刑事政策解釋(以下簡稱政策解釋)的方式,明確什么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以及實施該刑事政策的要求,從而把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實施變為具體的實施細則,以此作為各級司法機關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之行動指南的司法活動。認知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應注意以下兩個方面:(1)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是最高司法機關強化政策解釋的產物。如同寬大與懲辦相結合、嚴打等刑事政策一樣,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不僅蘊含著公平正義等理念,而且蘊含著定罪與量刑的規則,對刑事司法具有直接制約作用。[2]因此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實施中,需要以政策解釋的方式將其細化為具體的定罪與量刑規則,使其成為各級司法機關的行動指南。(2)各級司法機關以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為指導而開展的刑事司法活動并不屬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的內容。這是從刑法教義學上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進行的限定。我們固然可以把一切刑事司法都作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的內容,但這種研究過于寬泛,且沒有理論與實踐意義。事實上,當我們對政策解釋問題做出定位之后,刑事司法只須依據其行事即可,至于刑事司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完全可以從刑事司法角度闡釋,沒有必要畫蛇添足,再將其歸位到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之列。
不難看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實施由理性王國降落在現實大地的正確選擇,它包括了政策司法化與司法政策化兩個基本維度,并以政策解釋把以上維度統一起來。第一,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是一個政策司法化的過程。政策司法化表明的是,我們需要從具體且正確實施的角度,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從司法上進行再界定,即把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理念提煉出來,把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內容細則化,從而使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能夠具體化地、實踐性地成為刑事司法實踐的行動指南。只有這樣,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刑事司法的指導和制約作用才能落實到具體行動中,而不是停留在口號上。同時,如果我們對政策司法化問題缺乏正確認識和合理界定,那么司法機關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就會出現諸多亂象。因此,政策司法化是我們在刑事司法實踐中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前提條件。第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是一個司法政策化的過程。司法政策化意味著,一國的刑事司法必須以當下基本的刑事政策為指導,不得違背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更不能背離當下基本刑事政策的內容而孤軍奮戰。這是刑事政策與刑事司法的關系使然。同時,雖然刑事司法承擔著具體的犯罪控制與人權保障重任,但這種活動不僅在實施中難免具有盲目性——背離當下犯罪發展情勢,而且還會偏離刑事法治設定的犯罪控制目標——違背刑罰目的之實現規律。此時,解決刑事司法的盲目性與失偏性之重任就落在了一國基本的刑事政策上。而實現刑事政策與刑事司法之間的良性互動,又要求從經驗層面確立刑事司法應受刑事政策指導的原則,即刑事司法應在當下基本刑事政策之精神與內容的軌道上運行,背離刑事政策的司法應被糾正。第三,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最終是一種政策解釋活動。政策解釋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的外在形式。從概念上分析,政策解釋是最高司法機關對如何在刑事司法中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進行的闡釋與說明,它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規范性文件。有了政策解釋后,政策司法化與司法政策化也就找到了結合在一起的中介。不僅如此,政策解釋還使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實施具有了行動指南。這是因為:雖然政策司法化與司法政策化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中的內容維度,兩者構成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的完整內涵,但其內容的存在必須借助于一定的形式——政策解釋。政策解釋在體現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之內容的同時,也使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具有了規范支撐,不可替代。
綜上可見,政策司法化與司法政策化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中的一體兩面,無法截然分開,而且它們之間的關聯以政策解釋為中介建立起來。在這里,政策司法化與司法政策化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的內容,而政策解釋則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的形式,形式體現了內容,并使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成為了規范存在。因此,我們以政策解釋為中心,既可把握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實施中的規范依據。又把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之意義維度凸顯出來。
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的實踐
如何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不僅是立法之事,更是司法之事。而司法機關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實施,又集中以最高司法機關頒布的政策解釋體現出來。這其實是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再界定,即以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理念為制約,內容為基準,對司法機關如何依據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權進行的闡釋與說明,它大致包括了定罪與量刑、起訴與不起訴、證據標準與訴訟程序等內容。這不僅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的最主要實踐模式,而且是一種影響最廣泛、具有強制拘束力的實踐模式。那么,我國是如何開展這種政策解釋的呢?
自2005年國家提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始,“兩高”即頒布了一些政策解釋性的規范性文件。比如,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通過的《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和20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無疑,通過這些政策解釋,不僅體現了司法機關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貫徹落實的重視,而且還以其相對規范性為刑事司法提供了行動指南。正是這類投石探路、聚沙成塔的努力,使中國在強化政策解釋方面的主要條件逐步趨向成熟,并為今后可能出現更多的政策解釋鋪路奠基。
歸納起來,“兩高”的政策解釋具有如下突出特點:一是全面性。就政策解釋涵蓋的內容來看,兩高的政策解釋不僅包括從思想認識上正確理解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而且還包括如何在刑事司法中將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落到實處,同時還對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工作機制做出了規劃。因此是一個從理念到規則、從實踐到制度的全面解釋。二是混合性。不難看出,兩高的政策解釋兼具會議紀要與司法解釋雙重屬性,這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它不僅要求各級司法機關正確認識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內容與意義,而且對哪些犯罪應該“從寬”,哪些犯罪應該“從嚴”,如何“寬嚴相濟”等都做出了界定。三是矛盾性。即兩高都制定了政策解釋,但是在解釋的內容上存在差異,而且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理解與適用上也存在分歧。其中,爭議的焦點在于:兩高出臺的解釋到底是一種什么性質的規范性文件,其正當性依據是什么?這都需要我們從學理上給予合理闡釋。
首先來分析第一個問題。從建國以來,最高司法機關頒布的關于貫徹落實刑事政策實施的規范性文件并不鮮見。比如,1987年頒布的《關于依法嚴懲非法出版犯罪活動的通知》,2004年頒布的《關于依法嚴厲打擊集資詐騙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活動》等等,這些規范性文件的頒布,都是在嚴打刑事政策之下,結合著當時社會某種或某類犯罪案發的時態,而給出的政策性指導意見,它仍然是對刑法適用中的具體問題進行的闡釋性說明,因而屬于司法解釋的范疇。與上述規范性文件不同的是,《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和《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是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如何在刑事司法中運用進行的解釋,與一般意義的司法解釋不可同日而語。筆者認為,它已經超出了司法解釋的范疇,屬于典型的政策解釋,即最高司法機關對如何在刑事司法中具體地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進行闡釋與說明。雖然在這種解釋中,不僅有定罪與量刑上的闡釋,而且還涉及對證據標準和追訴程序的要求,但是這種闡釋是依附于政策闡釋本身的,它們并不是解釋的重心。其解釋的是如何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這種解釋不能再被稱之為司法解釋,而是典型的刑事政策解釋。當然,走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之路,需要先解決刑事政策解釋的一些理論問題。最大的理論問題是:兩高有權進行政策解釋嗎?這就涉及到了政策解釋的正當性基礎問題。
如果我們把刑事政策定位為黨的刑事政策,同時又容許司法機關對刑事政策進行解釋,就意味著司法權也可以進行政治目的性判斷,黨的領導和國家的司法權之間的界限豈不就變得模糊不清了?[3]可見,如要正確定位政策解釋之正當性,我們尚需回答“什么是刑事政策”。這是一個歧義紛爭,但又必須給予界定的問題。現在被我們接受并廣泛運用的“刑事政策”是一種國家控制犯罪的策略,正如馬克昌教授所指出,“基本刑事政策,是指黨和國家制定的,對一切犯罪及其他有關危害行為作斗爭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方針和策略……具體的刑事政策,是指黨和國家制定的,對特定的犯罪及其他有關危害行為作斗爭具有指導意義的方針和策略。”[4]到如今,國內學家有關刑事政策的定義基本上沒有超出這一界定。既然是一種控制犯罪的策略,必然會影響到刑事立法、刑事司法與刑罰執行等環節。在現代刑事法治之下,這就需要由具體實施犯罪控制活動的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和刑罰執行機關來完成。可是,一方面,國家定制的基本刑事政策具有高度抽象性,即只強調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另一方面,刑事政策要想成為刑事立法與刑事司法的行動指南,就必須具備可操作性,要體現為一定的規則,這就蘊含著政策解釋的必要性,即需要我們以政策解釋方式把刑事政策的內容展現出來。現在的問題是,政策解釋應該由誰來解釋呢?欲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尚需明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如何提出的。“寬嚴相濟”作為刑事政策是黨中央政治局原常委羅干同志在2005年12月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提出來的。之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不僅出現在2006年《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而且還出現在2006年兩高的工作報告,以及《刑法修正案》(六)、(七)的制定中。可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首先是作為黨的犯罪控制策略,之后分別在立法機關中發揮著刑事立法政策,在司法機關中充當著刑事司法政策和在刑罰執行機關中擔當著刑罰執行政策等角色。這是刑事政策運行的基本路徑,即黨首先提出某項刑事政策,然后以一定的方式將其上升為國家基本刑事政策。
鑒于立法、司法和刑罰執行是體現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三個維度,因此國家的刑事政策又會以一定方式分化為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罰執行政策。即刑事政策的內涵保持不變,但在傳導和適用的過程中,會發生名稱上的變化,即出現黨的刑事政策→國家刑事政策→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罰執行政策。其中,黨和國家的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而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罰執行政策則是具體刑事政策,具體刑事政策不應該抵觸基本刑事政策。既然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一項刑事司法政策,那么最高司法機關在貫徹落實該政策過程中,對其實施問題做出更詳盡解釋,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只不過在兩高的職權中,除了司法解釋之外,又多了一項政策解釋權限而已。當然,這種解釋相比較于司法解釋來說,更加具有彈性:一方面,最高司法機關在再界定(解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之時,必須堅持不抵觸原則,即不得違背國家基本刑事政策的精神與理念;另一方面,政策解釋會隨著犯罪結構的變化而變化,即當社會治安形勢發生變化之后,刑事政策解釋也應及時進行調整,把刑事政策之靈活性充分體現出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以刑事政策之優長彌補刑事法律之不足,發揮刑事政策與刑事法律之間互動的合力,增強刑事司法的能動性,以合理組織對犯罪的反應。
當然,就政策解釋來說,應該明確以下幾個重要方面:(1)政策解釋的主體只能是最高司法機關,即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其他的司法機關都無權也不應該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司法實踐中的貫徹落實做出解釋。(2)政策解釋的內容應包括如何認識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和如何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兩個基本維度,前者是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內容與意義的闡釋,后者則是對如何以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為指導進行定罪與量刑活動的詳細闡釋,它不僅包括從嚴、從寬處罰犯罪之范圍,從嚴、從寬處罰之幅度,而且也包括以什么程序、什么證據規則等來保障從嚴、從寬和寬嚴相濟的實現。這是政策解釋的重心所在。(3)政策解釋的程序可以參照司法解釋的程序進行,即參照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制定的《關于司法解釋工作的規定》之規定,遵循立項、起草與報送、討論、發布、施行與備案等程序進行,必要時還應進行政策聽證。(4)從政策解釋的制度績效出發,政策解釋應保持一致性。在政策解釋上,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都可能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貫徹落實做出解釋,雖然這些解釋分別針對刑事偵查、檢察工作和審判業務做出,但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理解應保持完全一致。(5)政策解釋是一種有權解釋,具有強制適用的效力,因此在政策解釋中,需要明確不抵觸原則在司法機關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的規則價值。
政策解釋在使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具有內容之時,也提升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貫徹落實的品質,因此,如何在刑事司法中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首先是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進行再界定的問題。所以,如何提高自身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認識并做出相應解釋,就成為當下最高司法機關所要面臨的新挑戰。由此決定,政策解釋應成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實施的重點。
三、結論:政策的在場與司法的立場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研究表明的是政策之在場與司法之立場的學術活動,與之對應,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則是一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作用于刑事司法,并與刑事司法之間形成互動的過程。顯然,強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刑事司法之間的這種互動,對于犯罪控制與人權保障目標之實現,對于正確適用刑法與開展能動司法具有積極意義。當然,這種互動不是一種空泛的學術闡釋,它需要借助一個中介轉化為具體行動。無疑,作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之外在形式的政策解釋,就充當了這一中介,而且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中介。有此,我們就在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之實施開辟制度通道的同時,又充分地發揮了其貫徹落實的制度績效。可以預見,有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的在場,刑事司法的有效開展也就有了基本的立場。這在著力倡揚能動司法、高效司法和公正司法的當下,意義十分重大,所以我們應重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的指導作用,確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的基本向度,并借助政策解釋這一工具,使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能夠切實地成為司法機關的行動指南。
[1]蔡定劍.中國憲法實施的私法化之路[J].中國社會科學,2004,(2).
[2]姜濤.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制度基礎與價值邊界[J].法商研究,2007,(1).
[3]季衛東.合憲性審查與司法權的強化[J].中國社會科學,2002,(2).
[4]馬克昌.中國刑事政策學[M].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77-78.
D 926.04
A
02-7408(2011)-0078-02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實施機制研究”(09CFX057)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姜濤(1976-),男,河南南陽人,江蘇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江蘇大學刑事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從事刑法學與法理學研究。
[責任編輯:張亞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