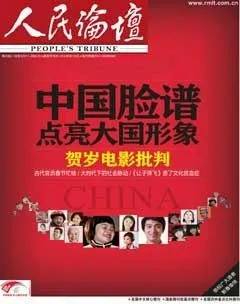價值判斷差異與意識形態塑造
近些年,在與學界朋友討論政治經濟問題時,常常涉及到意識形態,有時爭得面紅耳赤。爭論到一定層次,論者相互之間要說服彼此,殊為艱難。
大略來說,意識形態是一定規模的社會集團所持有的系統性的價值判斷。通常,一個社會因集團分化和歷史文化因素的影響,不會有完全統一的意識形態。官方政治精英所持有的意識形態會借助政府資源在社會上發生廣泛影響,但要完全替代其他類型的意識形態很不容易。為此,不同意識形態之間可以有批評,那么,批評的方式是什么?如何摒棄不同意識形態之間黨同伐異、好勇斗狠那一套?筆者以為這些問題值得探究。
舉例來說,關于民主政治及其延伸問題的爭論,就因為價值判斷的差異,到一定層次就難以爭論下去了。
甲說:大國推行民主政治的條件之一是語言及文化的基本統一,建立這種統一的基礎是經濟的高度一體化。如果沒有這種統一性和一體化,民主政治的后果可能是國家分裂。
乙回應:這個說法不對!人權高于主權,只要通過民主政治保障了人權,放棄其他次一級權利又算什么?
甲又說:你可以對權利做這樣的排序,但在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民族文化的差異性很容易被政治家利用來做政治動員的資源,引起文化背景不同的民眾之間的沖突,甚至引發戰爭。戰爭受害者最終是民眾,而很少是政治家。戰爭還會延后經濟發展。
乙回應:一切社會行動都會有犧牲,為了人權這個至高無上的目標,即使有戰爭,并產生犧牲,也應在所不惜!
上面假設的對話是筆者虛擬的,但類似的對話并不少見。由對話看出,甲乙雙方首先有價值觀的差異。最明顯的是,論者甲和論者乙在主權和人權的排序上不同,就是說,他們權衡此二者的價值有差異。實話說,要消除這種差異很難。通常,人們的爭論也就停在這一步。一個寬容的社會,也不必硬要誰閉嘴。
但是,就理性要求來說,進一步深究的空間還是存在的。人權固然有至高無上的價值,但如果沒有一定的條件,人權就是水中月、鏡中花。人們常常看起來在追求人權,但因為其他社會條件不具備,得到的還是對人權的踐踏。所謂“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一個有希望的社會,其政治精英對這個歷史邏輯會有深刻理解,并為創造這種條件去努力。
寫到這里,我愿意簡略談談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觀點。人們通常注意到羅爾斯對公平正義價值的肯定,其實,他還十分強調秩序和穩定的價值。離開歷史的邏輯,實際上很難對人類的一些基本價值給出一個排序。邏輯永恒,而價值排序卻可能遠離理性。
在眼下中國的一些講壇上,常常多有各種虛虛實實的價值判斷的宣泄,而像羅爾斯那樣的理性思考卻少之又少。也許怪不得中國人的智慧,只能怪某種過于急功近利的宣泄式的價值觀推廣。這種氛圍之下,無包容可言,理性思考總顯得不合時宜。在意識形態的塑造問題上,首先要講包容,誰也不必急于壓服誰;其次要講理性,否則包容就變成了死水一潭的折中主義,最終還要喪失包容。
在當下中國,學術界的朋友們喜歡講某左某右之類的話,近期似乎還把這種劃分推廣到了一些地方官員身上。例如,有朋友對重慶的“唱紅”就提到了左右評判的層次上。有時候,這樣講話有簡便的好處,但壞處容易失去包容性。依筆者看,一個社會,左和右也可以包容。
若把強調效率忽視平等看做“右”,把強調均等而忽視效率看做“左”,那么,這種對壘即使在高度市場化的發達國家也存在。至于西方社會,我們甚至可以把耶穌看做“左派”的領袖,把教會看做左的意識形態的倡導機構,若承認這個說法,就可見西方世界左的意識形態其實有普遍的影響。再深究一點,西方的宗教曾長期是“社會不穩定”因素;在有的歷史時期,它也罪惡累累。但到如今,西方的宗教也被“和諧”了,現在還有多少自詡為思想家的人有很大的興趣去批判它呢?也許羅素是批評宗教的最后一位思想家。這不是因為西方宗教經脫胎換骨后消失了,而是它退回到了一個合適邊界里面;它不再強加于人。
從西方宗教的歷史給我們一個啟示,問題不在于要不要左的意識形態,而在于這種意識形態存在的方式。我看左的意識形態是客觀存在,只是應讓其有適當的形式和適當的作用范圍。重慶的“唱紅”本身是強調奉獻,強調平等,似乎有些左,但不要忘記,重慶的政治家們還在不遺余力地抓經濟效率,絕非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只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重慶近日甚至用基尼系數來考核下級政府官員,可見,他們不是僅僅把平等當做歌謠來唱的。只要重慶和成都在經濟活動領域積極推進市場化改革,積極打破各種壟斷,對內開放與對外開放并舉,用“唱紅”的辦法來約束公務人員也是一種嘗試。“唱紅”范圍擴大既不必要,也可能有負面影響;學者們之所以擔心,是出于對“昨天”歷史的余悸,應該可以理解。但以我拙見,過去那種登峰造極的專權恐怖,其實已經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了,根本沒有了馬克思主義的一點影子。以我善意的觀察分析,對重慶、成都的改革,這個擔心似無必要。當然,從長遠看,“唱紅”是不是約束公務人員以求自律的最好形式,倒也不一定。未來也許中國需要不同意識形態在公共領域更大的分工,為此,杰出的政治家應有更大的探索。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