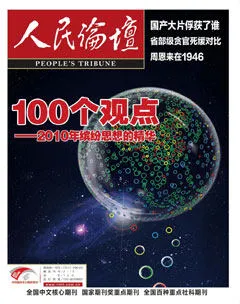方寸之間 乾坤無限
篆刻藝術,是中國藝術門類中的一個特殊門類,它與漢字、中國書法、中國畫等藝術門類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并在世界藝術百花園中獨放異彩。
我們知道,古代的實用印章藝術(古璽、秦漢印),其實是當時制印工匠們的工藝制作品。他們僅僅是依據當時的實用璽印制度生產出來的一些實用品而已,并不是我們現在所認為的藝術層面的那種藝術創作(篆刻)。他們中間大多數作者的作品也只是憑借一種制作經驗和制作技術之使然,并沒有追求藝術概念的因素在其中。后來,這種實用的形式,發展演變成為我們現在認可的篆刻藝術,也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孕育期,往往是數百年如一日,很難說它們在什么地方、什么時候是個分界。然而,當藝術從不自覺走向自覺的時候,尤其是其進一步完善成熟,并日漸過渡走向現代后,人們用藝術的眼光來重新審視它們的時候才發現,這些不經意的“實用品”,竟然是一些高不可攀的藝術杰作。這一情形的出現,令當時那些制印“工匠們”始料未及。也正因為如此,明清篆刻家對此曾一度不屑一顧,甚至深惡痛絕。不過,雖然明清篆刻家們的這種態度不無道理,但站在今天的角度,特別是站在純藝術的角度,我們覺得是一種淺見。中國藝術的幾個門類,之所以篆刻藝術的發展最大,從某種意義上反倒是得益于對明清這種片面觀點的反省,而回歸秦漢也意味著是一種進步。
馬士達先生正是當代篆刻藝術家這一主張的典型代表。他認為明清的東西,有時候過于文人化了些,甚至是過分地強調這一點。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值得商榷的。不僅如此,他們小看秦漢印是普通工匠,竭力主張“印從書出”,其實也是理解上的一種狹隘。秦漢印(古璽)自然、自由、純真、天趣,少有人為雕琢的東西,更沒有過于技巧化的成分,因此,有一種質樸、自然的美,是“源頭活水”,這恰恰就是明清印所不具備的。陳衡恪曾經告訴齊白石,不妨用漢磚的刀法來制印。后來他大刀闊斧,盡洗前人的追方逐圓,刻意求工,另辟蹊徑,別開生面。
其實,對于一個篆刻藝術的從事者來說,能否準確理解和把握其中真諦(中國藝術的精神)及其發展過程和規律是至關重要的,也是關鍵之所在。當然,具備一定的基礎技能,選擇一個合適的切入點,并進一步發揮個人的才情和修養,也是最終成就的一種保證。
馬士達先生的篆刻藝術是我所欣賞的,并勝過欣賞別的篆刻藝術家。他的作品有一種活的、有生命的“氣場”,同時也有千差萬別、變化無窮的形式。他能在不同的作品里有不同的意趣,并很少重復,更沒有刻意的雕琢。因此,看先生的作品,心動、回味無窮、美。
大多數人認為篆刻一定要學習篆書,馬先生則不然。他認為篆書與篆刻雖然有一定的關系,但沒有必然的聯系。所以,他不習篆書。在他看來,從篆書入手,路子窄,極易死板而缺乏生氣。他也不習草書,而是從行草或行書開路,因為草書的草法煩(蘇東坡也不寫草書,其實真正懂草書的人也不多),行、楷、隸倒是花了不少時間。隸書則是他的另一張牌,是既不同于別人,又完全是自己的風彩。他是以隸為本,楷、行為用,并幾乎是憑自己的理解。他的作品受古人的影響大,但又有所消化,并不是“邯鄲學步”與“東施效顰”。秦漢印章是本,明清的東西則是批判吸收,是唯我所用,又有不同。他一直堅信,藝術“自由則活,自然則古”。他的作品“無我為大,有本不窮”,寧愿讓一個內行稱道,也不愿讓一百個外行說好。
馬先生在篆刻藝術道理上的勝出,得益于兩位恩師:沙曼翁的正統和手上功夫及宋季丁的思路和靈性。同時,古璽、秦漢印、明清浙派、鄧派及近代吳昌碩、齊白石等大家的影響也是至關重要的。除此之外,他還將自己的精神境界和審美理想注入到創作中,以其特定的篆刻語言來塑造作品的“氣象”,豐富作品的精神意蘊。這樣一來,有效地增強了篆刻藝術的表現力。這是一種對象化了的人的本質能力,也是一種客觀化了的人的主觀體驗。我們今天的藝術所要表現的正是這個東西,即“美”。當然,并非一切文字都是書法,一切印章都是篆刻,也并非一切美都是藝術。如百靈鳥的叫聲和《空山鳥語》同樣好聽,但它不是藝術。與之相反,石器時期的繪畫和非洲叢林中的原始民族舞蹈,盡管簡單粗糙,但卻仍然是藝術。所以,我們認為,藝術作品的產生之所以叫創作而不叫制作,就是因為它自身的獨立的“美”。這個特性的“美”,就是不同之中有相同,相同之間又有不同,是個性表現和獨特的理解。馬先生的篆刻藝術作品里所表達出的那種氣息與藝術所要表達的東西正好不謀而合。所以,藝術家的工作既沒有現成的和明確的概念及工具可供參考和使用,也不可能用一種規范化的語言來進行一系列的陳述性表達。他們表達情感除了創造一種可以訴諸于感覺的形式之外,別無他途。
黑格爾曾把藝術分為三大類——象征型藝術、古典型藝術和浪漫型藝術。他認為象征型藝術的特征是物質重于精神(或者說形式重于內容),古代東方藝術都是象征藝術,建筑是象征藝術的典型代表。古典型藝術的特征則又是另外一種情形,是精神與物質的一種有機結合(或者說內容與形式的和諧)。這種和諧使藝術幾乎到了完美的境界。其典型代表是古希臘和古羅馬的雕刻。浪漫型藝術的特征則是追求精神超越物質(或者說內容服從形式)。浪漫型藝術使藝術進入一種理想境界。繪畫,詩歌和音樂是浪漫藝術的典型代表。也只有在這種藝術的藝術作品中,特別是在詩歌中,內容(精神)才真正超越形式(物質)的規定而自由地表現出一種自我來。這種超越性就決定了藝術家不同于哲學家,更不同于科學家。浪漫型藝術與其他任何形式的情感表現形式又不一樣。只有他們的這種創造,才是獨一無二的情感的表現形式,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種成功,如果不是,那就是不成功的。馬先生的藝術作品正是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一種情感的表達,因此,也是極具浪漫色彩的。
我們可以從這么幾個方面來分析馬先生及其作品。首先是他自由的精神。馬士達先生的個性是率真的,但又不天真,“真”是他的本性,用他自己的話說,“不假”。這其實就是一種自由的精神。而藝術從一開始就擺脫了現實的束縛而具有某種自由的性質,也是人類自由的一種形式,其表現在藝術作品中就是一種人的本質的對象化的精神現象——美。“美”才是藝術作品最高最后的標準,只有抓住了這一根本的東西,一切事物才可能是藝術。馬先生的作品就有這樣一種獨特的自由精神,并表現出一種獨特的客觀化了的人的主觀體驗的美感,所以是藝術,也是美的藝術。
其次是他與眾不同的性格。馬先生無論是在生活上還是在藝術上,特別是在他的藝術作品中,處處都表現出一種與眾不同的東西。生活上他不拘小節(“不假”),藝術上憑自己的理解,既不盲從于人,也不固步自封。用他自己的話:不自欺,也不欺人。因此,他的作品也與眾不同,并充滿無限的生氣和新意。
再者是他認真的態度。馬先生自認為自己是不聰明的,但也并不笨,至少還是清楚自己的,不至于太糊涂。自己喜歡的東西,就認真對待,從不馬虎,認真卻不過于認真,是“認真與不認真”之間。先生認為任何事情,過于認真了,就容易死板,以至于難以突破。而不認真就容易草率,特別是藝術,一旦草率就俗、就淺,甚至極易走向非藝術。所以,馬先生的成就,一靠認真,二靠靈活。其實,認真是一種態度,也是必須,“不認真”又是一種靈活,一種創意,而認真與不認真之間更是一種超越,一種境界。
另外,我認為喜愛音樂也是先生的“一劑良藥”。音樂與繪畫是姊妹藝術,也是浪漫型藝術典型的代表。對音樂藝術(特別是器樂)的情有獨鐘和獨特理解,可能也是馬先生的一大優勢。無論是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還是藝術作品中,音樂的成分隨處可見。
總之,馬士達的篆刻藝術,是一種不隨流俗的獨特追求,在當代屬上品。他的創作有“法”,但不拘泥于“法”,有“古”,又不是搬“古”,也不是套“古”,而是拓“古”、化“古”,是既有古人,也有自己,既有傳統,也有新意,并更具現代意識,是“技”與“道”的和諧統一。研究中國當代篆刻藝術,尤其是當代篆刻藝術史,先生是一重鎮,無法繞行。先生的作品,方寸之間,可謂乾坤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