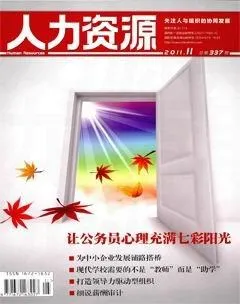君子的義利觀
職場和學校的一大不同在于,學校是“求真”的地方,而職場是“求達”的地方。什么是“達”呢?”達”就是效率、效益或利益,也就是以盡可能少的成本,獲得盡可能多的收益。簡言之,就是求利,為組織求利,為個人求利。所以“義利關系”問題是所有身在職場的人都要回答的問題,根據一個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看出他或她是不是一個真的君子。
關于義利關系的爭論在中國已經進行了兩千多年了,有人主張“重義輕利”,有人主張“義利并舉”,也有人主張“利字當先”。“義利之辯”是從孔子開始的,爭論各方也主要用孔子的觀點闡述自己的立場,如,
“重義輕利”者抓住孔子的兩句話: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為于利”和“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竟然發揮到把“義”和“利”和人的欲望絕對地對立起來、“存天理,滅人欲”的地步,直接導致國人思想僵化,羞于言利,影響了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持“利字當先”主要是揪住孔子說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這句話,富而可求,即使執鞭去給別人趕馬車我也愿意干,主張“重義輕利”是偽君子,嘴上重義,實際上重利,也是一種把義利完全對立起來的觀點:而主張“義利并舉”的人是對孔子義利思想的簡單折中,也是不得孔子義利關系的思想要領。
“義利之辯”本身有一個悖論,它是孔子挑起的,又是孔子說得最明白的。問題出在孔子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就“義”和“利”說過很多話,后人不能完整準確地理解,往往抓住孔子的一兩句話,甚至是半句話就當作自己立論的根據了。其實全面看一下《論語》,問題就解決了。孔子論“義”的話說了很多,論“利”的話也有一些,而將“義”和“利”放在一起說的地方不是很多,第一句在《里仁》第五章里,孔子說過: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真君子是實話實說、不裝腔作勢,孔子是真君子,他直言富裕和顯貴是人人都想要得到的,但如不是正道得來的,就不能要;貧窮和低賤是人人都厭惡的,但不用正當的方法去擺脫它,就不要擺脫。第二句是“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那么義而富且貴呢?孔子雖然沒說,但他的意思是很明顯的,是人人的追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為于利”,孔子的義利觀中,這句對后世的影響最大,經過后代儒家的發展,直接導致義利的尖銳對立,非此即彼的義利觀。聯系孔子在其他場合的義利關系論述,和講這句話的語氣,我認為孔子的本意是,君子遏事把義放在第一位,小人只知道利。而人們遇事時,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優先次序上是不言自明的。孔子思想和市場經濟是契合的,他的義利觀尤其契合。市場經濟建立在人性利己這個假設基礎之上,這個假設認為人們做任何事時都是優先考慮自己的利益。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說過:
“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師或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用市場經濟的觀點看,世人都是商人,都在買著什么,賣著什么,比如,官員“出賣”服務,教師“出賣”知識,哲學家“出賣”思想,牧師“出賣“同情,得到的錢購買自己需要的物品。任何人作為買方時,都是希望所買的商品價格低些,作為賣方時,無一例外地希望價格高些,這還不能證明任何人都是利己的嗎?孔子是真君子,真君子“不裝”,就像他沒有掩飾愛當官和愛美一樣,他也沒有掩飾自己愛財。在這個前提既定時,剩下的問題就是怎樣謀求自己的“富且貴”了,孔子認為,只要手段正當,謀利是人性。如果手段不正當,或一時找不到謀利的正當手段,就應該“安貧樂道”。從經濟學角度講,愛財是追求最大利益,有道是約束條件,用運籌學中線性規劃的語言表達就是在道義的約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市場經濟中的人都應該按這個模式在市場上工作和生活。這就是孔子的義利觀,用一句話說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人們進入職場,目的多重,但掙錢謀生肯定是一個重要目的,對今天職場中人講,一個月沒有幾千元的收入,就不能養家糊口,更談不上人的全面發展了。一個剛進入職場的人,收入不多,可能連對象都難找。所以,不要恥于談錢說利,只要取之有道,錢或利是多多益善的。只需要注意的是:絕不能發不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