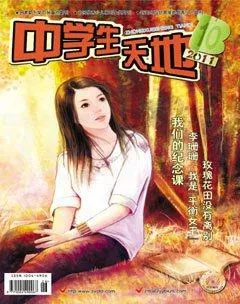歷史沒有柯南
動畫片《名偵探柯南》里面有著不變的一幕:小個子偵探柯南沉著地推一推眼鏡,胸有成竹地說——真相只有一個!然后他就找個代言人(多半是毛利小五郎),用麻醉針讓他沉睡,然后公布兇手的名字。
這種激動人心的時刻,只在推理劇中出現。我小時候也曾經以為,歷史和推理劇一樣,真相只有一個,就像每次期末考試的時候必然會在考卷上出現的填空題一樣。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1842年中英雙方簽訂《南京條約》;1895年,《馬關條約》;1898年,戊戌變法……作為學生的我們,似乎記住了年月日和某一相關的事件,就掌握并通曉了歷史。
“歷史只有一種版本”的錯覺一直延續(xù)到了中學畢業(yè)。這不能責怪任何人,當一個事件成為一道填空題出現在考卷上,并且擁有唯一的正確答案時,我們當然就以為歷史只有這么一個版本。
幸好,大學里的老師給我們開長長的書單。比如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看的時候,真是豁然開朗:歷史還能這樣寫啊?一個平平無奇什么都沒有發(fā)生的年份,一個會考、高考中都不可能成為知識點的年份,居然暗藏了明朝所有的機密。那本書,讓我明白,歷史中那些具體的年份固然重要,但是那些重大的事件往往是一系列偶然和必然相角力之后的結果。記住年份根本無助于理解歷史,重要的是了解“為什么”這個事件會如此發(fā)生。而這個“為什么”,永遠都不在書本的標準答案上。
歷史考卷只有一種版本,但是歷史可能有多種角度。
有一年我去歐洲旅行,在比利時待了一段時間。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的市中心有個巨大的皇家公園,樹陰參天,我在那里逗留了很久。那里有一座石碑,上面有一段文字,寫的是:“偉大的比利時民主先驅在非洲解放了處于水深火熱中的剛果人民。”這座石碑儼然是歌頌比利時給剛果帶去了文893fa633e024bde878700a6cf49db23408928506c45f42ef48c1e1a0d76605eb明。可是,當時我的班上有個剛果來的同學,他提到比利時就十分生氣,他說當年比利時完全是在剛果殖民,將無數的剛果人作為奴隸運到了比利時。“你可以去看他們的歷史博物館里的照片,黑人像猴子一樣套著項圈,這是他們所謂的解放嗎?”他說。他沒錢也沒法在一個國家的公園里樹立一座石碑來反對殖民者的良好自我感覺,歷史總是勝利者的書寫本。但是他提醒著我:歷史有這一面的寫法,必然有另外一面的敘說。不必太心急去判斷哪一面的敘說是真相,重要的是讓所有的敘說都浮上水面來。
漸漸地,我覺得歷史就像一幅巨大的拼圖,每一種敘說的版本,都是這塊拼圖上的一小片碎片,但是每搜集到一片,都能讓我們更接近原來的面貌。我們小時候死記硬背的年月日,是一份非常抽象的歷史。就像有人給了我們一幅拼圖,并告訴我們,這是一匹馬。但這是怎樣的一匹馬呢?是一匹白馬?一匹有著美麗眼睛的千里馬?一匹曾經在戰(zhàn)場浴血奮戰(zhàn)的馬?我們都不知道。那些滿足于知道“這是一匹馬”的人,就會失去真正認識這匹馬的機會。那些開始好奇并開始搜集不同版本拼圖的人,將靠近歷史的真相。
歷史是很有趣的東西,它沒有固定答案,它和歷史書給你的印象不一樣,你可以用自己的角度去解讀它。所以,你還會覺得許多年以前的事情和你沒太大關聯(lián)嗎?你還會覺得歷史課無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