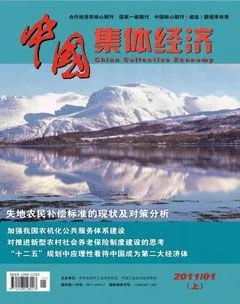“最優通貨膨脹率”理論的文獻綜述
摘要:文章對“最優通貨膨脹率”理論現有文獻的分析,發現理論研究文獻的關注視角各不相同,因此,各種結論之間難以形成共識;實證研究文獻提出“2%的最優通貨膨脹率”的觀點,雖然增強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操作性和可調性,但是2%的結論本身缺乏堅實的微觀基礎。現有文獻中多樣化的研究視角和方法,以及各種結論中不盡人意的方面,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借鑒依據和廣闊的研究空間。
關鍵詞:最優通貨膨脹率;弗里德曼準則;次優理論;鑄幣稅
通貨膨脹作為一種經濟現象,具有多方面社會經濟效應,一方面存在刺激產出、提高消費、增加政府稅收等方面的積極效應;另一方面也存在降低儲蓄、削弱投資、扭曲財富分配、加劇貿易逆差等方面的消極效應。既然通貨膨脹存在正負兩方面效應,那么政府應該追求“最優的通貨膨脹率”(the optimal rate of inflation)是多少?為解決這一問題,國內外學者們分別從理論和實證角度進行了深入研究,形成眾多卓有見地的觀點。
一、弗里德曼準則
新貨幣數量論的提出是以弗里德曼為首的貨幣主義者對現代經濟學理論研究的一個突出貢獻,其理論核心就是弗里德曼準則(the Firedman Rule)。弗里德曼準則(Firedman,1969)指出:在一個經濟穩態中,當名義利率為0時,貨幣增量和通貨膨脹率為最優。
這是因為通貨膨脹率猶如一種“隱形”稅率,會扭曲公眾部門的經濟行為,對社會福利產生負作用。Cooley and Hansen(1989)認為,貨幣能節約交易成本,便利日常交易活動,所以公眾持有貨幣能產生直接或間接效用,從而提高福利水平。但是,公眾持有貨幣存在機會成本——名義利息收入,而社會增加貨幣的成本幾乎就是國家印制鈔票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計。這樣一來,當名義利率為正值時,貨幣需求的邊際成本高于貨幣供給的邊際成本,此時必然產生低效率。因此,要降低這種低效率,就必須將貨幣需求的邊際成本降為0,即名義利率等于0,名義利率近似等于實際利率與通貨膨脹率之和,實際利率是資本邊際收益率,應該是大于0的正值,則名義利率為0時的通貨膨脹率必然為負值。所以,弗里德曼準則告訴我們“最優通貨膨脹率”等于實際利率相反數的通貨緊縮率。
弗里德曼準則始終是理論界關注的焦點。Lucas and Stokey(1983)通過完整的經濟模型分析,從理論上系統地論證了最優通貨膨脹率的問題,證實了弗里德曼準則的正確性。但是,無論多么完美精妙的數學模型都難以彌補弗里德曼準則在現實經濟中解釋力和可操作性方面的不足。
首先,Phelps(1973)指出弗里德曼準則僅從公眾的貨幣需求視角考慮“最優通貨膨脹率”問題,而忽略很重要的一點:通貨膨脹作為一種“隱形”稅,不僅扭曲公眾部門的經濟行為,而且也為政府帶來一筆可觀的稅收——鑄幣稅。政府通過通貨膨脹獲取鑄幣稅收入也是不爭的事實,這種情況在拉丁美洲和南歐國家中比較普遍。Lipsey and Lancaster(1956)提出的次優理論也說明,當市場失靈出現時,政府適當干預市場,是抵消市場失靈、增進社會福利的次優選擇。鑄幣稅作為政府干預市場的手段,在抵消市場失靈時將發揮積極作用。所以,Phelps對弗里德曼準則的批評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Christonian(2009)對“Friedman與Phelps爭論”進行總結,認為Friedman和Phelps分別從貨幣和財政政策角度闡述最優通貨膨脹率的觀點,二者的分歧實際上是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分歧。
其次,如果弗里德曼準則成立,那么為什么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采用這樣的貨幣政策?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來自三個方面:一是現有的各種模型本身都存在著先天不足,弗里德曼準則雖然在這些模型中被證明是正確的,但在實際經濟運行中是否依然是值得信賴就很難說了。二是一些重要的約束條件被忽略掉了。一旦考慮這些約束條件,原有被證明是正確的結論就有可能被推翻。三是即便證明了弗里德曼準則是最優的,當把它作為一項政策來實施時,如何順利實施這項政策也是一個現實問題。弗里德曼準則的可操作性不強,也很有可能是由其實施過程中受到的阻力過大造成的。
二、Cagan的“最優鑄幣稅”理論
鑄幣稅是一國貨幣當局(中央銀行)憑借對貨幣的壟斷發行權,通過增發貨幣獲得實際收入的現象。二戰以后各國政府通過通貨膨脹政策籌集財政收入變得日益重要,在貨幣擴張中,發行貨幣量的一部分直接轉變化為財政收入,政府無償獲得了一部分資源的支配權,這實際上是政府向所有貨幣持有者進行非強制征稅——鑄幣稅。鑄幣稅的稅基是實際貨幣余額,稅率是通貨膨脹率,鑄幣稅收入等于實際貨幣余額與通貨膨脹率的乘積。
20世紀50年代以來,國外眾多學者致力于研究通貨膨脹率與鑄幣稅收入的關系。其中極具影響力的是Cagan(1956)的觀點,他發現通貨膨脹率與鑄幣稅收入之間呈現一種“丘陵”狀的Laffer曲線關系(如圖1)。即當通貨膨脹率上升時,起初鑄幣稅收入會隨之增加,達到頂峰(圖1中的A點)之后便隨之減少,最優通貨膨脹率就是實現鑄幣稅收入最大化時的通貨膨脹率。
Cagan(1956)認為,如果存在資源閑置情況,貨幣擴張不會或部分轉化為價格上漲,政府發行貨幣速度快于工資和價格調整速度,實際貨幣存量增加,鑄幣稅稅基增加,鑄幣稅收入也隨之增加,對應Laffer曲線的上升階段(圖1中曲線A點以前的部分)。隨著持續的貨幣擴張,充分刺激社會總需求,資源達到(或超過)充分利用狀態,此時貨幣擴張將全部轉化為價格上漲,公眾通過工資指數化,避免高通脹引起的損失,導致通貨膨脹率持續上升,并達到較高水平,此時政府發行貨幣的速度慢于工資和價格的調整速度,實際貨幣存量減少,鑄幣稅收入也減少,對應Laffer曲線的下降階段(圖1中曲線A點以后的部分)。
Cagan從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研究視角出發,得出“最優的通貨膨脹率等于政府鑄幣稅收入最大化時的通貨膨脹率(圖1中A點對應的通貨膨脹率π*)”的結論,但是Cagan的研究方法僅僅限于政府的鑄幣稅收入方面,只適用于財政當局單一部門的局部均衡分析,無法對整個經濟社會進行多經濟部門的一般均衡分析,因此,其“最優通貨膨脹率”的結論必然具有片面性,這也成為Cagan最容易遭受批評之處。
三、中央銀行的“最優通貨膨脹率”傾向
各國中央銀行都具有特定的效用(或損失)函數,并確定實現效用最大化(或損失最小化)的政策規則參數值。由于貨幣政策關注于“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因此,Svensson(1978)認為中央銀行效用(或損失)函數中應該包括實際產出(或就業)和通貨膨脹率兩個變量。Barro and Gordon(1983)根據不同國家對貨幣政策的偏好,設定了發展中國家中央銀行效用函數(見式①)和發達國家中央銀行損失函數(見式②)。
其中:y、y*、π、π*、U和L分別表示實際產出、潛在產出、通貨膨脹率、目標通貨膨脹率、中央銀行效用水平和損失水平;參數λ表示中央銀行在產出擴張和通貨膨脹之間的相對權衡系數。
Barro and Gordon(1983)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政策兼顧“促進增長、穩定物價”兩大目標,產出擴張對中央銀行具有正效用,所以λ>0;而通貨膨脹率對目標通貨膨脹率的任何偏離對中央銀行具有負效用,所以π以負平方形式進入效用函數(見式①),其貨幣政策目標是實現max(U);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目標注重“產出和物價雙穩定”,實際產出對潛在產出的任何偏離,以及通貨膨脹率對目標通貨膨脹率的任何偏離會對中央銀行產生損失(見式②),其貨幣政策目標是實現min(L)。
Walsh(1992)利用Lucas(1972)的理性預期模型,對U和L函數進行研究,得到實現max(U)和min(L)的最優通貨膨脹率。根據結果,Walsh認為中央銀行追求的最優通貨膨脹率是實現max(U)或min(L)的通貨膨脹率。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對貨幣政策目標界定的差異,導致發展中國家的最優通貨膨脹率高于發達國家,因此,發展中國家中央銀行的信譽也低于發達國家。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政策兼顧“促進增長、穩定物價”雙重目標,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較低,在制定貨幣政策時具有制造通貨膨的政策動機,最優的通貨膨脹率總高于目標通貨膨脹率,中央銀行信譽也因此受損;而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強調“產出和物價雙穩定”,中央銀行不必擔負刺激產出的義務,其獨立性和自主性較高,在制定貨幣政策時喪失了制造通貨膨脹的政策動機,最優的通貨膨脹率等于中央銀行的目標通貨膨脹率,中央銀行信譽相應較高。
Walsh從中央銀行效用(或損失)的角度分析了中央銀行對于“最優通貨膨脹率”抉擇的政策傾向,其結論在相當程度上解釋了發展中國家物價水平居高不下的現象,因此,也得到了廣泛的理論和實證支持。但是Walsh的模型易遭批評之處在于如何確定中央銀行在產出擴張和通貨膨脹之間的相對權衡系數λ,貨幣政策委員會一般采用兩種方式明確或含蓄地確定λ:少數服從多數原則;顯示性偏好實驗。但是無論采用哪種方法,λ的確定都具有很強的主觀性和隨機性,從而影響到貨幣政策的規范性、持續性和可靠性。
四、“最優通貨膨脹率”的實證結果
“最優通貨膨脹率等于多少?”對于這一實際問題,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深入研究。Schmitt-Grohe and Uribe(簡稱SGU,2010)建立了具有財政和貨幣政策合作的最優通脹模型,主要從最優政策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角度以及價格粘性和工資剛性對最優通脹率進行分析,他們認為工業化國家的平均最優通脹率為2%左右;Coibion,Gorodnichenko and Wieland(簡稱CGW,2010)使用了簡化的新凱恩斯兩部門模型,使用美國經濟實際數據,采用Woodfood(2003)基于效用的福利函數二階近似方法,從貨幣政策角度和市場微觀結構對不同情境下的政策福利效應進行了研究,結論表明穩態的最優通脹率在1%-2%。SGU和CGW的實證結是對弗里德曼準則的顛覆。
Williams(2009)認為,由于存在名義利率的零邊界約束(Zero Lower Bound,簡寫為ZLB)(即名義利率必須高于0),中央銀行以2%的最優通脹率目標作為貨幣政策對ZLB的緩沖器,能夠為制定政策工具提供便利,但是,由于2%的最優通脹率并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而僅作為貨幣政策工具實施的技術性處置方式,為經濟危機埋下伏筆。
五、結束語
通過對以上研究文獻的綜述,我們發現“最優通貨膨脹率”的理論研究文獻往往集中于單一視角:弗里德曼準則立足于公眾部門福利;Cagan的觀點立足于政府部門的鑄幣稅收入;中央銀行的“最優通貨膨脹率”傾向立足于中央銀行效用最大化(或損失最小化)。研究視角的差異,導致觀點之間的分歧,正如Christonian(2009)所總結的那樣,“一切分歧都源于各方研究立場和方法的不一”;而實證研究文獻得出“2%的最優通貨膨脹率”的結論雖然為貨幣政策提供了便利的操作空間,但是,其結論本身缺乏堅實的微觀理論基礎。然而,當前對于“最優通貨膨脹率”問題呈現出“百家爭鳴、懸而未決”的研究態勢,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鑒和廣闊空間。
參考文獻:
1、姚長輝.貨幣銀行學[M].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