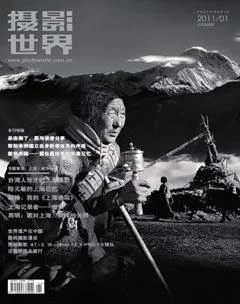從“黑暗面”照片想起
2011-12-29 00:00:00章開元
攝影世界 2011年1期

什么是攝影師鏡頭里的“黑暗面”無須贅述,看看這幾張照片自然就明白了。
英國攝影師唐·邁庫林當年就是靠“黑暗面”照片起家,現已躋身世界頂級紀實攝影大師行列。他的同國前輩比爾· 伯蘭特,也是位擅長拍社會“黑暗面”的紀實攝影大師,作品不光內容陰暗晦澀,形式上黑色調子也極為濃重。他倆還有一共同之處就是專拍自己祖國的“黑暗面”,是攝影界里典型的“不愛國”分子。黑暗面的英文為SEAMY SIDE;與之相對應的英文是SUNNY SIDE;后者一看就知道是陽光普照;SUNNY SIDE同時也是美國俚語“煎雞蛋”用詞,即形容蛋黃朝上的那一面。通常一提到什么什么的“黑暗面”,總會令人不寒而栗,它是“倒霉、挫折、蕭條、不振、末日”的總匯,是攝影師的一個禁區,尤其是表現本國的,偶爾幾張還行,多了輕則說你不愛國,重則有人會把你的飯碗給砸了。
從傳統觀念出發,東方人對黑暗一向就沒什么好感,現在已經好多了,從前黑色總容易跟晦氣死亡聯系到一起,尤其在中國,別說黑暗,連灰色都跟著招人嫌,灰溜溜地做人,灰蒙蒙的天氣,一聽就打不起精神。西方人則不,且不說黑烏鴉被英國王室奉為吉祥物,黑狗、黑馬的黑色都是品種最優良的標志性顏色;吃的東西,黑面包(被譽為糖尿病人最佳主食)、黑巧克力、黑魚子醬都是上等食品。一直以來,經典晚禮服,官方座駕也都是清一色的黑,其他顏色概不可。西方人不僅對黑情有獨鐘,對暗淡無光,夕陽西下也同樣蠻不在乎,朝向最好的房間就是面西的;黑燈瞎火的燭光晚宴,在燈光幽暗的環境中聊天是上流社會的傳統,盡管電燈是他們發明的,但在這些地方卻大受限制。而東方民族正相反,居住講究正南正北,寬敞明亮滿室生輝,連皇上辦事都標榜正大光明;黑乎乎絕對不行。老外的油畫講究的是在黑底上涂彩,咱們的水墨丹青講究的是在白紙上畫黑,兩者截然不同。
以上習慣對攝影風格與手法有重大影響,邁庫林的照片黑色濃重,給人以黑云壓城城欲摧之感。即便不是黑白照片,老外的彩色片子也普遍色重,讓咱看上去頗為“費眼”。就內容而言,西方攝影師的新聞紀實作品普遍反映的是社會“黑暗面”,形勢一片大好的“陽光”照片那就不叫攝影,只能算是“商業宣傳”與廣告等同。這種情況自打攝影問世以來即如此,的確不是想改過來一下子就能變過來的。
我們的攝影與世界接軌,首先要從觀念上改變,即使不是馬上,至少也要有所準備,尤其是對反映所謂“黑暗面”的照片,要給予光明的看法,寬容的態度,不同以往的理解。在西方新聞界看來,新聞的本質就是(除戰事之外)迅速地報道壞消息,事情越壞,新聞的價值越大。1912年泰坦尼克號沉沒的消息傳至紐約,那時收音機沒普及,電視更沒有,報紙沒那么快,通訊社便雇人將新聞隨時手寫到第五大道的新聞公示牌上,造成萬人空巷交通阻塞,通訊社卻股市飆升狠賺一筆。中國文化大革命時總習慣說“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其實根本不咋地。如今現實多了,也提倡一個民族要有憂患意識,居安思危;其實露露自己的軟肋,接受點國際援助也沒啥了不起,世界各國都一樣。除去國家,對于一個人而言,失敗、挫折、背運只要不永遠相伴,未必是壞事,處理好了倒可能因禍得福。
現在的世界是一個全人類集體包裝,集體涂脂抹粉,整個站在高跟鞋上的世界;尿不濕、不粘鍋是最響亮的招牌,鬧得個年輕輕的女同志竟讓人看不出她原本的面色和身高,許許多多人生本質的東西被掩飾,被淡化,甚至也沒人關心;個別媒體一提到社會的黑暗面就緊張得不得了,個人一提到挫折就好像從此一蹶不振,特沒面子。其實,人從一生下來就遭遇陽光和黑暗,挫折與勝利交織為伴,學走路的時候摔跟頭,把不該吃的東西放到嘴里,一切都是習以為常的事情。正常和堅強的人應該不懼黑暗與挫折。在電燈沒發明以前,晚上照明是一件極昂貴的事情,絕大多數人在那個年代都要忍受漫長的黑夜,所以在1999年美國評出的千年百位名人中,把發明電燈的愛迪生列為第一,因為他的發明使人能在晚上讀書看報,不僅令文化水平得到提高,等于人的壽命無形中也延長了四分之一。可是愛迪生只能幫助人類擺脫黑暗,卻無法擺脫挫折,一個政權的建立,一個偉人的誕生,一個事業的成就,一個家庭的生活,哪個背后沒有辛酸?哪個敢說從未經歷過挫折?如果說是沒有,那他一定是個死去的人。人生的軌跡就是從激情到平淡再到無聊;平淡和無聊是人生的常態,如何把這種常態不斷地變回激情,絕對是門耶魯不教、哈佛學不到的本事。忍受平淡和無聊、承認挫折和失敗并不意味是向它們低頭,在有意志、有理想、有作為的人的心目中,它們反而是催化劑,是動力。某種意義上講,如果說平淡和無聊是你的一對脾氣不好的孿生姐妹,那么挫折和失敗就是你的一對更糟糕的孿生兄弟。那又怎么樣,除非你不生活在這個世上,否則的話必須學會跟他們打交道。
古希臘之所以能成為西方文明的發祥地和奧林匹克的故鄉,這與他們特有的“悲劇精神”不無關系,德國唯意志論者尼采通過對希臘文化的研究發現,希臘人對人生的痛苦與挫折,艱難與恐懼有著深刻的感受和透徹的理解,面對黑暗莫測的未來,不消沉,不悲觀厭世,不逃避現實,而是勇敢地接受命運的挑戰,將思想準備和體魄鍛煉融為一體。希臘人的這種變消極為積極的人生態度體現了一種獨特的悲劇美。尼采還認為人只有處在悲劇文化的環境中,才能體察到世界真實的一面,才能承受人類所有的得失,才能使人生存的意志更加堅強。提倡所謂悲劇精神是用黑暗迎接光明,是用挫折換取勝利,是對立的統一,是自然的輪回。只有沒有意志的人才懼怕黑暗,拒絕挫折。從古至今流傳下來的幾乎所有著名劇種都是悲劇,喜劇則很快被人遺忘,同樣是這個道理。總之,形形色色的挫折誰也躲不開,只要是人總要生活下去,而且還應該比以前更好。在不朽的時間面前,黑暗都是短暫的,挫折也是“小意思”。作家海明威說過這樣的話:無論是誰,只有陽光而無陰影,只有歡樂而無痛苦,那就不是人生。以最幸福的人的生活經歷為例,本身是糾纏在一起的一團麻線,喪親之痛和幸福祝愿,彼此相接,使人們的感情跌宕起伏,游暢其間,死亡在這個時候都顯得平淡無奇,從厄運中解脫會讓你更加珍惜生命。在人生的清醒時刻,在哀痛和傷心的陰影之下,人們與真實的自我最為接近。
回頭再說照片,攝影師在創作題材上不應該受到太多的限制,至少不能給自己設限,至于是拍陽光面還是黑暗面各有所取,但也要承認,反映黑暗面的照片打動人的時候或許更多,就像悲劇的效果永遠勝于喜劇。目前的情況,照片的發布是有局限的,不可為所欲為,然而攝影畢竟是門藝術,好照片就是好照片,這個不是哪個人說了算的。攝影作為人生的反照和激勵斗志的手段,作為鼓舞人們擺脫愚昧和戰勝挫折的精神武器,我們應該對真實的寫照、艱澀的攝影題材給予更多的寬容和發表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