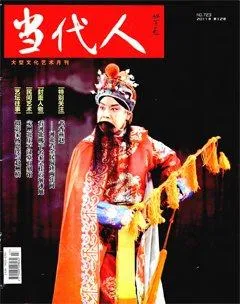攝影家楊恩璞與趙州橋
金風送爽,梨果飄香。
藍天下,古老的趙州石橋上走來一位身著草綠色攝影背心、肩背專業相機的攝影人,他叫楊恩璞。誰也不會相信這位精神矍鑠、談笑風生的教授,是位72歲的老人。
這是中國著名攝影家、北京電影學院教授楊恩璞先生第二次到趙州橋采風,這次來,與第一次相約古橋整整時隔30年。
帶著茅以升的故事一起來
歷經1400年風雨的趙州橋,它的身上寓滿故事,且與眾多古今名人結下不解之緣。被譽為“中國橋梁之父”的茅以升先生便是其中一位。
茅老長期研究、熱心宣傳趙州橋。早在1962年3月4日就曾在《人民日報》發表散文《中國石拱橋》,將趙州橋盛贊為世界上最偉大的石拱橋。之后,文章被選八初中語文課本,至今仍在沿用。本文的主人公楊恩璞,與茅以升先生有著不同尋常的關系。說不同尋常,不僅僅因為他的岳父與茅以升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同窗好友,還有一層關系就是,他為拍攝專題紀錄片,于1 980年6月與茅老一同來到趙州橋,這是茅以升先生發表《中國石拱橋》之后再次考察趙州橋。
我受河北省攝影家協會秘書長楊越巒先生委托,接待楊恩璞夫婦一行。一天時間里,我陪同楊先生參觀了柏林禪寺、趙州橋和古城其他國寶文物。午餐時,和善可親的楊先生特意囑咐,不進賓館,不進大飯店。他念念不忘的是30年前在我們古城曾經品嘗過的油酥燒餅。這樣,我們就隨意找了一家小吃店,點了當地的風味小吃鮮驢肉、油酥燒餅等。
坐在飯桌前,先生談著第一次來趙縣時的感受,談趙縣的變化,深情地回憶了他與茅以升先生一起來趙州橋時的情景:“1980年夏,北京科教電影制片廠接到國務院谷牧副總理的批示,基于當時許多著名國畫家深受‘文革’摧殘,有的重病纏身、有的年事趨高,為了防止他們的藝術失傳,要求立即拍攝一批介紹國畫大師藝術成就的專題影片,其中有:李可染、李苦禪、葉淺予、蔣兆和、吳作人等。我當時在該廠兼任導演,帶領電影專業學員實習,被分配拍攝《蔣兆和的畫》。蔣兆和是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教授,專工彩墨人物畫創作,其代表作有:《流民圖》、《醫學家李時珍》、《詩圣杜甫》、《曹操》和《給志愿軍叔叔寫信》等,并培養了范曾、馬振聲、韓國臻等新一代中國人物畫家。我們為了表現蔣先生的高超技法,在影片中設計了蔣兆和先生為茅以升現場寫生的情節,記錄了蔣老用毛筆進行素描造型的全過程。”
楊恩璞說:“蔣兆和先生將宣紙掛在墻壁上,他手握毛筆,案臺上是一方大硯,神情專注地看著不遠處坐著的茅以升先生。只見蔣先生將毛筆在墨硯中蘸了一下,接著他瞇起了雙眼,朝茅以升先生打量了一眼,就直接蘸墨在宣紙上作畫,先畫眉眼,接著畫鼻子、嘴唇,只幾秒鐘功夫,茅以升的形象就逼真地躍然紙上……”
通過這段拍攝,攝制人員慢慢就同茅老熟悉了。楊恩璞的夫人施湘飛插話道:“茅老1916年赴美留學,是我父親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同窗好友,回國后1926年任交通部唐山大學校長,1933年主持策劃和營造著名的錢塘江大橋。”在紀錄片拍攝過程中,茅老向攝制人員吐露了他內心的愿望,那就是他為了研究和撰寫《中國橋梁史》,希望再次親臨河北趙縣,參觀和考察趙州橋。聽到此事,攝制組就決定讓科學家茅以升和畫家蔣兆和同游趙州橋,讓他們加深彼此間了解,觸景生情,以便更好地刻畫茅以升形象。當時茅、蔣二老均年邁體弱,但聽到攝制組安排他們到趙縣看古橋,都表示出極大的熱情和興趣。
介紹到這里,楊恩璞甚是得意,嗓音頓時高亢起來:
“這就有了當年的趙州橋之行。1980年5月28日,我陪同茅、蔣二老從北京啟程,一路上,茅老談興很濃,他說,石拱橋不但形式優美,而且結構堅固。我國的石拱橋有悠久的歷史,幾乎到處可見,趙州橋橫跨在汶河上,是世界著名的古代石拱橋。這座橋修建于公元605年左右,到現在已經1300多年了,1965年河北邢臺地區發生大地震,它巍然不動,還保持著原來的雄姿,堪稱是世界橋梁史上的奇跡。”
“當晚,我們下榻在河北省政府的招待所。5月29日一早,便驅車前往趙縣,參觀趙州橋。那時候,橋體周圍沒有人行道,茅、蔣二老就漫步在河岸上,興致勃勃地仔細欣賞趙州橋每個細節,贊嘆著古代勞動人民的偉大創造。茅老興奮地說,從趙州橋身上,我們不僅看到了至今仍沒有過期的造橋技術,而且還感受到中華民族勇于攀登科學高峰的創造精神。蔣兆和先生聽到茅老這一席話,當下就有了想法,他決定,以恢弘的趙州橋為背景來構思創作茅以升的肖像畫,以景寫情刻畫當代中國科學家再創世界科技奇跡的決心。1981年,蔣兆和完成畫作,此畫曾在中國美術館展覽。”
在趙州橋的展覽館里,楊恩璞先生看到迎門陳列著茅以升的題詞:“歷經滄桑一千三百余載,李春的安濟橋依然為中華民族文化大放光芒。”欣然在題詞前拍照留念。他感慨地說:“見到題詞,恍如又回到30年前。我陪同茅以升、蔣兆和來到趙縣的情景歷歷在目。當年,我們曾受到省、縣政府的熱情接待,縣里還請茅老指導工作。為了更好地宣揚趙州橋,茅老回京后6月4日揮毫題寫了題詞,回贈趙縣。”
轉眼就是30年,今天楊恩璞又來到趙州橋,情不自禁地追憶起茅以升、蔣兆和兩位大師。
楊恩璞先生離開趙縣之后,我走訪了縣文保所,對當年茅以升等考察趙州橋的事情做進一步了解。經查證,當年與蔣、茅兩位大師一起來趙縣的人員還有蔣兆和的夫人、書法家肖瓊,茅以升先生的女兒茅于美等。茅于美在一段回憶中說:“1980年夏天,我陪同父親一起前往趙州橋。父親對橋的研究,除了查閱《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這些工具書以外,對實地考察也很注意。父親當時已是84歲高齡,但仍不辭辛苦地來到趙縣,他細心地觀察,對橋上每塊欄板上的雕刻都能詳細給我們講解一番。
大約四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10月,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茅老到邢臺市參加郭守敬紀念館奠基儀式,又特意考察了趙州橋。茅以升老人參觀考察趙州橋后,在自己的題詞前留了影。
30年后續寫古橋情
楊恩璞先生這次是專程陪著遠在美國教書的夫人施湘飛而來,同行的還有兩位來自石家莊市的影友。施女士是楊先生北影攝影系的同學,曾在北京科學教育電影制片廠、央視科教節目中心、峨眉電影制片廠擔任攝影師以及高級編導等職務。1998年赴美國,在jcpenney公司和哈維中文學校工作。她從美國飛來,主要目的就是拍攝趙州橋。她說,自己在美國大部分時間從事攝影和教學,在課堂上也為學生們講過趙州橋,但沒有一張趙州橋圖片是自己拍攝的,今天來就是要彌補這個遺憾。
除了拍攝趙州橋、柏林禪寺外,楊恩璞夫婦還要求到趙縣的其他景點走走。午飯后我又陪同客人參觀了趙州橋的姊妹橋永通橋、大觀圣作之碑和陀羅尼經幢。這樣,趙縣五處國寶文物一一納入了兩位攝影大家的鏡頭。
我們這些身背“長槍短炮”的年輕后生,一邊跟隨楊恩璞教授學習拍攝,一邊與他交談,對先生的經歷也有了大致的了解:楊先生小的時候,家里比較富裕,所以有條件較早接觸攝影,考取北京電影學院那年,他還不滿17歲。畢業后留校,在攝影系教學。在學院一千就是50年。他說,自己很留戀這半個世紀的時光,母校的教育不僅讓自己學會了專業知識和技能,而且懂得了怎樣用電影為國家、為老百姓服務。
楊恩璞學攝影、教攝影,最大的愛好還是攝影。在伴隨楊教授在趙州古城的采風過程中,他的活躍和激情總能感染我們這些隨行者。遇到好的畫面,先生就會主動地與我們交流,探討拍攝的角度、構圖等問題。
在柏林禪寺的萬佛樓拍攝時,楊教授主動站在欄桿處當起了模特,讓隨行的我們分別來拍。拍完,他走下臺階逐一點評。當發現小朱所拍攝的人物圖片,頭頂上方的牌匾影響畫面效果時,當即告訴他怎樣選取角度,如何構圖。
他還不停地把自己從事攝影工作中所得所悟,傳授給我們:要想在攝影方面有所成就,一般要跨越四個臺階,即:技術、技巧、語言和獨創。“技術”,就是掌握攝影器材的使用方法,古人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技巧”,就是運用攝影技術表現出造型美感。“語言”,就是要求攝影人走向世界,擁抱生活,進行有主題、有情感的創作。當技巧發展成敘述你所發現的生活故事、或抒發你對生活感受的表現形態時,技巧也就拓展為攝影視覺語言。這時,你所拍攝的作品從形式到內涵都有社會和審美價值。“創新”,藝術貴在創新,如果老是重復他人或自己的模式,也就不是藝術品,充其量只是作坊加工的工藝贗品。攝影創新沒有什么靈丹妙藥,除了提高自己各方面修養外,主要靠自己真正投身于生活,發揮獨立思考,腦勤手快反復實踐,用自己的視點發現題材,用自己的方式敘事傳情。
楊恩璞先生回到北京后不久,我便收到了先生發來的電子郵件:“感謝你的熱情接待。與趙縣闊別30余年,舊地重游感觸良多,看到了這古老的大地煥發著令人振奮的新時代活力。”先生隨信發來了幾幀采風照片,其中有風光攝影、也有他在薛家燒餅鋪拍攝的民俗攝影作品,令人驚詫的是,先生將自己的作品稱為習作。“習作”兩個字叫我感動了良久。
(責編: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