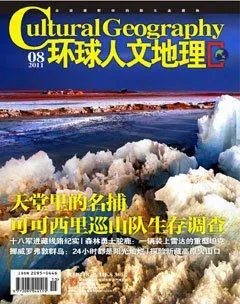記者手記:回望英
在可可西里采訪的時間段,由于環境等各種原因,發瘋似地想出去。尤其當走出昆侖山口時,腦子里甚至還浮現出那首蒼涼的秦腔《蘇武牧羊》:“千里的雷聲萬里的閃,北海的牧人就往家趕,登上長城就往南看,眼含淚水就望長安……”.
奇怪的是,當登上返程火車的時候,我竟然又開始發瘋似地想念這片土地。
我想念昆侖山和玉珠峰,盡管它們是如此的暴戾。
最震撼人心的古典藝術總是悲劇式的。我想念那座屹立在山口下的索南達杰紀念碑——有人說,一個將軍最好的歸宿,就是在最后一場戰斗中被最后一顆流彈擊中心臟,這位近乎神人的勇者索南達杰,也許沒能完成這個悲壯,但他的精神早已鐫刻在這里的每一塊石頭上。
我想念我的兄弟秋培扎西。這位扎巴多杰的小兒子,是巡山隊少壯派的代表人物。從我來到可可西里開始,他被才旦周局長任命為我的保鏢。他現在在干什么呢?又與兄弟們一起進山了嗎?在巡山途中有沒有遭遇暴雪或沼澤圍困?或者是正在期待著陰天——可可西里內的河流上午水淺下午水深,沙灘往往被太陽曬得滾燙,隊員們赤腳渡河很容易燙傷腳,所以,陰天早上渡河是最佳的選擇……
我還想念那些保護站救助中心飼養的藏羚羊。這群從盜獵分子的槍口下,或者猛獸的利齒下逃生的小家伙們,每天有按時吃奶嗎?它們能平安過冬嗎?可可西里的冬天,可是零下40℃的大風天……
相比自己身體的恢復,更讓我高興的一條好消息是,截至發稿時,遭遇大雪被困在太陽湖3天的那支巡山隊,已經沖出了險境——數日前得知巡山隊被困的消息,管理局已經緊急派出了救援隊,但由于夏天冰川融化,救援隊很快也被困在了庫賽湖沼澤區難以動彈,情況緊急,局長才旦周親自率領第三梯隊再次進入無人區:“千萬不要再下雪了。不然,只能向蘭州軍區航空兵求救了。”
前人說過,世間一半是地獄,一半是天堂。對可可西里而言,我找不到比這句話更合適的評語了。當我以記者的身份來到這里與巡山隊同吃同住的時候,就已經深刻地感受到了其中的艱苦。可是,我僅僅是過客,這群常年累月在這個環境下生活的漢子,他們的感觸是否比我更深刻,或者已經麻木呢?
我們無從得知。但可以肯定,他們就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