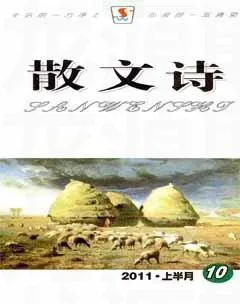望鄉
望鄉
從故鄉退去,我遠到天涯。
樹葉凋零,新墳瘋長,熟悉的人一個個老去。他們夏天坐在樹陰下,冬天偎在爐火邊,只打盹,不說話。
我在天涯遙望故土。飛鳥在高空掉下一片羽毛。苦楝樹上,一只空空的鳥巢在風中戰栗,如同我松散了的老骨頭,簌簌地落下塵土。
收拾好行裝,我在故鄉與天涯之間,來來回回細數落葉。
羊角風一陣強一陣弱,我一陣清醒一陣暈眩,找不到來路去路,我是一只迷途的螞蟻。
愛我的人躲在黃土之后避而不見。我在夜晚一次次從夢里醒來,熟悉的人在夢里一言不出,醒來后再也無法和夢中人對話。
故鄉,我該走還是該留?我已沒有了問話的氣力。
故鄉的石榴樹
如果那株石榴尚在,那些果實,應該將我虛空的日子填滿。
在長安,我打馬過秦嶺,隨身攜帶的三千顆石榴,從高高低低的棧道奔流直下,將偌大個四川盆地,裝滿玉粒般透明的石榴籽兒。
艱難地過涪陵,渡烏江,我從險峻的唐詩邊緣,爬過蜀道。帶著一粒石榴籽,我栽種在遍地巫風的楚國。引頸長嘯,石榴花再次開成火焰,而我,被風,吹到天涯。
今夜,我悄悄地向故鄉走去。月黑風高,我像蒙面的劫匪,潛入一株石榴樹的影子下,我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石榴樹是否被日子壓垮。
突然,一陣風起,一個又一個拳頭砸向我,我的詩句青面獠牙。夢的翅膀倏忽斷裂,我墜落在故鄉折斷的石榴樹下。
在故鄉,我的心是開裂的石榴。我牙齒脫落,張開嘴巴,無法說出一個字、一句話。
你從遠方歸來
梔子花從你的身體里開出。
你用體香過渡舊愛新歡。做一次深呼吸,我忘記舊恨新仇,你就鉆入我的七竅,讓我處處失守。
愈是靜夜,你的香氣,愈加響亮。
你在那株肥碩的綠葉梔子里敲鐘,隔著一重又一重山,我聽到了梔子花洗心洗肺的安慰。
今夜,你從遠方歸來,我守著燈花,反反復復捻撥。那婉麗的燈花,已經開成五月的梔子。
六月
不下雨,不流火,我安靜地坐在一株準備揚花的水稻之下。
雨季將臨。我要趕在下雨之前,讓稻花落滿我的頭發,我不是一個稱職的詩人,寫不出驚世絕句震響詩界,我只能像一個老實的農民,與水稻對話,聽流水細語輕言,將自己的心事漚爛于腹內,然后作為肥料,施于田間,等待飽滿的谷粒,給我安慰。
這個六月,大力神杯在遠處閃著金光,我聽到滿世界狂歡的嘯叫。
只有我,安于一隅,等待一株同樣金黃的稻谷,給我頒獎。
花兒朵朵
鳥總是棲息在高枝。它們的鳴叫,讓一朵又一朵的花綻放。
在五月的天空,那些花越開越高。天空藍得實在有些過分,詩人木木說,天藍得想叫人自殺。我相信不僅僅只有她才有這樣的感覺,只要靈魂尚未被塵埃污染的人,都會渴望著藍色的誘惑與幸福。
鳥聲清脆得似乎一切都要淪陷,仿佛有什么東西即將垮塌,我被圓潤的鳥鳴堆埋。
我有些發怵,恐懼墜入無窮無盡的藍。那些失去參照的飛行,將同時讓我成為時間的俘虜。
花兒朵朵開,紛紛揚揚如同一場又一場的大雪,它們連同鳥鳴,把這個世界喧騰成一個讓人忘卻一切的天堂。
風中的花瓣被鳥鳴吵落,幻化成無法辨識的色彩。此時,我不知道哪些是花瓣,哪些是鳥鳴,哪些是我墜落的詩句。
像森林—樣的手臂
那些高舉的手臂,森林一樣指向天空。
天色將晚,夕光將成片的森林投射出頎長的黑影,人們漸漸沉入土地,只有舉向天空的手,叉開五指,企圖抓住最后的機會。
我相信這些深入大地的腳趾。一定會像發達的根系,在竭力吸取最后的養分。而森林在枯萎,它們已經無力回天。
天色越來越暗,手的影子行將消失。突然,一陣風來,無數的手臂被吹向一邊。
我試圖與它們做最后的握別,那一刻,我的雙手突然軟弱無力。
木
他相信自己前世為木。今生,他反反復復躺下,將自己一截截鋸斷,分發給每個夜晚。
他不想那個斷面上的年輪,只橫臥在大地。
沉默,是他在夜晚對白晝的發言。夢是他的詩句。
他相信自己今生為木。他是不死的楊柳,只要靠著泥土,即使倒下,也會發出新綠。
豎著是生,橫著也是生,橫豎都是一樣。
柳線如絲,娥眉似葉。他把不死的盟誓寫在死亡之書的封面,在萬劫不復的死中永生。
籬笆
我不能給予這些籬笆任何新鮮的評語。
塵世中,這是慣常的所見——在菜園,或者某個空間,我們用竹片,抑或蒺藜,圍成一個圈圈,仿佛畫地為牢,有時真實,有時虛擬。
這些真實的或者虛擬的籬笆,能夠圈住一些什么呢?風可以穿過。小老鼠與銀環蛇也可以穿過,如果有人要不顧一切,也可以穿過。事實上,這樣的穿越是容易的,只是,我們有時為某種精神或者信仰之故,而放下了某些嘗試。同時也規避著某些風險。
這只是君子之約。過與不過,鉆過還是跨過,不在于一道虛線,而在于花開還是花落,在于籬笆之內的誘惑和籬笆之外一閃念的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