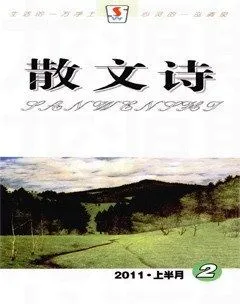高山仰止
松樟有一本散文詩集《憤怒的蝴蝶》,這個書名準確地體現了他的散文詩的特色。蝴蝶作為美的化身,是散文詩的象征,“憤怒”則是散文詩人對現實的邪惡事物出于正義感而產生的義憤填膺的一種反應。在當今的散文詩中,“蝴蝶”所在均是,“憤怒”者卻較為罕見。松樟是為數不多的幾位關注現實,敢于面向邪惡發出“不”的聲音的作家之一。我一直對他懷有深深的敬意。在不少作家專注于詩美追求而忽略思想關注的“氣候”下,松樟型的存在和發展尤其難能可貴。
不久前,他有一次新疆行,歸而得《伊犁短章》組詩,讀過后有一種情不自禁的喜悅,他的詩風出現了新的飛越:憤怒內斂而潛藏,蝴蝶的美姿卻在翩翩中更見豐滿。是否是他的詩美境界進入更成熟階段的一個開端?我這樣期待,且確信。
旅游詩泛濫。泛泛地就景寫景,只見客體,少有詩人獨特的感受,是常見的缺失。松樟的《伊犁短章》是以我為主的,我心目中的伊犁,我心日中的天山,思想的主體地位牢同,卻又不是堅硬的“骨頭”,而化為漫漫情思,溶化于詩的血液之中。《一切》全詩有一種如天山巍峨之體撲面而來的氣釋山河的氣勢,“讓你只可噤聲或膜拜……讓你只會聽見靈魂在軀體里瑟瑟地抖顫與驚悚”,這是一種令人油然而生的敬服,決非人為地強制,“連一棵可做佩飾的樹都不需要”,這才是真正的崇高。詩人以一種噴薄無前的速度,力度和節奏感,完成了他對于天山這一巍然存在的崇高美的頌歌,其音樂的內在潛能起到重要作用。《大天山》是《一切》的延續與升華,如果前者側重于山,后者則轉向了人,即在太天山面前的“小我”。“仰望”原是可以自上而下的。這不過是形式的“錯位”,詩人巧妙地轉向了“很多時候,我們不得不抬頭仰望,甚至被強迫著,將高貴的頭望向卑鄙或強權,望向腐爛或無恥”,這是直抒胸臆的“直白”,然而由于詩境提供了充分的準備,便絲毫不覺其牽強,而有一種水到渠成的痛快。“這就是世間的大,大到極致,才可以包容所有的小……”通常我們說,在詩中不宜“直白”,但并非絕對。我以為,松樟存這組詩中表達的思想,其藝術能量決不比他那些以象征手法表達的思想弱些。藝術無定則,一切由具體作品的意圖和語境而定。
作為一章獨立的詩作欣賞,《天馬》在思想與藝術結合的高度上,我以為更加完美。這里既有天馬揚蹄尋求自由的胸懷。又有“被一雙雙油膩的手來撫摸”的悲哀。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和構成的無奈,一一呈現在這短章之中,其思想內涵是渾厚的。由此我想起詩人白樺說過的一句話:“沒有思想就沒有文學”,強調思想的重要性,必須認識到她是文學自身的不可或缺的構成,所謂詩美,必須有思想美的成分在內。同時,我還想說,“只有思想也沒有文學”,這就是說,思想在詩中要渾然融匯在美的肌體以至血液之中。僅僅有思想還不夠,還要有詩美的全方位的渾然天成。我之所以認為《伊犁短章》在松樟散文詩中有其繼往開來的新的開創性意義,其根據便在于此。
《伊犁短章》以外,《杯子尋找水》和《擦肩而過》也是難得的篇章。
《杯子尋找水》的構思很新穎,將陶瓷杯形成中的水與火的關系作了充分的展示,而卻歸之于尋不到水了的“絕望”。一只杯子的命運的悲劇讓人能聯想到許多。《擦肩而過》不過是現代都市人日常生活的一幅小景、一個片段,人人親歷卻未必深思的這一種人與人之間冷漠關系的“確立”和流行,其實是“現代化”對于人的心靈“物化”后不知不覺間產生的效應罷了,比“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社會有過之而無不及。“會有人按響門旁的鈴聲么?”這一問,問得何其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