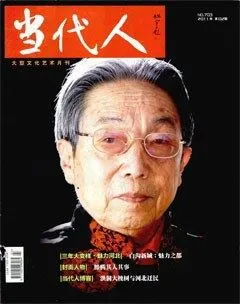集評孟東嶺
李維世(河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
中國山水畫的最高境界是意境。早在南北朝時期,著名山水畫家和理論家宗炳就提出了山水畫“神暢說”,提出“神本之端,棲形感類,理入影跡”的美學觀點。孟東嶺的山水畫,充分注意到了季節與地域的變化和特點;《暮色蒼茫看太行》云氣朦朦,霧靄氤氳,博大、蒼茫而深遠;《靜觀風云》筆墨恣縱,色彩明快,富有詩意。《秋思無垠》大氣磅礴,蒼茫渾厚,把太行山層層疊疊的山石、土坡、雜樹、衰草表現得淋漓盡致。“山如山,氣如氣,形如形”,具有“真山水”之川谷,之云氣,之煙嵐,之風雨,之陰暗,看此畫令人生此意,起此心,如真在此山中。從孟東嶺的優秀作品中,不難看出,他不僅注意意境、神態、情感的表達,還十分注重“真山水”的刻畫,盡力去追求情景交融、寓情于景、形神兼備。
王劍廷(詩人,畫家):
太行山古老雄奇,氣勢非凡,是經過血與火洗禮的地方,是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象征。孟東嶺把表現太行作為人生信念,那么執著,那么專注,那么一往情深。也許正是為了這樣一個平凡而偉大的藝術目的,他研讀燕趙歷史,遍覽太行古今,聆聽大山深處催人淚下的“昨天的故事”;他利用一切機會走進大山的懷抱,觀察山勢之縈紆高下、氣脈之綿亙貫通、林木之參差蓊翳。他還多次游歷泰山、華山、黃山、恒山、衡山、嵩山、天山等名山大川,回來對太行山進行反觀參悟……于是,太行山的險遠、夷近、高聳、宏闊,太行山的氣質、胸懷、性格,以及太行山的苦難、向往、貧瘠、繁榮,每每使他激動不已,化作無盡的智慧與才情。
孟東嶺的山水畫,自始至終都注意到“氣”的貫通,他遠取其勢,近取其質,如五代后梁荊浩所言“山立賓主,水注往來。布山形,取巒向,分石脈,置路彎,模樹柯,安坡腳,山知曲折,巒要崔巍。”他的山水畫表現的是太行山的魂魄和血脈,是太行山的寬厚和仁慈、偉岸與質樸。他筆下的太行山水是古景,也是今觀,太行山的山水風物在一位長懷“出世“之想又不棄“入世”之心的畫家筆下,有了太行山民的呼吸和脈搏。
劉金星(供職于河北省作家協會):
孟東嶺之所以能在眾聲喧嘩、世事蒼茫中發現美,除了畫家始終保持一份爛漫的心性、努力純正和純潔的畫風之外,還因為他對生活的摯愛,對生命的尊重,對藝術的真誠。孟東嶺當兵時多年居住在太行深處,經常與山民一同勞動,親身感悟到山民的淳樸和太行山的蒼茫厚重,轉業后他仍然對太行山情有獨鐘,多次到太行山寫生,在大自然中去捕捉靈感,置身太行,既用筆記其形,更用心畫其神,目觀心記,身游而神游,身入而神入。
孟東嶺的山水作品多以太行山野之趣為最,多畫原生態的山石溝壑,或鳥、或船、或房舍,寥寥數筆,恰到好處,細節生動傳神,仿佛春天新鮮的斑斕的色彩奔涌而來:山在動,水在流,草在生長,枝干在發芽,候鳥在眾聲啾啾,舟楫在輕輕撥動水聲。畫面氣韻生動,具有似靜還動的恍隱、轉瞬即逝的變化、模糊不清的幽暗、亦真亦幻的氣度。而且,對形的掌握嚴謹有序,對色的要求淡雅有度。每幅畫均欲予讀者豐富之宴,每一筆均欲向讀者陳述神游神八的風景,最大限度滿足了人們品畫、讀畫的審美欲求和愉悅心理。
(責編: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