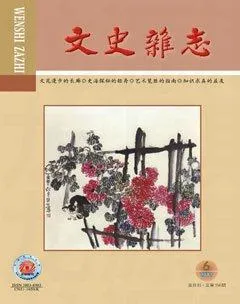作為音樂教育家的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魯國(今山東曲阜)人。孔子愛好音樂,學習音樂,且也注重音樂教育。他創辦私學所教授的“六藝”之中,音樂名列第二,《論語·泰伯》中所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就是說一個人的修養是從詩開始而完善于樂,可見他對音樂的重視。因此,孔子不僅是我國春秋時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同時還是卓有成就的大音樂家。他重視音樂在提高人的道德素質、凈化社會風氣和移風易俗等方面的作用,提出了音樂審美標準,開創了中國音樂教育之先河。可以說,孔子是我國最早提倡音樂教育和實施“美育”的人。
一、孔子對音樂的學習和欣賞
孔子在訪問衛國時,遇到舊友師襄。師襄是著名琴師,于是,孔子便向他學琴。《史記·孔子世家》詳細記載了“孔子學鼓琴于師襄”的過程和情形: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這段關于孔子“學鼓琴”的認真態度和學習進度的記載,在《韓詩外傳》卷五、《淮南子·主術訓》、《孔子家語·辨樂篇》等典籍上所載皆同。
這段記載中的“曲”與“數”,是音樂技術上的總題,而“志”是形成一個樂章的精神,“人”是呈現某一精神的人格主體。孔子對音樂的學習,是要由技術而深入于技術后面的精神,更進而要把握到此精神具有者的具體人格,這正可以看出一個偉大藝術家的藝術活動的全過程。對樂章后面的人格的把握,即是孔子自己人格向音樂中的沉浸、融合。
《論語·憲問》記載說:“子擊磬于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此一荷蕢的人,是從孔子的磬聲中,領會到孔子“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論語·微子》)的悲愿。由此可知,當孔子擊磬時,他的人格是與磬聲融為一體的。
《論語·述而》記載說,孔子在齊國聽到了韶樂(舜帝的音樂),竟“三月不知肉味”,說:“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論語·泰伯》記載有他對太師摯演奏的評論:“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史記·孔子世家》載有孔子被困于陳蔡之野的故事,說孔子在沒有什么吃的,大家的意志都很薄弱的困難情況下,反而“講誦弦歌而不衰”。
“弦歌”是孔子音樂活動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論語·述而》說:“子于是日哭,則不歌。”由此可知,孔子除非吊喪哭泣之日不唱歌外,其他日子都會唱歌的。孔子認為,音樂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禮記·曲禮》記載說:“士無故不撤琴瑟。”從《論語》中可以看出,孔子經常唱歌。《史記·孔子世家》說他“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后和之。”孔子喜愛音樂,不僅僅會欣賞,而且會演奏和吟唱。孔子“弦歌”的主要內容,即是詩,詩在當時是與樂不分的。孔子的詩教,亦即孔子的樂教。《史記·孔子世家》引《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而稍加以變通,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三千弟子。由此直至戰國末,《詩》、《書》、《禮》、《樂》成為公認的儒家經典教材。
可以說,孔子是終身與音樂相伴的。《禮記·檀弓》說孔子直到臨死前七天,還流著淚對子貢唱了一首歌:“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他是在“弦歌”中快樂去世的。
二、孔子對音樂文獻的整理
孔子不僅學習和欣賞音樂,而且還對音樂做過重要的整理工作。
《論語·子罕》記載孔了自己說他“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即是說,孔子從衛國回到魯國后,才把音樂的篇章整理出來,這使詩與樂,得到了它原有的配合、統一,使雅歸雅,頌歸頌,各有了適當的位置。
所謂“雅”、“頌”,一方面是《詩經》內容分類的名稱,一方面也是樂曲分類的名稱。孔子對《詩經》的“雅”、“頌”分類,至今非常清楚;而關于樂曲的分類,因為古樂早已失傳,所以孔子的“樂正雅頌”究竟是正其篇章還是正其樂曲?甚或是篇章、樂曲都正呢?雖然《史記·孔子世家》和《漢書·禮樂志》都認為主要是正其篇章,就是調整《詩經》篇章的次序,但是依據還不充分;如果考慮到孔子本人在音樂方面是有專長的,那么孔子“樂正雅頌”就未必然只正篇章而不正樂曲。
《史記·孔子世家》記載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關于孔子對音樂文獻的整理,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多處記載了孔子在這一方面的功績。如:
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春秋末期,社會處于大變革時期,“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周游列國14年沒能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在晚年轉向古籍整理,即通過整理文獻典籍來傳道施教,把以“仁”為核心,以“禮”、“樂”為形式的精神體現在文獻中。在這種指導思想下,孔子將“《詩》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者,編成了《詩經》三百零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所以,經孔子整理過的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無不體現著孔子的禮樂思想。
三、孔子對音樂教育作用的認識
孔子對音樂的教化作用非常重視。
《論語·先進》記載說:“子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認為,先學習禮樂而后做官的是未曾有過爵祿的一般人,先有了官位而后學習禮樂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如果要選用人才,應該選用學習禮樂的人。
《論語·子路》中也提到孔子說:“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孔子認為,工作搞不好,國家的禮樂制度也就舉辦不起來,刑罰也就不會得當;刑罰不得當,老百姓就會惶惶不安而手足無措。所以,孔子對“樂”很重視,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對“樂”進行研究。
孔子和當時的樂人交往很廣很深。這由《論語·八佾》“子語魯太師樂,曰”一章,及《論語·衛靈公》“師冕見,及階,子曰”一章,可以得到證明。《論語·微子》記載“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一章,當是孔子對魯國那七位樂人的風流云散,發出的深重的嘆息,所以他的學生才這樣把它鄭重地記下來。《論語·陽貨》還說:
子之武城,聞弦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爾。”
孔子的學生子游當了武城的縣長,孔子來到這里,聽見“弦歌之聲”(即是以樂為中心進行教育)而特別高興。此處的“君子”、“小人”,是就社會上的地位來區分的。這一段話表達出三種意思:一是弦歌之聲即是“學道”;二是弦歌之聲下及于“小人”,即是下及于一般的百姓;三是弦歌之聲可以達到合理的政治要求。這是孔子看到他所傳承的古代政治理想,在武城這個小地方加以實驗了,當然很高興。
《論語·衛靈公》中有孔子答“顏淵問為邦”一章,孔子特舉出“樂則韶舞”,并將“放鄭聲”與“遠佞人”并重,這也可以反映出樂在孔門的政治理想中的重要性。
《論語·八佾》記載孔子評價“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在這里,孔子為音樂定下了審美標準,認為《韶》這種樂舞,藝術形式美極了,內容又好;而《武》這種樂舞,藝術形式很美但內容稍遜。使人驚嘆的是2500年前的孔子對音樂價值的認定幾乎跟當代完全一樣,一是藝術標準,一是內容標準。他贊賞、推崇藝術上完美,內容又好的音樂;但對于內容無害而藝術上很美的音樂也予以肯定。
《樂》本無經,而在于人的創造。《論語·八佾》記有孔子說:“人而不仁,如樂何?”即是說,孔子認為,如果一個人為人不仁,那么他所演奏的音樂也將不會令人愉悅。孔子進而還提出人的品質與音樂的內在聯系,說,假如一個人沒有仁德,又怎能很好地把握音樂呢?樂在于創造,是建立在《詩》的感性和《禮》的理性基礎之上的升華,是二者相互融合于人的產物。賢達之人所奏之樂,就像《詩經》開篇的《關雎》一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以樂是人性的是最好的體現。
孔子精通傳統音樂,對音樂的教化作用有一系列的理論。在《禮記·樂記》、《孝經·廣要道》、《史記·樂書》等典籍中,均載有孔子的名言:“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孔子的觀點就是要在人民中普及有品味的音樂,潛移默化,提高人們的修養。《論語·陽貨》記載孔子之語:“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孔子的意思是,音樂不只是簡單地用鐘鼓等樂器發出聲音,它還具有陶冶人的情操的作用。根據孔子的立場,音樂的本質是和諧與歡樂。任何音樂,只要能夠體現這種本質而不過度,那就是好的音樂,就可以為“仁”服務,配合“禮”達到教化的目的,和“詩”、“禮”一樣起到修養的作用。
作者單位:四川音樂學院聲樂一系(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