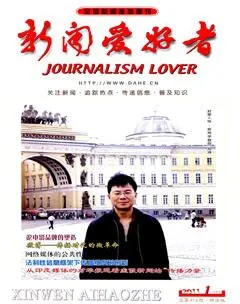鄉情的執
摘要:作為土家族作家,陳川的創作不僅立足于民族的土壤,描繪真實的土家風情風貌;更以一個思考者的身份,關注土家人的生存處境,審視土家人的生命形態;而且,小說敘事話語新鮮獨特,富有渝東南地域特色。
關鍵詞:地域風貌 土家風情 生存境遇 生命思考 敘事話語
地域風貌、文化風情的書寫
對地域與文化風情風貌的傾力傾情書寫是陳川小說的一個亮點。陳川深愛著他腳下的這片熱土,這塊地處黑山(武陵山脈)綠水(鳥江)間的渝東南土地是他魂牽夢縈的地方,他愿意也有意在自己的作品中糅合、呈現這一特定地域的地物特征、風貌人情、風土民習。
地域風貌的書寫。作為土家族作家,陳川筆下的渝東南地區也呈現出獨特的地域魅力,即一種神秘、鮮活而又粗獷剛烈的地域風貌。
渝東南地處中國的第二梯帶,云貴高原的邊緣,這里依山傍水,這里的人們靠山吃水。因此,山和水便構成了陳川作品地域風貌的主打元素與魂靈。他淋漓盡致地描繪出了山的神秘幽深:“一條趕場大路蜿蜒在大山之中,時而在山脊,時而在深谷。到處是幽深的密林,遮天蔽日,古藤纏繞”(《塑造》);山的雄壯崇高:“大山連綿,莽莽蒼蒼,像是從天邊涌過的波濤……大山沉默著……而博大的胸懷,無窮的力量和蓬勃的生機不正是蘊藏在這無邊的寂靜中么?此刻,他在靈魂深處理解了大山的這種崇高的靜穆,真正欣賞到大山的壯美”(《塑造》);山的孤獨肅寂:“這是一片廣袤、沉寂的土地……芭茅草、灌木叢,還有一籠籠野金銀花藤蔓,布置出一個蒼黃、蕪雜的世界,讓人感到一種沉悶,一種荒涼,一陣孤獨”(《那里,在遠方》)。在陳川筆下,我們不僅能體驗到山的迷魅魄力,也可領略到水的萬種風情:“每當夕陽落到山埡,瑰麗的晚霞把她的全部色彩傾倒在阿蓬江河面,或桃紅,或金黃,或紫藍。閃爍變幻,像一個多情的女人,眨著媚眼,逗引人們投進她的懷抱。”(《汪=新傳》)
在陳川的小說中,千姿百態的山和水無疑成為土家風情的承載者,從這片土家人生活生長的山水里,我們能觸摸到土家人生存環境的艱難與生活的艱辛。
土家風情的凸顯。作為土家族的一員。作者深愛著自己的家鄉與民族,熟悉本民族的文化。具有自覺的民族承擔意識。因而,偏僻、封閉的土家山寨構成了陳川大多數小說的敘事場景:“大山里有許許多多的溝,有一條叫灰溪溝”(《汪二》);“高巖是一個鄉場,背抵大山,一壁白晃晃的絕巖遙遙在望。臨面有一條小溪,水很淺……獨條街,百十步,全用光溜溜的青石板鋪就……兩排房屋連椽接瓦”(《塑造》);“水寨聳立在眼前。兩面萬仞絕壁,夾一潭凈水,一片死寂”(《夢魘》)。茶溪、椒溪、老街、青岡林、罩子蓋、苦竹蓋、諾扭灣、濯水鎮,這是一個個散發著馥郁土家山鄉氣息的小說故事衍生地。即使是作者筆下的馬喇城、石城也并非真正的城市,而是小小的邊城。在這一個個寨子中,土民生活在一座座“矮爬爬的,不少屋頂蓋著生了青苔的杉樹皮”的搖搖欲墜的吊腳樓里。這是土家民族典型的居住民俗。陳川更讓讀者領略到粗獷質樸的土家日常飲食民俗:喝的是香噴噴的油茶湯(油茶湯解渴提神);吃的是包谷粉子飯、包谷洋芋飯:下酒下飯的菜是蒸臘肉,帶有膻味的麂子肉,一塊塊肉都有巴掌大,膘肥流油,實在解饞。喝下半碗自己釀造的“包谷燒”,便昏昏欲睡了。
作為一個生活在高山惡水間的民族,土家族有自己特有的漁獵文化與習俗。《汪二》、《那里,在遠方》、《夢魘》將富有土家特色的“攆仗”(狩獵)、“趕鬧”(捉魚)這樣的集體漁獵活動進行了鮮活的再現。“圍山攆仗。鬧魚取蝦,見者有份”,這是土家人的規矩,是土家族的民俗民習。
土家族人長年生活在閉塞的山區,生活貧困,勞動繁重,娛樂方式單一。在這種生活狀態下,土家族人會用獨特的方式來放松精神,娛樂身心,除了他們特有的“擺手舞”、“茅古斯”、“撒爾嗬”、“薅草鑼鼓”等舞蹈形式外,豐富多彩的山歌,就成了他們極為重要的娛樂方式。山歌誕生在勞動中,淋漓酣暢地表現了土家人樂觀、睿智、幽默的民族性格。通過山歌來表現人物的性格特征,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是陳川小說的一個特色。“唱歌莫唱扯謊歌,風吹石頭滾上坡,冬水田里撿菌子,青岡林里鯉魚梭”,這是《那里,在遠方》中山野村夫勞動時唱的《扯謊歌》,風格清新幽默,體現出土家人特有的樂觀、風趣和詼諧的民族氣質。“涼風繞天要晴,莊稼只望雨來淋,莊稼只望雨來長,留郎只望妹才行”,這是《塑造》中火辣辣的姑娘小伙子傳情達意的對唱山歌;“我想你苦來想你多,想起你來睡不著,想著了又夢見你在懷,醒來才曉得是空場合”,這是《汪二》中主人公的風流調笑情歌。在土家族山歌中。情歌數量最多且最有特色。可以說是“十對男女九對歌,十首山歌九情歌”。渝東南地區的土家族情歌,其意真摯感人,情調質樸優美。是土家族男女相識、相知、相愛的媒介,既體現出土家族人的多情、誠摯和忠厚,又體現出土家族人的機智、俏皮與樂觀,使土家族青年男女的愛情附上了濃厚的浪漫色彩。在陳川的小說中,山歌歌詞簡潔,旋律簡單,雖短短幾行卻可以給小說增添無限的韻味空間,而且破譯出了土家族人特有的歌唱習俗與文化內涵。
此外,陳川小說中還有對哭嫁、交親等土家婚慶習俗(《心事》、《太陽下》),巫婆驅鬼的巫卜民俗,人死后的喪葬民俗(《塑造》)的征用與呈現。總之。作為一個出生成長于武陵山區的土家族作家,陳川將渝東南土家民族特有的民俗文化、民族風情有意識地糅進自己的小說,并對之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演繹與恰如其分的彰顯,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了濃郁的地域民族特色。
對生存境遇的呈現與對生命的思考
作為土家人民的兒子。陳川有著深沉的民族情懷。熟悉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心理性格和民族文化傳統,因此其創作抒寫人情,思索人生,關注人的命運。肯定人的尊嚴和價值;卻又根植于民族的土壤,表現淳樸的民情習俗,關注民族的生存與未來,創作上有著鮮明的民族印記。
文學源于生活,陳川的創作扎根于故鄉的那片土地,描寫熟悉的人和事。作品浸蘊著濃郁的民族文化氣息。他把創作的視野聚焦于人,表現他們的人生軌跡,思考他們的生存本真。
《那里,在遠方》講述了新上任的縣委書記劉仁和到全縣最偏僻、最貧窮的罩子蓋“微服私訪”,了解民情。山里人淳樸、善良、熱情、厚道、待人誠懇,但山里的環境卻異常艱苦:“這片土地確實瘠薄。終年霧沉沉的,日照太少,所以有罩子蓋之名。一入冬經常雪凌封山,寒冷刺骨,人們只能蜷在火鋪上度日。出產也很少,只有包谷、洋芋……交通也極其不便。距鄉政府有四五十里,而且懸崖阻路,危險難行;買一頭牛犢,要背上山,老死了、累死了,就剁成塊,背下山去,換回一點鹽巴。”面對如此惡劣的環境,罩子蓋的人并沒有退縮,靠這一片土地頑強地繁衍生息。受人尊敬愛戴的老支書,因久病而無錢治療,可至死也不離開這片土地。在故事中,作者還穿插了龔老大與寡婦銀花深沉、堅定、剛健的愛情。這篇小說給讀者所呈現的不僅僅是山寨沉重嚴峻的生存環境及山民生活的貧困,龔老大與銀花大山性格般的愛戀,作者更想挖掘的是山民們堅忍不屈的生命態度,是他們對土地的摯愛,是他們力求生命繁衍、壯大民族群體的原始生命力及力求改變山村落后面貌的生命祈求。整個作品呈現的是一條土家山民堅忍不拔、樂死達觀的生命軌跡。
但我們又隱隱感覺到,作者要反映的不僅僅如此。正如文章中所說:“這也許就是山里人的性格吧,是固執愚昧呢?還是自尊自重?也許二者兼而有之。但這于事無補,得想辦法慢慢開導他們,他想。”蓋上的年輕人寧愿不結婚當“單條子”,也不下山去當上門女婿;老支書寧愿死在這片土地上,也不肯到山外的醫院去看病等。對山民們思想的封閉、落后與頑固,對穩固如山的民族性格惰性,陳川有了隱憂。
短篇《夢魘》更是一篇現代土家的“寓言體小說”。所謂“寓言體小說”就是:“小說文本雖然描寫現實生活,由于作者理性觀念的介入,賦予文本以寓言性,因此故事并不是它表面所顯現的那樣,其真正的意義是需要解釋的。這種小說的敘事模式是寓言話語,它以隱藏性的指涉方式言說人類生存的各種信息,體現人類整體生存狀態和集體深層心理。文本與外在世界豐富深刻的對應關系傳達出隱喻的效果,寓言話語的模糊性、多重性使文本的理性結構呈現為一種深度空間,為讀者開啟了多個透視文本中心的解讀視角。”《夢魘》講述了一輩子謹慎規矩木訥、年過六旬的老焉,在載送陌生人去水寨的水路上第一次看見了槍,也第一次打了槍,但這個足以讓老焉一輩子值得自豪的奇遇,卻讓他和家人遭到了寨子里其他人的譏諷和嘲笑:“人家三公走南闖北見多識廣也沒放過盒子炮呢,他老焉不是做夢么越活越糊涂噦,哈哈嘿嘿嘻嘻嗬嗬……”在德高望重的三公的勸說下,老焉終于相信打槍的奇遇不過是自己做的一場荒唐的夢,并從此一病不起。《夢魘》的旨意豐富而深刻:不被人理解、孤獨無援的老焉,嘲笑、諷刺老焉的寨子山民,心地善良卻無法讓人同情還帶有悲哀的三公,小說觸及的是土家民族超穩定的社會心理結構模式中沉淀的集體深層文化心理的積習和惰性,反思的是土家人生命形態上的心理萎頓和生命性格中的偏失贏弱。
陳川的目的是顯明的,他的小說無時無刻不在思考土家人的生存境遇,審視土家人的生命形態;同時,站在救贖的立場,揭示土家人生存的孤獨和荒誕、生存的尷尬和局促,揭示土家人在現代生存環境中生命的掙扎、扭曲甚至異化。反映生活、關注生存、思考生命使陳川的小說散發出較為持久的藝術魅力!
冒著地氣的敘事話語
作為渝東南土家民族文學的一個代表,陳川的創作還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語言——一種誕生于這片土地上,有著濃郁地域色彩的敘事話語。這種語言既有著高原峽谷文化的怪異與奇崛,也有著與山相依的水文化的鮮活與靈泛;既有著與自然山水相接的靈氣與飄逸,也有著民間煙火的平實與粗俗。“喂,為哪樣喲?恁大的太陽,來洗澡吧,好涼快,好安逸喲”(《汪二》),“你默嘛,蓋上又窮又苦,有哪點留戀頭”(《那里,在遠方》),“你下細默默,我哪里說走展了”(《心事》)……這是貼切形象的地方口語;“臉愁得變成核桃殼兒”(《酒瓶》),“包谷個子如鹽荷包大小”(《那里,在遠方》),“就你這鼎罐不醒事”,“喉嚨像遭包谷芯堵住了”(《心事》),“太陽像被一種魔力送上天空的簸箕”(《太陽下》)……這是地道活氣的鮮亮比喻;“正該”、“周遭”、“扯謊”、“包瞞”、“攆仗”、“趕鬧”、“逛逛神”、“做活路”、“毛腳桿”、“老蜷了”、“挨攏去”、“花眉花眼”、“二不掛五”、“天才麻麻亮”……這是生動形象而又貼切的地方口語。這些語言雖然不及書面語正規、嚴肅甚至還有點粗俗野蠻,但正是在這一類話語中,我們讀出了土家人民的語言智慧與民族本性。《民族文學》老編輯白崇人贊譽陳川“把根深扎在自己民族和地區的生活土地上”,從語言方面來說,陳川確實是扎根于民族生活的沃土,吸收、提煉本民族的日常生活口語。從而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小說敘事話語。雖難免有粗糙、生硬之處,但他的這種探索精神是難能可貴的,是應當值得肯定、鼓勵的。
作為少數民族作家,陳川可謂是一位認真的作者,其小說散發著濃郁的地域和民族色彩。他以獨特的民族歷史、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傳統做根基。表現出對民俗民習的關心和熱愛,對民族民性、人性的關懷和思索,對民族話語的開掘和調用。他的作品值得我們去關注!(本文為重慶市教委科研項目“烏江流域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09SK004)
注釋:
1、丁世忠:《重慶土家族民俗文化概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頁。
2、宋永祥:《關注生存
沉思生命——論土家族作家陳川的小說創作》,《西南民族學院學報》,2000(8),第51頁。
3、陳川:《夢魘·序》,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2頁。
(作者單位:長江師范學院文學與新聞學院)
編校: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