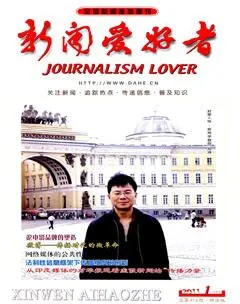上古到商周中國古琴文化功能的演變
古琴是中華民族最早的彈撥樂器,是中國傳統文化之瑰寶。古琴藝術體現著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體現著豐富的美學思想。古往今來,在文人墨客的心中,“詩、書、禮、易”為安身立命之本,“琴、棋、書、畫”乃修身養性之源。而從上古到商周時期,古琴的審美價值取向卻與現代不同,本文從文化歷史背景更替的角度略論這一時期古琴文化功能和審美角度的演變。
琴之本初的文化目的是追求善與美的統一與和諧
古琴又稱“七弦琴”,是中國最古老的弦樂器之一。有關古琴的記載,最早見于《詩經》、《尚書》,《左傳》等文獻,《尚書》載:“舜彈五弦之琴,歌南國之詩。而天下治。”在商代甲骨文中,已有“樂”字出現,作“槳”形,像絲弦架在木上,這說明,早在夏商時代或更早的時期,我國已有琴瑟之類的弦樂器了。古琴的出現和我國上古文明聯系緊密。“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者居營窟,夏則居槽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十分有限,面對許多自身無法抗拒和無法解釋的自然現象,只能借助和祈求上天、神靈的保佑。黃帝時,“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擷頂“依鬼神以制之”、“潔誠以祭祀”,帝譽“明鬼神而敬事之”,就這樣逐步形成了對山川等自然物崇奉的多神論觀念。而這一時期,人們在射殺獵物時,受到弓弦彈射時發出悅耳聲音的啟發,遂將其改制成了早期的琴瑟之類的弦樂器,用來悅神、祈福、求雨。有書記載:“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蓄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堯使無勾作琴五弦”,可見此時琴瑟等弦樂器已成為祈神、娛神、求雨的樂器了。在古琴起源傳說中,蔡邕的《琴操·序首》說:“昔伏羲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桓譚《新論·琴道》說:“琴,神農造也,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昔神農氏繼宓羲而王天下,上觀法于天,下取法于地,于是始削桐為琴,練絲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八音廣博,琴德最優,古者圣賢玩琴以養心。”這些傳說無不體現出古琴原初創制的根本目的,正是“神人”教化天下,追求善與美的統一與和諧。
夏商時期琴扮演著巫樂祭祀法器的角色
夏商時期,是我國進入奴隸制的時期,人類雖然進入了階級社會,但仍然繼承了上古文明的天命鬼神觀,整個社會仍處在神的威力之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在這樣濃郁的迷信神權的意識中,夏朝、商朝產生并發展了一種可稱為巫術的文化形態,它可以“以舞降神”,預決吉兇,占星祈雨,醫病消災,就這樣,巫術成為神與人交流的工具。而這時的樂器則是用“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這可能是古人想用琴、瑟這優美的聲音娛神,最終實現風調雨順的好年景。“戛擊鳴球,搏柑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下管蜚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于予擊石扮石,百獸率舞。”這些雖然指的是一些化裝表演,其中也不乏娛神并乞求神靈保佑的意思。可見,琴最初只是祭祀、祈福時使用的法器。從夏商樂舞的發展也可以窺視出琴在當時除了充當巫樂法器角色之外還充當歌頌君主帝王的道具,《大夏》是歌頌大禹治水的,《大武》是歌頌武王伐紂的,樂舞的內容有早先宗教儀式表演到對原始圖騰的崇拜,漸由“敬天”轉為“敬人”,著重對帝王文德武功的贊頌,由此可見其音樂文化的轉變,除了漸向“雅樂”的表演模式靠近外,商代以宗教巫術為主的音樂表現方式,也轉向周代的封建禮教音樂形式。
周代琴的文化功能由“崇神”轉變為“尊禮”
周朝是我國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化時期,從“殷人尊神,而周人尊禮”中我們可以看出殷、周在處理神人關系問題上的不同,殷人尊神,說明殷人只是盲目地把鬼神看做統治人們的神秘力量,認為天命不可違;而周人尊禮,說明周人開始具有某種理性自覺,認為天命可違,強調盡人事。周人以尊禮否定了殷人的尊神,實際上是把人們虛無縹緲的思想從天空中拉回到現實中來。王國維認為,夏、商兩代的政治制度基本相同,而“周人制度”卻“大異于商”。周朝除繼承夏商的天命鬼神觀外,同時改革了“殷禮配天,多歷年所”。所以,周禮改革了上古、殷禮用宗教祭祀的儀式,它的“制禮作樂”是采用宗法封建等級社會的典章制度和人們的行為規范,用禮樂制度規范社會生活、統治社會的各個階層,使周禮覆蓋了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無形之中禮教的內容內置于人們的心中。成為其生命中的一部分。“士無故不徹琴瑟”,“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而非滔心也”。演奏古琴時,還須“先除其浮暴粗析之氣,得其和平淡靜之性”、“焚香靜室”、“衣冠整齊”、“或鶴髦、或深衣,要知古人之象表”;鼓琴時,“心不外馳,氣血和平”,這都說明禮樂制度的禮把人嚴格地區分了等級。而琴就是這一等級的體現。
為了避免“威儀三千”的禮造成下者對上者的抵觸甚至“離心離德”,便產生了具有“和合”作用的文化因素——樂,因為樂“天生”具有調和社會各階層關系的能力——“樂從和”,“聲以和樂,律以平聲”,“樂者,天地之和也”。就這樣,具有神秘色彩的“琴”就理所當然地做了樂的代言人,因琴可“御于邪,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琴,禁也,禁之于邪,偶以正人心”,“養君中和之正性,禁而忿欲之邪心”,而且琴“足以通萬物而考治亂也”,“可以感格幽冥,充被萬物,況于人乎”。就這樣用樂教引導民眾,使人心所生的感情從一開始就受到統治者的控制和掌握,又把禮教的內容內置于心中,成為其生命中的一部分,是變被動的說教為主動接受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因此,自上古以來,樂教就受到相當的重視,而且,樂也成為時代精神的象征。自此禮樂文化為儒學的產生提供了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其實,儒學就是宗教封建等級制度及其文化。
春秋戰國“士”的文化因素在琴上的體現
本來,這種帶有原始巫文化色彩的樂文化意識,是分載于各種不同樂器上的,特別是祭祀用的鐘鼓類樂器,后來鐘鼓之類的祭祀樂器只是作為普通樂器一直被保留下來,并沒有賦予什么文化內涵,而在眾多的古樂之中,琴卻獨樹一幟地成為中國代表性文化之一,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文化的主要載體不是帝王、神,而是士人。士,原指宗法封建等級制度社會的一個特定等級——“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家”。看來士的地位在貴族之下,庶人之上,是最低等的貴族。春秋戰國時期的士階層是在生產力提高、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分工、不耕而食成為可能,以及禮崩樂壞、擺脫了神力威懾的恐懼,為尋求平靜生活,憑借心志和口舌被有霸力的國君和侯王招攬中產生的,它不是一種等級身份,是社會動蕩下從各等級中游離出來的人組成的具有獨立人格、獨立意志、自己的價值標準,能夠自由思想的、社會中最活躍的階層。他們宣揚“天道遠,人道邇”、“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主張,從巫師手中接過特權,剔除了巫師們挾持的原始神秘的文化內容。與巫師宣揚的神本不同,形成了以民為本、以人為本的熱愛生活、熱愛人生的思想。春秋戰國士的興起,即是人本文化發展的結果。士人宴樂時當然要講究鐘鼓的排場,鐘鼓能體現天音,但畢竟還需他人的幫助,當他獨處時,體悟個性,鼓琴不能不說是最簡便也最富個性化的行為了。琴音可隨彈奏者的喜好而變化。此時,正值士人有取樂以娛的風氣,與封建統治者的重樂不同,士大夫作樂,更多地是要表達內心的情感。彈奏者通過彈奏,可以寂然同于大通,處于忘我的狀態,感悟出天地運化的大道或人生的喜怒悲歡。伯牙的高山流水,其意已不在琴弦和樂音,而在于那些琴音交織形成的“高山流水”的悠然興致。陶淵明蓄無弦琴,既不能彈奏,也不能聆聽,只是想通過“撫”琴的動作,達到調節心性的目的。為了修養心性,琴樂趨靜求緩,少有急弦繁音,于悠揚和諧之中,達到精神上與自然的相通相融。
總之,琴從法器轉化為樂器,從祈福、求平安轉化為表達個人情懷的“發乎情止乎禮”的精神境界,正是由于巫師是從居于社會的中堅力量,曾是社會中最有文化的,對中國的天文、音樂、歷算、舞蹈、詩歌、醫藥、史學、哲學的發展都產生過深遠影響的階層,轉變為宗法封建等級制度社會的一個特定等級——士階層的原因。由此可見,我國古代文化是從以巫師為主要載體的神本文化向以士為主要載體的人本文化的轉化,正是這種文化意識的轉化帶動了古琴審美功能的轉型。儒家視彈琴為人格修養的途徑,把琴德與君子之德聯系起來,目的是要君子通過彈琴禁邪念,收放心,守禮法,使人成為“克己復禮”的君子。他們愛琴、操琴,沒有任何外在的功利目的,只是為了培養自己的節操,陶冶自己的性情,增加涵養。他們彈琴、寫琴、贊琴。認為世上的萬物皆有盛衰,只有音樂永恒不變。正是他們,使古琴藝術得到極大豐富,不斷把它推向峰巔,最終賦予它中國古典藝術的靈魂,使它成為古典藝術的杰出代表。
(作者單位:洛陽師范學院音樂學院)
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