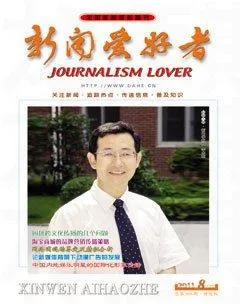革命根據地時期的新聞法制及其當代意蘊
自井岡山根據地創建以后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各根據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不斷加強包括新聞法制在內的政權建設。本文擬對這段時間的新聞法制建設作一梳理,以供共和國新聞法制建設參考啟示。
革命根據地不同時期的新聞法制
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就在黨的“一大”通過的決議中明確提出出版物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必須貫徹黨的路線。此后,黨的有關文件除繼續強調該原則外,還把爭取新聞自由的斗爭視為民主革命的重要內容。進入土地革命以后,中國共產黨通過領導根據地政權將其不斷上升為新聞法制。
土地革命時期的新聞法制。自“八七”會議至1933年下半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武裝開辟出10多塊革命根據地,建立了工農民主政權,出臺了旨在加強新聞工作的新聞法制。該時期的新聞法制主要體現在憲法性文件和懲治反革命條例中,專門的新聞法制并沒有出現。
新聞自由在蘇維埃中央政權和地方政權的憲法性文件中都有體現。在中央,由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修正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10條規定了中華蘇維埃政權的目的就是保障工農勞苦民眾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在地方,地方蘇維埃政權也規定了新聞自由,比如《江蘇省蘇維埃臨時政綱》第8條規定:“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住居、罷工之絕對自由。”
新聞法制還體現在懲治反革命條例中。1934年4月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公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2條規定反革命行為是:“一切圖謀推翻或破壞蘇維埃政府及工農民主革命所得到的權利,意圖保持或恢復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該條例列舉了27項反革命行為,其中第10條、第12條、第13條與新聞傳播活動有關。
抗日戰爭時期的新聞法制。抗日戰爭爆發后,各抗日根據地依據《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之“全國人民除漢奸外,皆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武裝抗敵之自由”規定和國民政府的有關法令,除在懲治漢奸條例中規定新聞法制內容外,都在出臺的有關施政綱領或專門人權條例中規定了新聞自由的內容。
施政綱領中規定新聞自由的內容具體情況是:《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1939年4月)第8條、《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1941年5月)第6條、《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施政綱領》(1941年9月)第3條(丁)、《對于鞏固和建設晉西北的施政綱領》(1942年10月)第4條、《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1943年1月)第6條、《山東省戰時施政綱領》(1944年2月)第3條(丙)等。
在專門人權條例中規定新聞自由的內容具體情況是:《山東省人權保障條例》(1940年11月)第4條第三款、《陜甘寧邊區保障人權財權條例》(1942年2月)第2條、《晉西北保障人權條例》(1942年11月)第8條、《修正淮海區人權保障條例》第4條規定等。有的人權條例還以專章形式規定了新聞自由權,如《冀魯豫邊區保障人民權利暫行條例》(1941年11月)第三章。有的雖沒有明確規定人民言論、出版自由權利的條款,但卻有保障權利實現的內容,如《渤海區人權保障條例執行規則》(1943年2月)第2條即是例證。
解放戰爭時期的新聞法制。進入解放戰爭時期以后,各解放區繼續在憲法性文件中規定了新聞法制內容。如《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施政要端》(1945年9月)第2條、《蘇皖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施政綱領》(1945年12月)第1條、《東北各省市(特別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綱領》(1946年8月)第7條、《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1947年4月)第6條、《華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針》(1948年8月)“政治方面”第4條,等等。
此外,解放區政權還頒布了管理新聞事業的專門法規,如《北平市報紙、雜志、通訊社登記暫行辦法》(1949年2月)和《華北人民政府新聞發布辦法》(1949年6月)。它們的頒布,標志著黨領導的根據地政權新聞法制的進步。
革命根據地時期新聞法制的主要特點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政權不同于中國歷史上既有的任何政權類型。它創制的新聞法制也不同于以往政權出臺的新聞法制。具體來說,主要表現在:
新聞自由權利主體范圍的確定性。自晚清創制新聞法制以來,南京臨時政府、袁世凱政府及北洋軍閥政府、南京國民政府不但在其憲法和憲法性文件中規定了享有新聞自由權利的主體為人民,而且還在其出版法、報紙條例中頻繁出現“人民”一詞。但綜觀前述政府的新聞法制,均未對“人民”作出具體解釋,沒有明確說明“人民”具體指社會上的哪些人,使“人民”成為一個不確定的詞語。正因為新聞自由權利主體“人民”的不確定,使得只有以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為基礎的政府才能對新聞事業實行專制和獨裁。
革命根據地時期新聞法制中雖也規定了新聞自由權利的主體為人民,但與前述政權所說的“人民”有著本質不同。這里所說的“人民”內容是確定的,而且隨著民主革命任務的變化而有所變化。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人民”的范圍就是工農勞苦民眾,而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一切剝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不屬于“人民”的范圍。進入抗日戰爭時期以后,抗日成為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人民”的范圍也有所變化。所有贊成并參加抗日的、反對投降賣國的人都屬于“人民”的范圍,而投降賣國者都不屬于“人民”的范圍。解放戰爭時期,排除在“人民”之外的僅限于大地主、大官僚、大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反動派。“人民”外延的不斷變化,決定著新聞自由權利主體范圍的不同。
新聞自由權利切實實現的保障性。盡管袁世凱政府及其后的北洋軍閥政府、南京國民政府都在根本大法中規定人民享有新聞自由權利,以標榜所謂的民主。但又通過具體法規、條令、命令、辦法等加以限制,把民眾的言論出版自由剝奪得一干二凈。正如毛澤東指出:“背叛孫先生的不肖子孫,不是喚起民眾,而是壓迫民眾,將民眾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權利剝奪得干干凈凈”。①與“背叛孫先生的不肖子孫”不同,革命根據地的新聞法制則從法律上和物質上確保了新聞自由權利的實現。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根據地時期的新聞法制就有了保障新聞自由權實現的規定。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10條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民主,主張工人農民的民主,打破地主資產階級經濟的和政治的權利,以除去反動社會束縛勞動者和農民自由的一切障礙,并用群眾政權的力量,取得印刷機關(報館、印刷所等)、開會場所及一切必要的設備,給予工農勞苦民眾,以保障他們取得這些自由的物質基礎;同時反革命的一切宣傳和活動,一切剝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蘇維埃政權下都絕對禁止。”此后,抗日根據地、解放區的民主政權都繼受了該原則,切實使新聞自由權利在根據地得到實現,“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是徹底地實現了。”②
新聞法制創立方式的特殊性。與晚清以來的新聞立法方式相比,根據地時期創制新聞法制的方式較為特殊。這種特殊主要表現在:
一是立法依據的特殊性。綜觀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的新聞立法依據均為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和政策。而晚清以來的其他新聞立法均在形式上以約法或憲法為依據。二是立法主體的特殊性。在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和政策指導下,各革命根據地結合實際制定適用于本根據地的新聞立法,有利于體現地方特色。有的在政權組織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則以黨的組織名義進行。而晚清以來的其他新聞立法則由國家立法機關統一進行。三是黨的新聞政策的特殊性。黨的新聞政策不屬于新聞法制的范疇,但當時的新聞管理多依據黨的新聞政策。黨的新聞政策不但規范根據地的新聞事業,而且具有強制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起到法的作用。而其他政權的新聞立法則較為少見。
革命根據地時期新聞法制的現實意義
革命根據地時期的新聞法制已經成為歷史。以史為鑒,它還具有如下幾點現實意義。
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法制建設提供了歷史淵源。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過程中,新聞法制建設也不斷推進,內容涉及新聞事業的發展方向、公民的新聞權利、新聞事業的限制范圍、新聞事業的管理等內容。可以說,我國新聞活動已經有法可依,但從法治的眼光來審視,作為效力位階更高法律層面的《新聞法》、《出版法》等專門法尚未出臺。盡管新聞界多次呼吁制定專門的《新聞法》,“然而,《新聞法》等專門的新聞傳播法律至今仍處于呼吁和立法規劃階段,《新聞法》文稿至今還沒有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出版法》文稿分別于1990年和1993年兩次提交立法機構審議,但均未獲通過。”③
當然,健全新聞法制并非制定《新聞法》、《出版法》等專門法即告完成,它需要根據《憲法》第3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制定一系列相配套的法律法規,形成較為完善的新聞法律體系。這個過程是較為漫長的。它需要從多方面著手準備條件。基于革命根據地時期政權與共和國政權的傳承性,它的新聞法制可以直接為共和國新聞法制建設提供歷史淵源。
它為法學學術研究提供了有益啟示。在中國法學如何發展的問題上,專家學者提出了諸多不同的主張,并就此展開過激烈的論爭。鄧正來為此對“本土資源論”、“權利本位論”、“法條主義”、“法律文化論”等當代中國最具代表性的主張逐一進行了分析和批判。但對于“中國法律理想圖景”,他拒絕用一種更為明確的方式來解釋,而是用一句令人深思的話作了回答:“當我把你從狼口里拯救出來以后,請別逼著我把你又送到虎口里去。”④中國法學確實存在著諸多問題,但再多的雄辯與精彩的哲理思辨,都不能脫離社會實踐這個基礎。
革命根據地的新聞事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政權下的新聞事業,是共和國新聞事業實踐的前奏,是真實存在過的社會實踐。這一時期的新聞法制是新聞史、法制史共同研究的對象,具有交叉學科的特點。就研究狀況而言,新聞界已有陳建云的《中國當代新聞傳播法制史論》、馬光仁的《中國近代新聞法制史》等專題涉及該領域,而法學界整體來說則關注不夠。這就啟示我們,法學學術研究需要加強對專門領域實踐的關注,以使研究更加具有針對性。
它為正確理解政策與法律的關系提供了實證。近代以來,政黨這一新生事物力圖通過自己的政策來影響立法,從而實現其自身的特殊利益,同時它又強調在社會控制中實行法治,倡導法律至上。因此,如何理解政策與法律的關系一直是學界研究的熱點。
其實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政策與法律的關系在《中共中央關于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就已明確:“在人民的法律還不完備的情況下,司法機關的辦事原則應該是:有綱領、法律、命令、條例、決議規定者,從綱領、法律、命令、條例、決議之規定;無綱領、法律、命令、條例、決議規定者,從新民主主義的政策。”但自1957年以后,政策與法律的關系開始走上曲折發展的道路,“政策是靈魂,法律是工具”逐漸成為強勢理論。上世紀末我國確立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但如何正確理解政策與法律的關系依舊有待進一步擴大群眾基礎。革命根據地新聞法制的立法模式為我們理解政策與法律的關系提供了歷史實證。它啟示我們要正確理解政策與法律的關系,不能僅進行理論上的思辨,還要從歷史由來中理解它們的關系可以使我們理解現狀的合理性。(本文是河南工業大學博士基金項目的成果,項目編號2009BS005)
注 釋:
①②《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0頁。
③陳建云:《中國當代新聞傳播法制史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頁。
④鄧正來:《中國法學向何處去》(續),載《政法論壇》,2005(4)。
參考文獻:
1.本文引文內容未標明出處的,均引自韓延龍、常兆儒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第1~4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2.《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全三冊),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
3.馬光仁:《中國近代新聞法制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單位:河南工業大學)
編校:趙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