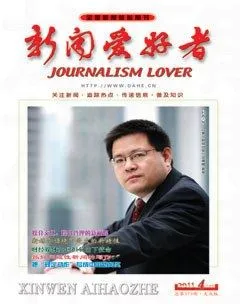淳美視域的天人和諧
自北宋始,評論王維詩歌審美價值最精當者,莫過于大文豪蘇軾,他在《書摩詰藍田煙雨圖》中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王維“詩中的畫”,是靜穆心靈里物我相親的“畫”,是淳美視域中天人和諧的“畫”。從自然美與藝術(shù)美高度統(tǒng)一的視角來看,在中國古代詩史上,王維的詩歌堪稱“淳美視域天人和諧”的極品,我們僅擷王維眾多詩歌中的一首——《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就可見一斑。
咀嚼品味王維的五言律詩《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眼前便呈現(xiàn)出一軸“淳美視域天人和諧”的秋晚山村水墨畫,耳畔則回旋著一首悅耳動聽的蟬鳴溪唱田園曲:
寒山轉(zhuǎn)蒼翠,秋水日潺湲。
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
渡頭余落日,墟里上孤煙。
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
秋天來臨,寒意漸濃,遠山抹上了蒼翠的濃妝,澄澈照影的澗水緩緩流淌。“我”輕扶竹杖斜倚在柴門之外,迎著徐徐秋風靜靜地聽著秋蟬在暮靄中低吟淺唱。黃昏垂下了金色的帷幕,秋風停歇了輕盈的腳步,舉目環(huán)望,四野幽靜;河渡盡頭,只剩下圓圓的落日;村莊深處,一縷炊煙裊裊升起直上碧霄。這時,又碰到好友裴迪喝醉了酒來到“我”面前,正乘酒興,擊節(jié)狂歌,吟詠著他的得意詩篇。
讀罷此詩,細細品味,筆者認為此詩的精華乃是表現(xiàn)了淳美視域中人與大自然的高度和諧。
所謂“淳美”,即厚重美好,樸實美麗。淳美的美學價值在于“樸中寓真,淳中見雅”;“視域”是指人們感受、理解審美對象的構(gòu)架或視野;“淳美視域”是指以淳美為審美范疇和平臺,感受、理解審美對象的思維構(gòu)架。所謂“和諧”,即如黑格爾所說,客觀事物“各因素之中的這些協(xié)調(diào)一致就是和諧”,“和諧之所以美,是由于它們的鮮明的差異和對立已經(jīng)消除掉了”。和諧的美學價值在于“異中求和,靜中寓動”。《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這首詩的淳厚和諧之美,主要表現(xiàn)為人與大自然外在的協(xié)調(diào)一致與內(nèi)在的和諧統(tǒng)一。
先談人與大自然的外在和諧。這種外在的和諧是人與自然景物“形態(tài)”之間的協(xié)調(diào)一致。本詩寫“寒山”,渲染其“色”的蒼翠,以凸顯人與景物的視域和諧;寫“落日”,突出其“形”的空靈,以凸顯人與景物的心域和諧。這是靜態(tài)意象的摹寫。寫“秋水”,描繪其“音”的潺湲流淌;寫秋蟬,摹狀其“聲”的淺吟低唱,以凸顯人與景物的聽域和諧;寫孤煙,展現(xiàn)其“態(tài)”的輕逸舒徐,以凸顯人與景物的視域和諧。這是動態(tài)意象的描繪。詩人從視覺和聽覺上寫這些意象,其動靜相映,形態(tài)相襯,聲色相生,不僅景物之間的“形”十分和諧,而且景物與人之間的“神”也十分和諧,因為抒情主人公“我”處在這些優(yōu)美的景物之中,面對蒼翠的寒山,欣賞潺湲的秋水,聆聽淺唱的蟬鳴,遙看渡頭的落日,沉醉墟里的孤煙,自身仿佛變成了大自然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完全融入了大自然的幽美景色之中,沉醉于人與自然景物形態(tài)相融的淳美境界。這時,審美主體已被審美客體同化,人的外在之形與自然的外在之形完全協(xié)調(diào)一致,二者達到了高度的和諧統(tǒng)一。
再看人與大自然的內(nèi)在和諧。人與大自然的和諧美,不僅表現(xiàn)為外在的和諧之“形”,更重要的是表現(xiàn)為內(nèi)在的和諧之“意”。這種“意”就是審美的主觀性。《紅樓夢》第四十八回寫黛玉與香菱論詩,談到了王維詩“渡頭余落日,墟里上孤煙”的妙處: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菱笑吟吟地送了書來,黛玉道:“可領(lǐng)略了些滋味沒有?”香菱笑道:“領(lǐng)略了些滋味,不知可是不是,說與你聽聽……‘渡頭余落日,墟里上孤煙’,這‘余’字和‘上’字,難為他怎么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灣住船,岸上又沒有人,只有幾棵樹,遠遠的幾家人家做晚飯,那個煙竟是碧青,連云直上。誰知我昨日晚上讀了這兩句,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王維的這兩句詩引發(fā)了香菱上京泊船觀村景的聯(lián)想,以及讀詩倒像“又到了那個地方”的體認,都表明“人”(作者、讀者、詩中農(nóng)人)與大自然已經(jīng)有機融合為一體,表現(xiàn)了人與大自然主體相親之“意”,達到了人與大自然內(nèi)在和諧的崇高境界。雖然在這特定的時空里,眼前除詩人之外四野空曠,只“余”落日,似無它物,但是,此時詩人已將天地之間所“余”落日賦予人性,認為知己,人與自然景物“落日”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認同感,實現(xiàn)了內(nèi)在的“意”的和諧。何況遠處村莊星星點點,“孤煙”直上云霄,農(nóng)人樂享天倫。在這幅淳美的畫圖中,人與大自然實現(xiàn)了高度的內(nèi)在和諧。
本詩所寫的人與大自然的內(nèi)在和諧由以下三個層面組成了和諧之美的主體結(jié)構(gòu)。
第一個層面是審美移情。審美移情是指人的情感直接與客觀事物相結(jié)合,從而使知覺表象與情感相融合的過程。當人們凝神觀照審美對象時,就會產(chǎn)生將人的生命和情志注入對象、使審美對象顯示出情感色彩的現(xiàn)象。也就是說,審美移情是把人的感覺、情感移植到客觀事物里去,使原本沒有生命的事物仿佛有了感知、情感和意志,產(chǎn)生“物我同一”的境界。由于審美的移情性、主觀性的作用,因此詩人往往將自然景物賦予人的靈性。在本詩中,本應蕭索的秋山,卻為詩人而轉(zhuǎn)為蒼翠;本應枯竭的秋水,卻為詩人而每日潺湲;本應噤聲的秋蟬,卻為詩人而盡情鳴唱;本來闃無人跡的“渡頭”,卻因現(xiàn)實中“我”的閑適愉悅而顯現(xiàn)出落日的輝煌;本來雞鴨息鳴的“墟里”,卻因想象中農(nóng)人的歡愉而顯現(xiàn)出“孤煙”的輕飏。這都是詩人審美移情的結(jié)果,詩人主觀的“意”與景物人格化的“意”達到了內(nèi)在的和諧統(tǒng)一。
第二個層面是審美怡情。怡情是指陶冶情操,調(diào)節(jié)心境,使心情愉快。培根說:“讀書之用有三:一為怡神曠心,二為增趣添雅,三為長才益智。怡神曠心最見于蟄伏幽居。”其實,怡情豈止在讀書之時,更在審美之中、賞物之時。一般人在欣賞美景的過程中,身心獲得放松,性情得到陶冶;詩人在欣賞美景時,不僅心情變得愉快,情緒得到調(diào)節(jié),心靈得到凈化,情操得到陶冶,而且還會在賞物審美的過程中“思接千載,視通萬里”,遨游古今,物我兩忘。陶淵明在賞菊中洽受怡情,張九齡在詠月中感受怡情,孟浩然在垂釣中消受怡情,李太白在望瀑中享受怡情。在《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一詩中,詩人王維在移情欣賞景物的基礎(chǔ)上,自身也獲得了怡悅的享受。詩人扶杖倚門,望寒山轉(zhuǎn)翠,聽秋蟬吟唱,賞夕陽徐落,看孤煙直上,不僅精神得到無窮的美的享受,而且心靈得到極度的凈化,行到且行處,坐看云起時,晚風吹解帶,秋水映落日,真正達到了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崇高境界。這時,大自然的“美”與人物的“意”達到了內(nèi)在的和諧統(tǒng)一。
第三個層面是審美抒情。移情與怡情都是內(nèi)在的意識和情感,而審美抒情則是人物情感外化的手段。面對同一審美對象,不同的抒情主人公會有不同的感受,會抒發(fā)不同的情感;就面對“秋蟬”這一審美對象而言,不同際遇的詩人會抒發(fā)不同的情感。駱賓王《在獄詠蟬》抒發(fā)出“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的感嘆;王維在《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中也詠蟬,但他抒發(fā)的情感與駱賓王迥然不同:“寒山轉(zhuǎn)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在秋山逐漸由翠綠轉(zhuǎn)為蒼翠、清澈照人的秋水如彈琴般潺潺流淌的時候,詩人斜倚在柴門之外,靜靜地聆聽薄暮中秋蟬的吟唱,心情格外舒暢。在這里,詩人抒發(fā)的是出離官場,遠離塵囂,親近自然,慰藉心靈的暫且偷閑之情。不過,偷閑之情畢竟是“暫且”的,隱居山林并非沒有寄托。輞川之作表面上只是自然山水的描繪,實際上有王維清修的理想寄托。即是說,輞川別業(yè)實際上是王維心靈寓所、心中凈土;輞川詩的終極內(nèi)涵,是作者寓道的心靈語言。本詩的尾聯(lián)表面看來是寫好友裴迪乘醉狂歌,其實是詩人借裴迪之口抒發(fā)自己內(nèi)心深處的不平之情。在本詩中,景色的淳美、隱居的閑適與對張九齡罷相后朝廷奸佞專權(quán)的憤懣,都寄于田園,移于山水。這看似對立,實則統(tǒng)一,即統(tǒng)一在詩人寓情于景、借景抒情上,統(tǒng)一在人與自然的內(nèi)在和諧上。
由此可見,《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是一首淳美視域中天人和諧的田園交響詩。
參考文獻:
1.《蘇軾集·補遺》,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頁。
2.黑格爾[德]:《美學(第一卷)》,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79年版,第180~181頁。
3.《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校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頁。
4.培根[英]:《談讀書》,《世界文學》,1961(1)。
(作者為內(nèi)江師范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編校:董方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