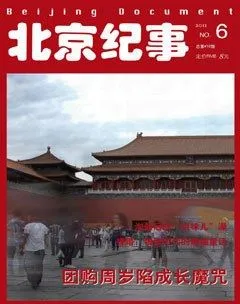北京七味之柴
2011-12-29 00:00:00陸原
北京紀事 2011年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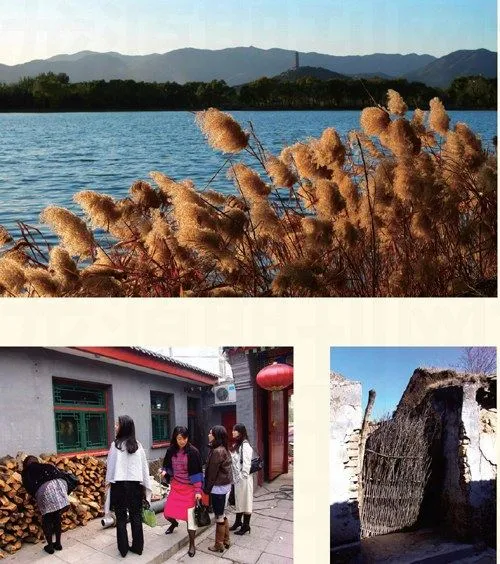
俗語說,家常過日子是“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字典說,柴是“燒火用的草木”。
草本的柴,是野草和莊稼秸稈。木本的柴,就是樹木。柴出自山野,只須費些采伐和搬運的功夫即可得來,因此在“七件事”當中售價最廉,但是可以名列榜首。我想大約除去協調平仄的原因,還有彼物待此物而熟的道理吧。可不能小看了這個“熟”字。教科書說,猿就是吃了熟肉,獲得了足夠的營養,然后才能頭腦發達,才能稱其為人的。你看那個“熟”字,底下那四個點,那就是火啊。
在煤炭、石油、電力、天然氣、核動力出場以前,柴就是火的來源,所以有“柴火”這個稱謂。就說沏茶吧,古人有煎水不煎茶之說,就是講究火候。陸羽《茶經》10個章節,有一節專說煮水:“其沸如魚目,微有聲為一沸,緣邊如涌泉連珠為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宋人龐元英說煮水要觀察氣泡,“初滾者曰蟹眼,漸大者曰魚眼,其未滾者無眼。”所以,蘇東坡在《試院煎茶》詩中寫道:“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新泉。”
掌握火候,那可是一門功夫,一旦遇到了狗屎運,其功效不下于十年寒窗。明朝學者張岱的著作《夜航船》里邊就記述了一則廚師善于掌握火候也可以當高官的故事。話說兩漢之交,群雄并起反抗王莽,為了統一號令,推舉了一位與劉邦沾親的窮小子劉玄當了更始皇帝。這位窮小子皇帝娶了趙萌之女,此后將政務全權委托給趙萌,自己終日酒色豪飲,給不少廚師封了高官,以致長安城里傳開了段子:“灶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你看看,能夠把骨多肉少的羊頭給燉爛乎了,就可以馬上封侯,這可比后來的白水羊頭見效快多了。
一旦到了柴米油鹽全都沒有了的時候,可就顧不上講究火候了。《春秋·左傳》記述,楚國軍隊圍困宋國都城9個月,致使城里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就是吃孩子,自家的孩子不忍吃,那就互相換著吃。無法出城樵采,城里邊能燒的也早都燒完了,好在尸骨有的是,那就劈了骨頭當柴火燒。這也難怪魯迅他老人家說,翻開歷史一查,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骨瘦如柴算是一個比喻嗎?在宋國,尸骨確實成了柴火。
然而嶙峋瘦硬的柴火,有時候和佳人一樣,也是能夠“入得廚房,出得廳堂”,經歷大場面的。女媧補天的故事盡人皆知,女媧是使用什么燃料熔煉五色石去補天的呢?蘆葦。當時不僅是天崩,而且還地裂,九州的地面裂開大口子,洪水泛濫成災。女媧使用蘆柴燃燒之后的灰燼,堵住了那些大口子,堵住了洪水。
天帝的兒子是天子,祭天是天子的專利權。北京人沒有不知道天壇的,全都知道天壇是皇帝祭天的地方,但是未必就知道皇帝舉行祭天儀式,從頭到尾全都離不開柴火。
祭天可是個大場面,皇帝要提前一日住進天壇齋宮實行齋戒。祭天典禮在冬至那天黎明開始,先要在圜丘下面的綠色琉璃磚燔柴爐里焚燒一頭牛犢,稱為迎神,意在請天帝聞到氣味下凡赴宴。皇帝從圜丘中層平臺走到上層平臺,到天帝牌位面前下跪上香,然后返回中層平臺行三跪九叩大禮,再上去跪獻玉帛,最后又上去三次獻三杯酒,每次都要一跪三叩。這套禮節,還要在天帝牌位兩側配享的祖先牌位面前重復兩次,最后率領陪祭群臣再行三跪九叩大禮,然后禮成,撤供。將供品送進琉璃磚的燔柴爐和鑄鐵的燎爐里邊,架上柴火燒掉,意在讓天帝帶回天上慢慢地享用。這樣算起來,皇帝祭天時,要由圜丘中層平臺至上層平臺往返19次,下跪31次,叩頭66次。這可是一宗力氣活,難怪有許多皇帝都要找借口派大臣替自己去“恭代”祭天。在明朝,就有兩位皇帝因為身子骨太柴,體力不支,祭天不能禮成,回去不久就一命嗚呼了。
說起明朝的皇帝,那個素質不是一般的差勁。不要說治理天下,有好幾位就連自己也沒有調理好,好不容易先皇駕崩,輪到自己登極,緊接著也就終極啦。為什么呢?他又沒有大種馬的體格,偏要一宿寵幸10個佳麗嬌娃,結果是這位一個月就駕崩了,那位一年也駕崩了。皇帝短命的結果,就是少帝即位。少帝即位的結果,就是率意胡為,以為做皇帝的職責,就是享受人生,享受天下,然后斷送天下。
清朝康熙皇帝8歲失怙,他也是少帝即位,他就比較懂得持盈保泰,他活到69歲,在位61年。康熙皇帝56歲那年,垂問大學士等人:明朝宮中每年消耗馬口柴和紅籮炭多達數千萬斤,你們知道馬口柴嗎?大學士等人回答,臣等不但不知,而且聞所未聞。康熙皇帝說道,木柴加工成三四尺長,表面凈白不能有黑點,兩端刻上馬齒狀的缺口,以便使用繩子綁扎成捆,這個就叫馬口柴。在清朝,馬口柴僅用于天壇祭天焚燒供品,但是在明朝卻當作御膳房做飯的柴火使用。這些奇聞都是康熙皇帝小時候聽明朝遺留的老太監說的。還說明朝有宮女9000人,太監10萬人,平時不許隨意走動,乃至于有飯食不周饑餓而死者。明朝有服務于皇家的四司八局十二監,皆由太監執役。如今在西安門大街有個惜薪胡同,就是明朝的惜薪司所在地,是供應皇家柴炭的機構。附近還有個大紅羅廠街,那是明朝貯存紅籮炭的倉庫。所謂紅籮炭,是在河北易州一帶采伐的硬木燒制的木炭,加工成為一尺來長、兩三寸粗的小段,裝入刷成紅色的小筐,供皇家冬季取暖使用。這種木炭火力強勁,灰燼呈白色,不會爆裂火星。
還有一個臺基廠大街,那是明朝的工部五大廠之一臺基廠所在地。有人告訴我,工部給皇宮造宮殿,臺基廠給宮殿造臺階和基石。可是《明史·職官志》告訴我,“臺基廠以貯薪葦”,也就是存放柴草。柴草堆放在高臺上邊以防水浸,說的是這個臺基。住過四合院老房的都知道,葦箔也是一種建筑材料。
還有一個辟才胡同,以前就叫劈柴胡同。有人告訴我附近還有一個大木倉胡同,大木倉里邊的木材下腳料,拿到劈柴胡同里邊賣,想象力頗為豐富。可是《明史》告訴我,明朝征稅分為三種:征收銀錢、征收鈔票、征收竹木。征收竹木的稅務所叫作抽分廠,截住販運竹木的客商,就要按照比例征收竹木實物稅,用作皇家的建筑材料和燃料。大木倉胡同,以前是明朝的抽分廠所在地。
元朝將路口拐角處稱為角頭,東城區的交道口在元朝稱為大都角頭,因路口緊鄰著大都路總管府而得名。交道口南大街一帶,在元朝有賣柴的柴市,柴市東邊現在叫府學胡同,是關押過文天祥三年的兵馬司牢房所在地。1283年1月9日,元世祖忽必烈親自出面勸降文天祥,遭到拒絕以后,在柴市設置刑場將文天祥殺害。文天祥臨刑前向南方跪拜行禮,最后一次表達了不忘故國的赤誠之心。文天祥是狀元出身,他在柴市刑場上還寫了一篇絕筆詩,最后那四句是:“天荒地老英雄喪,國破家亡事業休。惟有一腔忠烈氣,碧空常共暮云愁”。明朝推翻元朝以后,將柴市一帶的街巷命名為教忠坊,并在關押文天祥的地方建立了紀念祠堂。文天祥生前在這里寫作的《正氣歌》,如今就鐫刻在祠堂的東墻上。
說起詩篇,我倒想起一篇和柴相關的,可以拿來作結:
應憐屐齒印蒼苔,小扣柴扉久不開。
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
編輯/麻 雯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