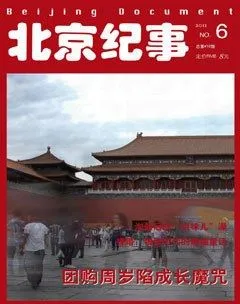革命“紅”人在北京
革命人物簡介
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縣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他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創建中國共產黨,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李大釗1913年冬留學日本。1918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并參與編輯《新青年》。俄國10月革命后,1918~1919年,先后發表《庶民的勝利》等著名論文,與陳獨秀創辦《每周評論》,積極領導了五四運動。1920年春,和陳獨秀開始醞釀組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10月,建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924年1月,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幫助孫中山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為改組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1927年4月6日,張作霖派軍警搜查蘇聯大使館,李大釗等60余人被捕。28日慷慨就義。李大釗還是一位著名學者,“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是對他一生的寫照。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李大釗文集》。
在中國共產黨90年的歷史中,李大釗這個名字十分響亮。而他又和北京有著密切的關系。從1916年創辦《晨鐘報》開始,到1927年壯烈犧牲,李大釗在北京度過了11個春秋。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李大釗為中國革命奮斗的足跡。
李大釗在北京先后居住過8個地方,這些地方記載了這位共產黨人的斗爭歷史。多數地址處于安全考慮被隱藏了,有證可考的只剩下兩處。
坐落在西城區西長安街南側文華胡同24號(原石駙馬大街后宅35號)是李大釗在北京的一處故居。他在文華胡同24號居住了將近4年,這是他在家鄉河北樂亭之外與家人生活時間最長的一個住地。文華胡同24號是一個很普通的小三合院,占地面積約550平方米,有北房3間,東、西耳房各2間,東、西廂房各3間。其中北房東屋為李大釗夫婦的臥室,東耳房為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的臥室,東廂房北間為李大釗長子李葆華的臥室,南間是客房。西廂房為李大釗的書房。李大釗非常喜歡這處住宅,因為它鬧中取靜,出行方便。當然更重要的是便于進行革命活動。李大釗的次子李光華、幼女李鐘華就出生在這個小院中,長子李葆華、長女李星華也都是在這里接受李大釗潛移默化的影響,最終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堆雪人,抗寒冬
有一年的冬天,北京城內下了一場大雪,雪花飛舞,一片銀裝素裹。李大釗對兒女說:“今天的雪下大了,你們快拿掃帚到院子里去掃吧!要是高興的話,堆個大雪人也好哇!如果有興趣還可以借雪吟詩,這比我小時候只能隔窗望雪作詩要好得多呀!”
孩子們一聽,一陣歡呼雀躍,立即拿掃帚蹦蹦跳跳地出去了。可是孩子的外祖母和母親卻十分反對。她們勸阻說:“外面天氣太冷了,要是凍壞了孩子怎么辦?”李大釗笑著說:“咱們的孩子應當從小就養成吃苦的習慣,免得將來長大了什么也不會做。何況人只有經常活動,身體才會有抵抗力!出去掃掃雪怎么會凍壞身體呢?反而是在屋里不動彈,才經不起風寒呢!”
李大釗說完話,就帶著兒女出了門。一邊掃雪,一邊給孩子們講故事,干得熱火朝天。
李大釗在后宅胡同居住的時期,是他人生事業的第一個黃金時代,也是他異常忙碌的時期。他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創建中國共產黨、建立國民革命統一戰線,鞏固和發展國共合作、領導北方革命運動作出了巨大貢獻。
唱一首贊美詩
在此居住期間,李大釗發表了各種文章140余篇,文字總量超過33萬余字,平均每9天一篇;參加各種會議約120多次,包括“共產黨三大”“國民黨一大”等,平均每10天一次會;陪同會見、拜訪各界人士30次,講演30次,還不斷地到廣州、上海、武漢、洛陽、天津等地從事教學和革命活動。
李大釗不僅向學生們灌輸革命真理,為革命事業培養接班的“火種”,在家庭中也經常教育子女要鍛煉膽量、開闊胸襟,努力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李大釗經常利用教孩子們唱歌的形式,潛移默化地傳播革命道理。在學唱教堂里的一首贊美詩時,其中有這樣幾句:“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我們就要歡喜,禾捆收回家。”
他邊唱邊講解:“你們看農民們辛辛苦苦地種下東西,收獲的時候是多么喜歡呀!他們忘記了辛苦,只有快樂。我們的革命也是一樣,等到革命勝利的那一天,我們會像農民把莊稼收回家一樣快樂呢!”
他還帶著李葆華、李星華去拍賣行買回一架舊風琴,由他彈琴伴奏教孩子們唱《國際歌》、《少年先鋒隊歌》等革命歌曲。教完歌還給他們講解歌詞的含義,講解從事革命的道理。這種寓教于樂的教育行動,在孩子們幼小的心靈里播撒下革命的種子。
中共北方黨組織的一些重要會議曾在李大釗的書房內召開。李大釗曾在文華胡同24號主持過黨的會議,接待過陳獨秀、鄧中夏、梁漱溟、章世釗和吳弱男夫婦等眾多文化名人、朋友、學生。這里也是李大釗和同志們、朋友們聚集活動談論事情的地方。
為黨起名
1920年1月,陳獨秀從武漢講學回到北京。因受到警察當局的追捕,由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化裝離開北京去上海。分手之前,他們分析了中國當時的國情,交換了建黨的意見,并決定南北相約建黨。李大釗和陳獨秀在建黨初期,書信往來頻繁,關于為黨起名的問題,陳獨秀來信問李大釗,李大釗和張申府研究后,定名為“中國共產黨”。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秘密組織成立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研究會很快發展到全國,很多會員后來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20年9月,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建立。成員有李大釗、鄧中夏、張申府、羅章龍、劉仁靜、張太雷等。同時,在李大釗的關心和支持下,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了。這些組織后來都成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組織。
在北京大學,他第一個公開宣講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唯物史觀,并組織了中國第一個研究馬克思學說的團體。反動當局十分害怕這種新思想的蔓延,曾暗中派警察便衣前來查詢這個團體的情況,李大釗機智地說這個團體是“馬爾格斯學說研究會”。警察趕緊向局里匯報,最后警察局認為這個研究會是研究人口論的。
李大釗在任北京大學教授、圖書館主任期間,參與《新青年》的編輯工作,是社會名流。但他生活儉樸,“冬一絮衣,夏一布衫”,一張大餅,一根大蔥,常常就算是他的便飯。
有人去他府上拜訪,見他的幼女鐘華,身穿紅粗布小棉襖,外套藍粗布小褂,前襟和袖口油光光的,土里土氣的,像個鄉下孩子,完全不像北大名教授的女兒。
有位親戚對此很不理解,有次問起李大釗,他只是淡淡一笑,說:“點種。”親戚迷惑不解:“莊稼人種地要點種,你當教授點什么種?”直到后來才明白李大釗所說的“點種”的意思!他所說的種子,就是革命的種子,共產主義的種子!
相約建黨
1921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華,他經上海來到北京,與李大釗商談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相關事宜。經過李大釗、陳獨秀的建黨準備,以及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籌備工作,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誕生了。李大釗因領導北京國立高校教職員工進行索薪斗爭,未能參加中共一大,經研究決定派張國燾、劉仁靜作為北京代表出席大會。陳獨秀也是由于公務難以脫身未能參會。在1921年11月簽發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定為由李大釗負責領導北方地區黨的工作,陳獨秀負責南方地區黨的工作。這就是大家常說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1923年“二·七”慘案發生后,李大釗被反動當局通緝,他就從院內有三棵海棠樹的石駙馬后宅35號,秘密地搬到銅幌子胡同甲3號,并在這里寫了《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紀念劉寧和“二七”》兩篇文章。這處宣武門內銅幌子胡同甲3號的住宅是李大釗在北京的第五處居所,位于石駙馬大街(現新文化街)南、回回營胡同東。往南穿過水月庵胡同,就是宣武門的城墻。
幌子是舊時商店門前懸掛或擺出的表明店內所銷售商品的標志,如酒店門前懸掛酒葫蘆,藥店懸掛的木制膏藥等。而用銅制的幌子招徠顧客的店鋪就是大買賣,銅幌子胡同曾經是店鋪林立,十分繁華熱鬧的地界兒。
幾進幾出于京城
1924年是李大釗一生中最艱苦、最繁忙的一年,也是最為輝煌的一年。
這一年春天,國共第一次合作,李大釗代表共產黨赴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并與孫中山先生共商大事。李大釗剛回到北京,北洋政府警察總監王懷慶,以“共產黨首領”罪名,下令通緝逮捕李大釗。得到消息后,李大釗剃去標志性的兩撇濃黑胡須,穿上長袍馬褂,扮裝成商人,由兒子李寶華陪同,攜帶輕便軟包,從容通過軍警的崗卡,進前門火車站去往五峰山。
李大釗與其子李寶華剛剛登上東去的火車,王懷慶派的軍警就闖進銅幌子胡同甲3號,經過一番搜查和盤問之后,一無所獲,悻悻離去。當天夜里,就有軍警裝扮成流氓,到院里尋釁鬧事,更有“盜賊”,偷偷潛入院內,偷雞摸狗,打探消息。
幾乎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派人登上五峰山,通知李大釗回京,率中共代表團到蘇聯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考慮實際情況,中共中央同意李大釗直接從五峰山至昌黎乘車赴蘇聯。
臨行前,李大釗派人送信給妻子趙紉蘭,信中說,“這不過是一時恐怖罷了,不出10年,紅旗將會飄滿北京。”
待李大釗從蘇聯回京時,已是楓葉剛紅的秋天。為了安全考慮,李大釗從銅幌子胡同甲3號,遷居到報子胡同對面的邱祖胡同居住。
往事如煙,歷史的一幕幕早已化成塵埃消失,但關于李大釗的傳奇人生,卻已深深烙印在古都北京,載入了共和國的史冊,永遠被后人所傳頌。
編輯/馮 嵐 icarusfe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