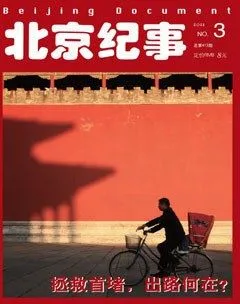龔琳娜:神曲《忐忑》之母
2011-12-29 00:00:00陽潔王玉
北京紀事 2011年3期


2010年一首《忐忑》在網絡上爆紅,并在幾個月內被迅速傳播,風靡國際,網民冠之以“神曲”的稱號。這首作品在極其快速的節奏中,夸張變形,獨具新意,演唱者夸張的表情和奇異的曲調,使得這部“神曲”備受爭議。隨后網友又自發掀起模仿狂潮,參與者不乏天后王菲、梁靜茹、郭德綱、杜汶澤等名人。而作為《忐忑》的演唱者,龔琳娜的名字也隨之一夜被中國聽眾所熟知。
神曲誕生記
龔琳娜,這位被稱為感動歐洲的中國民歌歌手,在民歌與新音樂之間游刃有余,被歐洲各大音樂廳爭相邀請,曾以一曲《走西口》為代表作。2010年,龔琳娜在人民大會堂北京新春音樂會上獻唱《忐忑》,一舉成名。
初見龔琳娜,她身穿貴州少數民族的服裝,臉上一直掛著微笑,對于一名如今風靡國際的歌者來說,這笑容顯得未免有些太“親民”。什么時候發現自己突然一下子就紅了? “其實我開始唱這歌是在四年之前,但真正被聽眾所知曉,還是在我參加完北京新春音樂會之后。”龔琳娜說,其實這里還有一個小插曲,“在上臺前我并沒有意識到,鏡頭會把人打得那么厲害。大年初五我回到家,看到在人民大會堂我演唱的這個視頻,我自己就沒法看完,我說這多難看,眼睛都對上了,把我嚇死了,我根本不知道好不好,也不敢打電話問朋友,就自己藏起來了。但沒有想到,居然就是這個視頻被網友轉載。當時我還在德國,我有朋友給我發郵件,跟我說你上網看看吧,結果我一看,大家的評價太有意思了:神人,神曲。還有網友說這是國產神曲。其實,我想糾正一下,這首歌是德國作曲家寫的。”突然一下子“火了”,你對于這件事怎么看待呢?我問龔琳娜。“我覺得這個事也不是那么突然,因為我基本上用了八年的時間,一直默默地在創造我的新音樂之路。在這些年中,我唱了很多的歌,并不是只有《忐忑》這一首。《忐忑》恰好是在合適的時機被大家聽到了,所以它一下子爆發了,對我來講,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首歌那么難,還有那么多音樂界的朋友及網友愿意學唱。”
談起《忐忑》這首歌要講的內容,我問龔琳娜,你覺得這首歌傳達的是一種什么樣的內容呢?“是一種生命力,”龔琳娜對我說,“一種旺盛的生命力,就是說,如果你聽了這首歌,會把你激活。”有沒有一個具體的內容,或者表達思想呢?“沒有,就是人的聲音像樂器一樣的,它會有多種多樣的變化和上下跳動,如果你聽這個歌,不是說要去聽它表達了什么中心思想,最重要是聽了它以后,會讓你坐不住,會讓你也想動,會讓你的毛孔張大。”第一次唱這首歌的時候,就有這種感覺嗎?“是的,我第一次拿著這個作品的時候,第一次唱的時候,感覺我的心一會兒上一會兒下,有一種很強的什么東西要冒出來,所以我取名叫《忐忑》。”什么東西你感覺要冒出來?“那就是生命力,”龔琳娜看我聽得有些吃驚,笑著解釋道,“我們每天面對的生活,也許很無聊,很麻木,每天都做著一樣的工作,或者心情很低落的時候,人需要激發,比如說你看一場電影,它讓你流淚,你聽一首歌,它讓你感動,你去見一個老朋友,激起你對過去的回憶,那都是讓我們的生命變得更有色彩,更有意思。所以我希望我在唱歌的時候,歌里面也有這樣的東西。它會給人鼓舞,給人希望。”
請叫我新藝術歌者
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如何去形容龔琳娜,當我第一次看到視頻的時候,我覺得她的聲音很特別,因為《忐忑》是沒有歌詞的,只用來表達自己的一種情緒。之后我翻閱網上資料,發現原來龔琳娜并不是一開始就走“非主流”路線:龔琳娜5歲登臺演出,7歲全國巡演,12歲初訪法國,1992年~1999年,龔琳娜先后考進中國音樂學院附中,之后又被保送中國音樂學院繼續本科學習,在這7年中打下了扎實的基本功。1999年,龔琳娜獲得文化部授予的“民歌狀元”的稱號。我不禁納悶了,對于一位嗓音條件極佳,求知欲強又勤奮的歌者,這一切都顯得那么順理成章,為何她卻突然放棄在這條康莊大道上前行,反而輾轉去了一條不被人看好的小路?龔琳娜向我解釋道,那時候她的音樂之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瓶頸。“當我決定放棄我在中央民族樂團的工作,決定放棄像很多歌星一樣出名的那條路,準備走上一條中國新藝術歌曲的路的時候,是很艱難的。因為新的東西沒有形成,而長期占主導地位的老的東西,全部又要剝掉。”
至于是什么原因讓自己走上這條新藝術歌曲的道路,龔琳娜講了個故事。“那是我還在北京的時候,因為我們家住在八層,每天練歌的時候,我一唱高音,比如彝族的高腔,樓上的鄰居就來敲門,說,你一唱到高音,我的心臟病就要發作了。那段時間我真的特別壓抑,我每天練歌的時候,一邊唱著,還要一邊擔心千萬別讓鄰居的心臟病發作。”龔琳娜模仿鄰居的樣子,用手捂著胸口。“后來我去了德國,住在巴伐利亞森林的旁邊,有一個小山坡,我就跑到山上去練歌。那時候我每天都唱得很盡興,因為再也沒有人干擾我了,我就大聲地喊,大聲地唱。那讓我真正感受到,原來人與自然是可以融為一體的,我覺得我整個人都打開了。有一次我在山上唱歌的時候,那時候我的孩子三個多月,我把他背在胸前,當我一唱,好多馬跑過來了,當時我特別害怕,那些馬那么大,我也跑不過它們,我抱著小孩我不敢跑,就只能站在那兒,它們離我越來越近。當時嚇得我腿都發軟,因為那種情況下我并沒有考慮到馬不會傷人,它們卻一群把我圍住,用鼻子來觸摸我的身體。那是我第一次確確實實地體會到,原來音樂是可以超越國界、超越種族的,也從那時候起我就決定,做一名真正的歌者,唱出自己的靈魂。”
“新音樂歌者這個稱呼是我一直追求的,我希望能在中國的傳統音樂的根基上,更往上發展,更國際化地發展。”在采訪過程中,我始終無法把坐在我對面的她,與那個舞臺上表情夸張,神奇極度亢奮的她聯系在一起,“在演唱的過程中,我整個人就進去了,就是說,我進入了那首歌里面,被賦予了一個新靈魂,我自己也就不重要了。”投入是一件很難的事,要做到真正的投入,需要拋棄很多東西,比如別人的評價。“但是我很享受。在唱歌的時候,如果你過多地關注你的‘臺型’,那么我認為你不會是一個好的歌者。”
神曲之父——老鑼
那么,在這么多模仿你的人中,龔琳娜覺得哪個模仿者模仿得最到位?答案就是老鑼。老鑼是一個德國音樂人,是《忐忑》的作曲者,同時也是龔琳娜的先生。老鑼和龔琳娜的緣分也是由音樂開始的,可以說,如果沒有老鑼,也就沒有今天的龔琳娜,沒有今天的《忐忑》。
2002年,老鑼和幾個朋友一起在北京搞了一個音樂會,當時在中央民族樂團的龔琳娜是作為觀眾來欣賞音樂會的。“老鑼在臺上跟中國音樂家合作,他談巴伐利亞琴,我在臺下跟我的好朋友,一個彈古箏的女孩坐在一起。音樂會完了之后,我的朋友就想見一見他的琴。老鑼留下了我們倆的電話,說你們倆是音樂家,哪天我們倆一起玩音樂吧。”從此以后你就愛上他了嗎?“不是,”龔琳娜笑了,“其實我們倆的感情是在討論音樂中慢慢培養起來的。”
“記得第一次我邀請他去我們家,我母親拿出我的VCD,是我參加比賽或一些節目的演出,很自豪地放給他看的時候,他對我說,太惡心了。他說那不是你,我在里面聽不到你。他把我的心里的聲音給說出來了。其實我一直都是這樣想的,只是我身邊一直沒有人這樣對我說,因為在那個環境里,如果你不能出名,不能當明星,那你就是失敗的。而我就是想把歌唱得舒服,唱得爽。可是真沒有人告訴我,所以經常我會想,是我想錯了嗎?”龔琳娜和老鑼從那時起就“一拍即合”了,并于2004年步入了婚姻殿堂。
談到先生,龔琳娜很滿意。“很好,拋開他作曲家的身份,他還特別懂生活,他做一手拿手好菜,有一句話不是說,要想留住男人的心,先要留住男人的胃嗎?在我們家這句話正好相反。因為我是南方人,在德國住的時候,我不會做面食,但有時候我非常想吃糖花卷,他就給我做。而且他非常地幽默,比如說我懷孕了,他每天看著我的肚子,非常羨慕地說,上帝太不公平了,為什么只有女人能懷孕,男人就不能懷孕?然后我生了小孩,開始喂奶了,他說實在是更不公平,為什么懷孕的機會都不給男人了,喂奶的機會還要給女人呢!然后他就跟我說,這樣吧,我們倆分工,你管‘進’,我管‘出’,就是我管喂奶,拉屎拉尿換尿布洗屁股全是他管。”龔琳娜拿出他們的全家福給我看,照片中的她將兩個兒子抱在懷中,臉上洋溢著作為一個母親所獨有的幸福與滿足。
對于《忐忑》這首歌褒貶不一的評價,龔琳娜沒有因反面的聲音而退縮,也沒有因正面的褒獎而驕傲,她一直為自己的音樂道路努力著,奮斗著。正是由于這種對藝術的執著與堅定,才使得曾經的“民歌狀元”的龔琳娜,放棄了成為主流音樂家的機會,她為自己選擇的這條新藝術歌曲的道路,就是讓她的藝術之路,隨著內心的方向得以延續。
編輯/任 涓woshirenju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