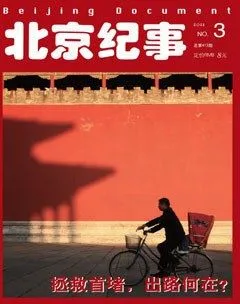放空鐘
形容人們發家了、富裕了,光宗耀祖,老北京人慣用“您瞧,抖起來了不是”。這“抖”的便是“空鐘”,是流行于舊京年節的兒童游戲。時下孩子們的玩意兒跟從前大不相同,小到掌上游戲機,大到米老鼠迪士尼,不勝枚舉。許多老北京孩子的玩意兒,已經被無情地拋棄了。盡管空鐘科技含量不高,制作也不甚精良(含自制),但也伴隨著這座古城的孩子們一道見證了歷史,走過了無數春夏秋冬的風風雨雨。想想,雖然是時代發展之必然,卻多少也是遺憾。
那日清晨被一陣“嗡嗡”聲喚醒,音律忽遠忽近,錯落有致,那么熟悉。照早先住大雜院兒里,我準一道煙兒循聲而去,現在望樓興嘆,只能憑窗眺望啦:這應該是一只十六響以上的大空鐘,聲音悠遠宏亮,朦朧間我仿佛回到了從前,回到了空氣中彌漫著鴿子哨、空鐘鳴叫聲的歲月……
空鐘即空竹,以竹木制成,中空,因而得名。據說此物起源于葫蘆,還俗稱響葫蘆。我猜想,早先就是葫蘆,后經演化僅形似而已,多半兒取的是葫蘆的諧音“福祿”,又是官又是財,都是吉祥的詞兒。至于為什么又叫“空鐘”,這里面就有點兒說道兒了。“鐘”就是鐘表的鐘。只不過在這里,它不是一般看時刻的鐘表,而是觀季節的“時鐘”,還非常準確。舊京,“放空鐘”只在過年時進行,平常不興。“空鐘”一響,就過年嘍。“空鐘”一詞既含有空竹豐富的內涵,又融有時令節氣參照,實在是奇妙,這就不是單純的玩兒了。
在空中旋轉的空竹其形制可分為單輪和雙輪兩種,中有木軸,輪盤四周有哨口,大的方孔叫“悶兒”;小的長方形細的眼兒叫“響兒”。大哨口發低音,小哨口為高音。孔內木片作笛,拽拉抖動空竹,各哨同時發音,高亢雄渾,聲入云端。玩家雙手各持小棍,頂端系一繩的兩頭,懸空竹扯拉旋轉,越快越響,而且還是高低音合奏。
每年春節的廠甸,男孩子磨著大人買的大多是風箏和空竹,到手立馬拿出去向小朋友顯擺,接著胡同里便響起悠揚的“嗡嗡”聲。空竹一定要抖,不抖就玩不轉,不轉就不響。我的第一個空竹是十二響兒倆“悶兒”的,在我們那條胡同里是最大的,令小伙伴們羨慕不已。但很快我就從得意變成了失意,十二響兒的空竹拉起來頗為不易,放響更難。多虧了隔壁的“瘸二爺”指點迷津,給了我一個搪瓷茶缸的蓋子讓我拿它練,后來我把家里能抖起來的相同形狀的杯子蓋、鍋蓋、壺蓋都抖了個遍,終于放起來了十二響兒的空竹!那叫一個得意。
“瘸二爺”腿腳雖然不太麻利,但空竹抖的那可叫一個絕。他的空竹就不光是抖了,由抖而變拋、甩、飛、盤、套、挑、跳、爬、鉆、繞……再結合身體動作,千姿百態、變化多端、滿眼飛靈了。玩起來空竹忽左忽右、忽高忽低,時而身前,時而身后。舒緩時如行云流水,連綿不斷,勝似閑庭信步。急重時瞬息萬變,直刺如劍,橫砍如刀,擊打如棍,翻卷如鞭,酷若舞槍使棒。時而快如電光,夢境般地飛舞著;時而慢如落花,在和風里飄搖。慢時無聲無息,快時激起攝人魂魄的陣陣嘯聲。令觀者眼花繚亂、目不暇接。一時間你會忘了他那條瘸腿,忘了那兀自上下翻飛的空竹,沉浸其中就只有感嘆的份兒了。
深藏不露的是“瘸二奶奶”,大腳,旗人。平常日子口“瘸二爺”玩的時候,她決不摻和,樂呵呵站在一旁,遞個手巾把兒,送壺釅茶。那日巧,趕上二奶奶高興,從家中取來一長一短兩副竿子,短的一尺,長的丈二,都垂著長長的黃穗子,據說是二奶奶的陪嫁。單只這家伙什兒一亮,引得路人紛紛駐足。丈二的竿子在她手中揮動自如,單輪空竹仿佛粘在繩線上一般,劃過大大的弧線,或上或下地變換著旋轉著,伴著黃穗飛舞,美妙和諧。換短桿,空竹甚至沿著交織的繩線一級級爬高,名曰“絲瓜上架”。我偷偷問過二爺他的功夫是不是二奶奶教的?二爺對我說:記住嘍小子,藝高一招就是師傅。
老北京孩子的玩意兒,是包容在胡同、四合院里的。在那種鄰里密切的環境中,只要在窗戶跟前招呼一聲,其他孩子便跑出來和你玩在一起了。現在不行嘍,住在混凝土澆筑的塔樓里,即使兩家住得再近,也被防盜門隔得如月球那么遠,那些“吃了嗎您?”的問候聲聽不到了。得打住,說遠了不是。不過,現在咱北京的水越來越清了,天越來越藍了,抖空竹隨著健身活動的發展越發受到人們的青睞,公園、廣場、綠地多有抖空竹的人群。抖空竹這種兒童游戲在新時期已經成為全民健身的一個項目了。
空竹之聲是和諧之聲,是在這太平盛世里的和諧之聲,也是北京的符號。
編輯/任 涓 woshirenju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