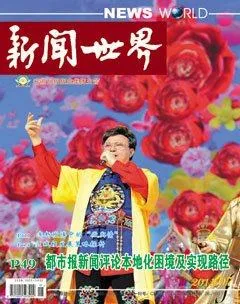論電影《盜夢空間》的敘事結構
【摘要】2010年,克里斯托弗·諾蘭把一個寫了近10年的故事搬上熒幕,展現在世人面前的絕不僅僅是一部感官大片,“夢境”這一母題的描述多少給《盜夢空間》增添了一絲“心理懸疑”的色彩。電影未上映之前影評界的熱烈追捧,劇組創作成員的閃爍其辭,都讓《盜夢空間》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正如電影本身要為我們表現的主題一樣。影片的主演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在采訪中說:“這部電影,完全是克里斯托弗·諾蘭對夢境的理解和想象,里面有特有的結構、規則,這些也是諾蘭的創作內容之一。”如果將電影界比作浩瀚的宇宙,那諾蘭一定是擅長電影敘事形式主義的一朵奇葩。
【關鍵詞】《盜夢空間》 敘事結構 復調敘事 敘事角度
一、《盜夢空間》內容梗概
弗洛伊德說,“夢境是避開壓抑作用的迂回之路,它是所謂的間接表白所用的主要方法之一。①” 14年前憑借影片《泰坦尼克號》走紅的好萊塢男星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飾演的男主角唐姆·柯布是一名高科技竊賊,他利用在人的夢境中竊取有價值的商業機密的盜竊手段而獲利,他認為人的潛意識是可以被操控的,潛意識的能量也是不可估量的。因此,人可以在夢境中發揮幾乎是全知全能的能動性去獲取一切需要獲得的信息。在對潛意識能量的探索中,柯布喪妻,并且被指認為殺妻兇手只能遠走海外,丟下家人開始流亡的生活。柯布在一次對商業巨賈齊藤的任務中失利,卻反受雇于齊藤,此次任務的內容是對齊藤競爭對手的新一任繼承人植入“解散家族企業”這一意念,而相應的回報則是撤銷對他的指控,重返美國和家人團聚。
二、敘事角度的糅雜與轉換
普林斯認為敘事學是這樣的一門學科,它研究不同媒介的敘事作品的性質、形式和運作規律以及敘事作品的生產者和接受者的敘事能力。如果將電影《盜夢空間》作為藝術文本來研究,那么導演諾蘭的敘事功底在影片當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電影作品從文字文本轉化為視聽語言,是導演在其統一的意志下層層鋪開的過程,為了豐富作品的張力和表現力,往往會采用多角度敘事來進行展現。“在敘事作品中,視點不僅反映敘述者和人物的所知、所感和所為,他還反映敘事作品作者的心理、立場觀點和意識形態。②”大體上來說,敘事角度一般分為:全知全能敘事,限制敘事和純客觀敘事。由于母題是“夢境”,電影主要展現的是主角如何潛入他人夢境并竊取機密,《盜夢空間》在敘事角度上主要采用純客觀敘事,這種敘事手法,也稱第三人稱敘事。托多羅夫認為這是一種典型的“敘事者小于人物”的敘事視角,這種視角能充分的展現客觀生活,以及客觀事物發生的全過程。采取這種敘事視角,也為《盜夢空間》蒙上了一層后現代主義的色彩。但本片并不是單線展開敘述,諾蘭為柯布預設的感情奠基也是其中一條重要的敘述線。在“回憶”的部分,采用了以柯布為第一人稱的限制敘事視角。主客觀多方位的敘事手法,使該片在敘述視點上轉換糅雜,顯得更富張力。與此同時,也給觀影者帶來了一定的挑戰,需要其投入更多的分析和關注去感受和理解該片意圖。
三、敘事結構的交叉變異
電影《盜夢空間》在“柯布完成齊藤的任務”這個主系統和多個“每一層夢境”這樣的子系統,分別采取了不同的敘事結構來構架。
在“柯布完成齊藤的任務”這個主系統的故事中,諾蘭采取了傳統的因果式線性結構。雖然作為科幻懸疑電影,影片在一開始并沒有透露時間地點這樣典型的表明因果的信息,卻花費了近15分鐘的時間去表現一次盜夢任務即“盜取齊藤的信息”,而這場任務的失敗卻成為整部電影發展的一個誘因——齊藤反雇傭柯布。隨著這次任務的展開,故事線條逐漸清晰,人物心理性格也得到了充分的描繪。主線追求情節的環環相扣、邏輯嚴密完整,并有相當激烈的外部沖突。比如天才造夢師阿德涅與柯布的相遇,學習如何造夢,和她得知柯布內心深處的情感秘密之后所遭受的心理沖擊;盜夢團隊的組建,各類人物的參與,都和整項任務密切相關,且具有明顯的目的性。
在子系統中,也就是“每一層夢境”的敘事結構上,諾蘭采用了“回環式套層結構”。回環式套層結構,是以多層敘事鏈為敘事動力,以時間方向上的回環往復為主導,情節過程淡化,講述方式突顯。這種敘事結構是一種非線性的結構,即不以時間為發展線索,強調觀眾在觀影過程中以理性的思維去思考建構,從而理解影片意義。柯布展開的盜夢行動這個部分,一共四層夢境,每一層夢境都是以上一層夢境而展開,深入,最后通過外部的刺激而回到上一層夢境中。每一層夢境都是下一層夢境的驅動因素,為下一層夢境提供可能,次級夢境則是上一層夢境中任務得以成功的保證。這樣的套層使得影片情節環環相扣,缺一不可,并使得影片節奏更加明快和緊湊。在最后一層夢境,也就是柯布和梅爾建造的荒蕪中,柯布終于走出對亡妻的愧疚,找到在夢境中死亡的齊藤并成功的將其帶回現實。同時,也意味著柯布這個角色完成了對自己心靈的救贖,使得全片的感情線得以完整和升華。在筆者看來,影片中沒有出口的樓梯和永遠不會停止轉動的陀螺,恰恰意指這種潛在的循環往復性。
《盜夢空間》中,夢境里的時間比現實中的時間慢很多,時間在這里產生了一種“縮放效應”。現實中的一小時,等于夢里的五分鐘,而上層夢境的五分鐘,又等于次層夢境的一周時間。在夢一層層深入的時候,時間在這個時候反而以一種相對的形式發揮作用。因此,在各層夢境同時發生深入的時候,交織式對照結構講述了子系統之間是如何相互聯系和作用的。在首層夢境中汽車落水的幾十秒鐘與后層夢境時間上的畸變,以及影片開頭柯布落水,而夢境被大水淹沒給觀眾帶來的視覺沖擊和心理壓力,都體現出這種對照結構的魅力。
四、“復調”敘事手段的運用
在細節的處理上,導演更多的運用到了“復調”的敘事手段。
“復調”最初是一種音樂術語,后來被引用到文學領域。巴赫金用復調這一術語來開拓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詩學特征,即在一部完整的小說中存在的“多個聲音”。后來這一術語更被廣泛的應用到美學,電影學等多個領域。夢幻式復調結構具體表現為電影當中現實和夢境的對話和沖撞,以凸顯人物的“心理時空”,深入刻畫人物性格。電影中,意識與潛意識(夢境)的沖撞也是復調的主要體現。現實中柯布深懷對亡妻梅爾的愧疚,亡妻的意向卻不斷的在夢境中出現,并且犀利激烈地責罵柯布,不僅加深了柯布的愧疚,同時也延伸了他對梅爾延綿不絕的回憶。現實中柯布對兒女的熱切思念,而夢境中卻總是出現兒女定格的背影,可以說是柯布有意識地對自己潛意識壓制的結果,卻遭到潛意識的反攻,最后潛意識竟成為任務最大阻撓。在最后一層夢境中,柯布與梅爾重遇,柯布回歸現實的意識最終勝利,意識與潛意識得以同化,兩者由對立面達到統一。
《盜夢空間》突破了傳統敘事視角和敘事結構,多視角轉換和多結構的糅合,打破了時間的固定性,擴大了時間的畸變和夸張的場面運動設計,對于導演本是一場挑戰,而觀眾也在導演的巧妙敘事下,經歷了兩個半小時的奇妙之旅。影片的最后由一個不停旋轉的陀螺結尾,開放式的結局,留予了觀眾更多的思考空間,正因如此,也加強了觀眾對電影文本的自我構建和解讀。
參考文獻
①弗洛伊德:《少女杜拉的故事》,九州出版社,2008
②祖國頌:《敘事學的中國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作者單位:四川師范大學文理學院傳媒系)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