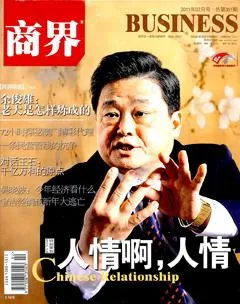2011地方稅改潮
2011-12-29 00:00:00盛立中
商界 2011年2期


2011年,財經圈內最有可能入選的流行語:“讓稅收飛”。在激烈的結構性減稅與地方稅改的大潮中,企業最需要做的事情,首先是系好稅負的安全帶,而不是老想著遇到麻煩時如何乘救生艇逃生。
地方稅改起步
2010年下半年,新疆拉開資源稅改大幕;2011年初,海南啟動“離境退稅”、“離島免稅”;與此同時,關于房產稅、車船稅的爭論更是甚囂塵上……套用一句流行語,2011年,“讓稅收飛一會兒”——轟轟烈烈的地方稅改潮正呼之欲出。
眾所周知,我國目前的地方稅稅種主要包括:營業稅、地方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資源稅(其中的海洋石油企業資源稅屬中央稅)、房產稅、土地稅、車船稅、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和一些其他的附加稅(費)種。現實的情況是,由于稅制多次變動,我國的分稅制體系并不嚴謹,上述多數稅種大部分還屬于收入共享,而非地方政府獨占。
“十二五”來了,從地方層面,中央政府最近釋放出關于財稅配套改革幾個重要信號:一是健全省以下財政管理體制,賦予地方適當稅政管理權;二是進一步理順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
這些信號是什么意思?我們的解讀是,“十二五”期間,步入深水區的地方稅改所牽動的利益關系,將有一些重大調整。
在地方稅改層面上,除了地方政府的稅收立法權問題比較糾結外,在稅收方面,由中央政府主導的資源稅改革已經起步,某些地區已經開始受益,而營業稅、房地產稅、環境稅、車船稅、個人所得稅以及社保費改稅,也已經進入2011年的稅改議程。
在此輪稅改中,對企業影響最為深刻的稅種主要有:資源稅、環境稅、營業稅和社保費改稅。但其中的“社保費改稅”,說白了只是一個換換跑道,由過去的軟約束變硬約束,對企業既有利益的影響并不明顯。
那么,我們的企業又應該關注些什么呢?
房產稅怎么看
作為地方政府,要有穩定的稅收來源,賣地這東西總是靠不住的,而土地也被地方官員們折騰得差不多了,賣地成本越來越高。中央政府在這個時候賦予地方政府收稅權,這是他們求之不得的事情。
至于房產稅開征影響到地方政府的土地生意,以及從高房價中謀利的問題,并不像外界認為的那樣嚴重。不管哪一級政府,財政收入還是要靠實體經濟、靠稅收,賣地從本質上看,無異于敗家子行為。
另一方面,在中國城鎮家庭的資產構成中,房產已成為最主要的資產,占比高達62.72%。龐大的個人資產,無疑是未來物業稅瞄定的主要標靶。地方政府也會由此得到穩定的稅源支撐,這也是物業稅醞釀推出的初衷。
房產稅改革的目的,并非簡單增加地方財政收入,而與解決高房價混在一起,更是有些牽強。于是,重建地方稅收體系,首先要做的是撤并掉那些不合理的稅費,其次是中央收入的適當讓利,在保持稅收中性原則下,建立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地稅體系。
換言之,新的地方稅稅收框架的搭建,企業與居民的總體稅負應該是下降的。至少,不應該增加。
結構性減稅中的風險與機會
不妨先從大處來看。中央已經定調,2011年繼續進行結構性減稅。結構性減稅是在“有增有減,結構性調整”下,側重于減稅的一種稅制改革方案,是一種有選擇的加減法,屬于特惠制而非普惠制。而減稅的結構性,也意味著企業的結構性機會。
然而,企業要從中獲得較實在的稅收利益,并不現實。很明顯的例子是,有些行業和企業(比如資源煤炭行業)在結構性減稅的大背景下,稅負反而是增加的。而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幅,卻絲毫未因結構性減稅而減緩,反而超越了GDP的增速。
理論上,任何資源環保類上游產業稅負的增加,終將傳遞到下游的終端企業。其中受影響較重的可能就是中小企業。有資料顯示,占我國GDP60%左右的最終產品和服務價值是由中小企業創造的,繳納的稅金占全國稅收總額的50%左右。
因此下一步,企業要密切注意資源稅改革后的稅負轉嫁鏈,切忌成為資源稅改革后的最佳稅收終端。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營業稅改革,此項改革對地方財政收入影響甚巨。營業稅的課征對象主要是服務業,其收入大多歸屬地方財政。具體到行業而言,營業稅改革(主要是增值稅擴圍)受益最大的是倉儲物流交通運輸行業,此外,建筑業和服務外包業也將受益匪淺。為穩定稅基,金融保險企業的營業稅改革可能來得比預計的要保守。
現行營業稅的主要問題,在于盡管營業稅屬于地方稅收入的主要來源,但減免權全部集中于中央政府。原則上,營業稅對企業和個人一律不予個別減免稅,但在實踐中,減免稅“個例”,甚至包括直接利益輸送的政策幾乎時時發生。而像外包業務,自2009年開始,我國對離岸服務外包業務收入實施暫免征收營業稅政策,但有一定的期限、門檻、區域等框架條件規定,不僅限制較多,而且審批手續繁瑣,很多中小企業被拒之門外。
值得警覺的是,即使在中央層面,現在的稅收政策有一種被利益集團或官辦企業挾持的傾向,比如官辦的中小企業擔保機構稅收優惠政策;通訊、郵政的專項免稅政策;包括鐵路、航空在內的國有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等,僅剛剛過去的兩年內,我國就出臺了大大小小的十幾項與營業稅業務有關的稅收減免政策。尤其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由中央政府操作的稅收優惠,大多由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埋單。
此輪地方稅改革后,如果某些稅種的立法權下移地方政府,企業可能有更多的機會。
企業稅負的安全帶
華潤集團曾在一份內部總結中稱,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后,整個集團的稅負不減反增,GDP稅負率比全國高出20%,增值稅稅負率大部分高于行業水平,個別子公司甚至高出88%。究其原因,一是對稅務管理重視不夠,在經營決策中很少考慮稅務事項,導致不必要的稅務損失;其次是沒有配備專業稅務管理人員;三是很多稅務優惠政策沒有運用到位。
有研究報告顯示,具備稅務風險管理意識的企業家比沒有此意識的企業家,平均每年為公司多創造的利潤高達38%!然而我國的實際情況是,各稅種的名義稅率一直偏高。較高的名義稅率對企業家們的風險在于,誰也不知道何時可以參與“零和游戲”,何時可能被“依法治稅”。一張白條入賬,可以罰三五千元,也可以“合乎用途”。任何企業也難以擺脫這種罰有理、不罰也有理的窘境。
2009年,審計署有個總結認為,我國稅務部門自由裁量權太大。有專家曾頗有體會地稱:“不管什么稅率,也不管什么會計、審計,總之每年都要被稅務局評稅,討價還價,吃喝一番,再疏通一下就降下來了。”不過從根本上來說,為爭取更多的稅收優惠,企業還是要對稅收自由裁量權予以更多的關注。
企業另外面臨的一個問題是,中央政府的稅收優惠政策執行的彈性過大。在不富裕的地區,中央的某些稅收優惠政策存在被打折的風險,或通過嚴格的稅收稽核,或通過提高操作門檻等其他拐彎抹角的方式;而在一些稅源相對充裕的地區,地方政府可能會通過一些地方稅種的減免稅優惠政策,比如減(免)某些附加稅費,吸引外來投資。對此,希望企業要學會與稅收討價還價的技巧。
最近看到,不少人紛紛為節能減排和打壓房價設置新車船稅和房地產稅獻計獻策。事實上,一個好的商業環境,稅制必須要保持相對穩定。稅收不能像公共場所的旋轉門那樣被決策者推來轉去。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國開征的那個筵席稅,最終變得不倫不類就是切膚之痛。減稅并不意味著減收,相反,在一個不受納稅人約束的財政體制框架下,任何加稅舉措,無疑皆是讓所有人都站在通往地獄的跑步機上,沒有人可以幸免。
這么說吧,企業稅務風險防范之要旨在于首先系好安全帶,而不是老想著遇到麻煩時如何乘救生艇逃生。
此外,作為地方政府,應該盡快理順自己在市場管理中的角色。為公民提供服務是政府的義務,也是納稅人之所以賦稅的根本原因。政府對城市的管理,來自納稅人的授權。除了必要的公共物品供給,政府不能以公權的名義參與市場盈利活動,乃至“攥著橡皮圖章不顧吃相”地老是往自己家里鼓搗東西。
我們始終認為,在時下的中國,解決財稅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轉型中的問題,絕不是錢的問題,關鍵在于政府有沒有這個決心。
編 輯 白 靈
E-mail:bl@cais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