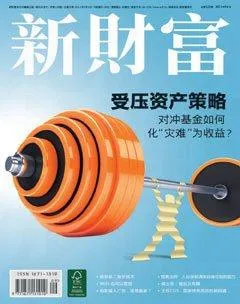世界經濟下一輪是貨幣危機
2008年金融風暴爆發至今的3年來,世界經濟進入了比較快速的恢復期,但是深層次的矛盾并沒有解決。2011年8月初以來,美債危機爆發,引發了新的一輪金融市場波動。這輪波動會對世界經濟和金融體系帶來什么影響?下一輪危機的爆發點在哪里?世界經濟走勢在未來若干年將會如何演繹?這一形勢下,中國應當如何準備,臨陣以待?這些問題我們必須要有預判。
美國經濟徹底恢復路途茫茫
美國是全球金融風暴的策源地,美國經濟本身也蘊藏著深刻的矛盾,必須解決。上一輪金融風暴之所以比較快地結束,美國的主權信用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國以其主權信用為擔保,幫助私人部門修補資產負債表,由此帶來了資產價格的迅速上漲,也帶來了經濟比較快的恢復。但是如今,美國財政部的債券信用卻出現了明顯的下滑,財政開支在未來必須削減,投資界對美國經濟預期出現了新的一輪下調。
那么,美國經濟到底出現了什么問題,其如何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呢?可以說,從本質上講,美國經濟體制正面臨著深刻的改革重任。
用二元經濟形容今天的美國經濟再恰當不過。這就是說,美國既有極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部門和人群,包括高科技、高等教育、高端制造等方面,蘋果、微軟、谷歌、波音等大公司比比皆是,但是必須看到,美國還存在著一大批不具備競爭力的產業、部門和人群,積聚在低端制造業、普通的國內服務業,他們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犧牲品。
這部分不具備競爭力的部門所對應的人群,是一批沒有受過良好基本素質訓練、從拉丁美洲國家通過非法移民或投親靠友進入美國境內的、連英語都講不好的新移民,這部分人事實上已經成為了美國經濟和社會的包袱。由于這部分人的進入,美國已經成為了英語和西班牙語的雙語國家,在美國,存在相當部分只會講西班牙語而不會講英語的低端勞動人群。難怪哈佛的著名政治戰略家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去世前大聲疾呼:“誰是美國人?”在他看來,美國制度的基礎正在動搖,新教的傳統正在喪失,由此導致美國社會面臨挑戰。
面對這樣一個二元經濟現象,美國當前的經濟制度不但不能化解反而會激化矛盾。美國長期形成的高福利的制度安排,在二元經濟和全球化的催化下,導致60%以上的財政支出屬于賦權性的財政支出,用于失業保險、醫療保險、貧困救濟、低收入家庭過多的住房補貼等方面。這一切使得美國社會中沒有競爭力的那部分人群更加沒有競爭力;而這種負擔將越來越重,又會反過來作用到高端人群身上,使得他們的稅收負擔日益加重。
我們甚至可以合理地推斷,美國式的民主體制應對二元經濟體制很可能是最束手無策的。事實上,今天的美國政壇變得四分五裂:以奧巴馬為首的民主黨人認為,應該增加社會財政開支,以刺激經濟和解決社會矛盾;而以共和黨、茶黨為代表的政治家們,卻想恢復美國早年以新教徒文化為社會核心的傳統經濟制度,那就是大幅度地削減財政開支、削減稅負,以此刺激經濟。雙方一直爭執不下,因此,美國出現了改革意志不清、方向不明的政治局面。
特別令人遺憾的是,美國社會目前沒有出現一批思維清晰且有號召力的學者,為改革指明方向。美國當前的改革與上世紀80年代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的改革不同,當時民眾支持改革的意愿十分強大,與此同時,社會上出現了一批極具感召力的學者,比如出現了經濟學領域的供給學派,大幅度號召私有化、減少管制,以此推動了里根改革的成功。今天的美國政壇顯然不是這個情形。
有理由推斷,美國經濟、政治格局在未來4-5年內很難出現大規模的逆轉,下一屆總統也很難像里根那樣大力地推動改革,社會共識在短期內難以凝聚。據此我們可以認為,美國的主權債務規模很難在短期內削減,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政府所能削減的是一些社會最需要的財政支出,比如科研、高等教育、基礎建設,而傷筋動骨的福利性支出卻不能削減。
基于這一分析,筆者認為,美國經濟復蘇的道路可能比歐洲還要艱難,盡管美國自身具有一批極具競爭力的產業。未來四五年美國的基本狀況,將可能是維持比較低速的經濟增長,財政情況繼續惡化,政治紛爭不斷出現。在此情況下,美國唯一的政策選擇就是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此帶動和刺激經濟的發展。因此,第三輪量化寬松不管以什么名稱出現,可能都是遲早的事情。
歐債危機三年內將有起色
歐元區的狀況也可以歸納為二元經濟:一元是德國,它的制造業與中國等新興市場相互匹配,不斷互補,而且經濟的整體實力不斷增強、極具競爭力,是歐洲境況最好的經濟體;另一元是南歐一些競爭力較差的經濟體,它們所面臨的是必須削減政府福利性開支,不僅是為了平衡預算和削減債務,更重要的是通過削減社會福利的方式增加其勞工的競爭力,跟上德國等歐元區其他國家的步伐。
但是,當下歐洲的問題是,極富競爭力的德國的百姓不愿意為過高社會福利的南歐諸國埋單,德國的政治家很難說服選民。因此,最有可能發生的情形是,希臘、葡萄牙等國家會由于得不到德國等國的直接援助,同時自身也沒有明確的改革意愿用以說服資本市場,最終出現債務的違約和重組;違約和重組將使這些國家面臨不可能再借到新債。最終,只有在被逼無奈之下,這些南歐國家將會啟動改革程序,而改革程序不可避免地會帶來社會的騷亂。在這種情況下,歐債的價格可能將進一步下降,從而給德國和法國的金融機構帶來沖擊,德國和法國政府將不得不拿出財政資金挽救自己的金融機構。換句話講,德國和法國的納稅人由于不愿意直接為希臘、葡萄牙等南歐國家埋單,最后將不得不為自己的金融機構埋單。當然,從政治上講,為自己的金融機構埋單,比為南歐國家直接埋單理由充分得多。假如個別南歐國家出現了違約和債務重組,其他身臨債務危機的南歐國家也會得到警示—必須真正拿出勇氣進行財政稅收的改革,大幅削減社會福利水平。
綜上分析,筆者認為,已經爆發了近兩年的歐債危機可能會在3年內得到根本性的改變,也就是說,南歐國家會進行深刻的改革,而德國等國則將為自己的金融機構埋單。南歐國家的改革是整個國家面臨國際壓力整體削減社會福利的改革,而美國的改革是國家內部針對部分社會階層的社會福利的削減,美國的改革難得多。
新一輪的風暴是貨幣危機
根據以上的分析,美國的財政情況將繼續惡化,經濟改革步履艱辛,而歐洲被逼無奈必須出手改革,3年的時間完成轉變。因此,未來3年之內會出現這樣的情形:歐洲的債務情況得到穩定,金融市場得到恢復,而美國仍在動蕩之中。這時將出現一個很有意思的情況,那就是,金融市場開始擔憂美元的信用,資本會從美國流向歐洲,導致美元兌歐元匯率出現大幅波動,美元危機將會出現,類似于1971年8月前的情形。當然,整個歐美債務調整的過程中,投資界會不斷地看好新興市場經濟體,導致后者的貨幣面臨持續升值的壓力。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當今世界沒有歐元崩潰的機制。無論從歐債危機兩大主角的哪一方來看,歐元垮臺都對它們自己不利。從德國的角度看,如果其重新啟用自己的貨幣馬克,則將面臨巨大的貨幣升值壓力,是引火燒身,同時這也意味著歐洲政治一體化的進程在退步,這對德國明顯不利。從正處在主權債務危機中的南歐國家的角度看,歐元倒臺更是引火自焚,因為如果脫離歐元區,它們自己發行貨幣將面臨極大的市場挑戰,市場會不信任它們的貨幣,而它們此前已經發出的債券是以歐元計價的,它們不可能以發行自己貨幣的方式逃脫已經重壓在身的債務負擔。因此,我們認為,歐元機制不會因為這一次的債務危機而崩潰。
中國必須嚴陣以待
面對這樣一個動蕩的國際經濟形勢,中國必須做好認真的準備。
第一,必須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因為外部市場的需求不可能迅速恢復,貿易保護主義還會一浪高過一浪。
第二,必須管理好自己的外匯儲備。對于已經投入的發達國家主權債務而言,要加強與各國政府的協商,講清楚中國政府是有選擇的,不一定非得把這部分資金投入到他們手中,我們只是出于對世界經濟穩定的考慮,出于負責任的大國的考慮,繼續持有他們的債券,同時提醒發達國家必須要考慮中國的利益,包括自由貿易、臺灣、新疆和南海等政治問題。
第三,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是對流機制的建立,鼓勵中國的企業和居民走出去投資,利用當前國際金融動蕩的機遇,投資到境外的資源型、經營狀況比較好的金融工具中去,尤其是投資到那些與中國經濟聯系緊密、正在分享中國經濟增長成果的境外資產中去,由此獲得中國經濟自身發展帶來的好處,所謂“肥水不流外人田”。
總之,動蕩的國際環境將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這給中國經濟提出了挑戰,但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在動蕩中也蘊藏著可以讓中國經濟不斷崛起的重大戰略機遇,我們在做好認真準備的同時要抓住機遇,利用好有利條件,為中國經濟未來長期穩定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對于本文內容您有任何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