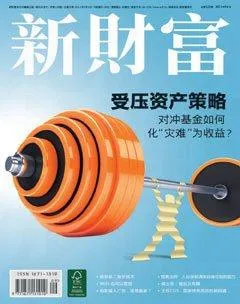從創新能力看美國的國家競爭力
2011-12-29 00:00:00朱為眾
新財富 2011年9期

不要低估了美國的實力
標準普爾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從AAA降低到AA+以后,已經在全球甚囂塵上的“后美國”和“后美元”時代的說法似乎得到了進一步的印證。其實,在這個動蕩多變的年代,在國界日益模糊的全球化大潮中,盡管新興力量在不斷崛起,多極時代在逐步成形,美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絕對優勢不但沒有削弱,從某種意義上反而得到了加強;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權威地位,也在剛剛過去的世界金融危機和美國主權信用降級事件中經受了考驗。
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在一次半公開會議上的一句話發人深思:“事實上,因為我們的真誠,因為我們的市場的開放性,如果你低估美國的實力,那是你自討苦吃。”盡管坎貝爾并沒有一言道盡美國的實力,但我非常贊同他的這個忠告,無論是美國的盟友、競爭對手或是敵人,在審視自己與美國的關系時都可以從中得到啟迪。
那么,美國最不可低估的實力究竟在哪里呢?
創新是美國最大的國家競爭力
一個國家的競爭力,歸根結底是其創新能力,這大約是全世界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都一致認可的。盡管創新(innovation)作為一國競爭力的特定涵義是一個相對新的概念,但是,創新作為大國崛起的主要國家競爭力卻是世界歷史再三證實的不爭事實:
無論是小小的葡萄牙,還是后來與其瓜分世界的西班牙,依賴的都是航海技術的創新,成為捷足先登、掠奪致富的典范;緊隨其后的荷蘭,則是典型的“以盈利為目的,用新穎的方式利用現有知識”的創新者,其在造船業不斷創新,最終以海運和貿易后發制人,在17世紀成功地完成大國崛起;人們在討論英國長達幾百年的世界霸權時總是念念不忘工業革命,其實,工業革命恰恰是最大的創新,它不僅僅表現為工業技術的創新,更表現為工業制度的創新(如工廠制)和經濟制度的創新(包括司法制度和對所有權的保護);如果說法國崛起的創新力量更多得益于法蘭西文化的源遠流長和思維方式的深邃,那么,晚生的德國資產階級則不失時機地抓住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以教育興國,以科技求發展,在夾縫中實現了德意志民族的統一和崛起;日本的創新是以向西方學習為特征的全民族創新,涵蓋科技、教育、軍事、政治和工業,從根本上說是社會的變革和創新。
美國作為世界超級大國的崛起,更從一開始就與創新息息相關:以憲法為綱、三權鼎立的政治制度創新;以汽船業和公路網為標志的交通運輸創新;用國家大法對專利權呵護有方的價值觀創新;以硅谷為代表的高科技集群創新;甚至包括以華爾街為代表的、在金融危機中變得臭名昭著的“金融創新”。毫不夸張地說,美國的歷史本身就是一部創新史,美利堅這個民族的DNA就是創新。
如果說大國的崛起依賴創新,那么,其沒落或是變得平庸,則是因為創新力的衰竭。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幾十年里,美國不但創新能力沒有衰退的跡象,反倒出現了一波又一波可持續的創新浪潮。看看當代一些最偉大的公司—無論是高科技行業的戴爾、微軟、蘋果、英特爾、惠普、谷歌、Facebook;傳統制造業的波音、福特、通用汽車(其迅速的破產保護和重組本身就是創新的典范)、3M、通用電氣;還是顛覆傳統郵局、用快遞方式把包裹送到世界每一個角落的聯邦快遞和UPS,風靡全球的麥當勞、必勝客和星巴克;以及代表美國軟實力、征服全世界的好萊塢電影和NBA籃球,其品牌的核心競爭力其實都是創新。
波士頓咨詢公司一位領導全球創新力調查的咨詢師詹姆斯·P·安德魯 (James P.Andrew)說得精彩:“不是國家創新,而是公司創新。但是,一個國家可以對該國公司的創新能力,包括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以及其他創新所需要的要素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其實,美國公司無與倫比的創新能力,恰恰是該國政府政策、教育制度、人力資源和法律制度所營造的創新能力生態系統(InnovativeEcosystem)成功的佐證。
良性循環的教育制度
為創新提供了無盡頂尖人才
國家的競爭力要看其創新能力,而創新歸根結底全看人的素質,人才是打造一個具有創新能力生態系統的核心資源。
人們常常津津樂道的是,美國有世界一流的教育制度,哈佛、斯坦福、耶魯等世界排名前一百名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一半在美國;而被忽略且更重要的一點是,這一優秀的教育體系不僅僅是培養美國創新人才的搖籃,更為美國吸引了世界各地各行各業的精英,形成生機勃勃的良性循環。
美國的人才戰略是“培養+吸引最優秀的人才”。一方面,一流學校培育優秀人才,優秀人才提升學校名聲,構成一輪良性循環。另一方面,這些一流學校又作為全世界頂尖學子和教學、研究人員向往的圣地,通過吸引人才形成新一輪循環。在中國,清華、北大這樣的名牌大學因為品牌效應,每年報考的優秀學子趨之若鶩,他們在最頂尖的高中畢業生中再三篩選,在慕名而來的優秀教授中百里挑一,想不優秀都不行!可是,清華、北大和世界各國的重點大學卻又都成為美國教育體系的預備學校。領先全球的教育,為美國營造了一個獨特的人才壟斷地位,為可持續的創新提供了取之不盡的人力資源,為美國保持創新這項國家競爭力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除了人才和高等院校這兩個核心資源外,美國還在創新能力的生態系統所具有的主要其他資源上獨占鰲頭: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實驗室;高科技公司云集、形成集群效應的硅谷;一流跨國公司提供的就業機會,這些都是其他國家在相當長時間里難以超越的。
去年我在上海的一個會議上巧遇哈佛大學商學院院長杰伊·萊特(Jay O. Light),當談起為什么該院要建立上海中心時,他回答說:“中國正在成為一個世界中心,作為世界頂級的商學院,我們首先要置身其中,去了解,去感受,去參與;我們在上海的中心并不賺錢,但是它已經成為我們教授的一個海外培訓中心,他們在輪流到上海來執教的同時,又學習和了解中國,拓展了自己的視野;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學生都是或將成為中國的商界領袖,我們到上海來就是要吸引中國最優秀的人才!”我聽了這一番話受到很大的震動,世界最負盛名的商學院果然了得,這樣的視野怎能不培養和吸引人才?
批判性思維是創新的源頭
什么是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簡單說,就是一種挑戰傳統、懷疑假設條件的思維方式。批判性思維是人類不斷創新的最大動力,而思維方式無疑也是最難摹仿的競爭力。
最近,我應“七姐妹在中國”的邀請,以顧問身份參加了她們在北京舉辦的“女性及青年領導力論壇”,感受很深。“七姐妹”包括芭娜德學院(Barnard College)、博懋學院(Bryn Mawr College)、曼荷蓮學院(Mount Holyoke College)、拉德克利夫學院(Radcliffe College)、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和維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等七所文理學院,其創建于1837-1889年,歷史上均為富于盛名的女校,美國現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前勞工部長趙小蘭、宋美齡、冰心、復旦大學前校長謝希德等杰出女性均畢業于此。“七姐妹在中國”則是“七姐妹”學院的中國女留學生創立的非贏利組織。
我受到的最大觸動是,會議組織者在美國教育制度里獲得的最大益處是批判性思維方式的訓練,這在她們的言談舉止、擇業和生活閱歷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并和參會的未出國大學生形成明顯的反差。芭芭拉·侯(Barbara Hou)放棄待遇優厚的律師職業,中斷博士學習,為創辦亞洲女性領導力大學四處奔波;自由創業人張東櫟專注于改善氣候和綠色建筑研究,為政府和企業提供咨詢。她們選擇的事業領域迥然不同,但都讓人感到血液中的創新,其源頭就是在美國受到的批判性思維教育。
在美國,文理學院的最大特點在于:
1.學校規模小,強調對學生更多的關注和教室里的互動;
2.學生全部住校,強調住校為學生帶來全新的生活環境,包括文化、政治和智力開發方面的種種活動;
3.最重要的一點是,注重博學,大學一、二年級時讓學生在不同學科(文理并重)的互相沖擊中受到熏陶,然后再選擇專業。
不要小看了這三條,它們塑造的是一種不同的思維方式—批判性思維,而批判性思維是任何創新的前提和基礎,也是領導力的核心要素。遺憾的是,這恰恰是中國教育制度最欠缺的。2010年在南京舉行的第四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萊文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留學生缺少批判性思維,認為中國需要鼓勵學生的創造力以及獨立的思維能力。他特別批評亞洲和歐洲大學過早讓學生選定專業,且很少涉及專業之外課程的教育模式:“這種模式,對于培養一些流水線上的工程師或是中層的管理干部可能有用,但是,如果培養領導力和創新人才就顯得過時了。”
美國的文理學院所強調的通識教育,則通過博學產生超越單科束縛的視野,塑造解決新問題的應變能力和以創造性理念解決問題的習慣。這種訓練方式的最高境界就是培養學生最終的創新能力,敢于推翻立論,提出獨到的見解,能夠應對變化多端的世界;而中國的教育模式是在學生的腦子里灌滿實用但容易過時的知識,所灌輸的社會價值又是根深蒂固的“聽話”這樣一種非批判性思維。
最近有兩個事實讓我對美國的批判性思維方式有新的認識。
首先是金融危機后的世界動蕩不安,可是美國這個可以充分發表意見又受到最大沖擊(高失業、房地產危機、汽油價格飆升和通貨膨脹)的國家,社會卻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穩定,沒有北非、中東的血腥暴力,甚至沒有倫敦式暴力事件。純屬偶然嗎?不然!我覺得,這和美國人比較理性的批評性思維方式和他們對自己制度的創新能力、糾錯能力有信心有著重要的關系。
再者,就是標準普爾將美國主權信用降級引起一片譴責之聲,從政府高官到跨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幾乎異口同聲地批評標普的計算錯誤和選擇的時間錯誤。從一個消費者和企業高管的立場,我本人也覺得標普的做法頗多欠妥之處,但是,它不從眾、不屈于權威的做法,仍值得欽佩,在全世界哪個國家可以做到這一點?其實,這里最可貴的不是標準普爾的勇氣,而是營造其創新能力的生態系統和鼓勵這類行為的批判性思維。我可以不認同標準普爾的做法,但我極其看好這一創新生態系統和思維方式。
中國提高創新能力勢在必行,機不可失
筆者以為,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的地位還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太多的分析家和政治家低估了美國的國家競爭力—創新能力。歸根結底,美國強大的政治機器、無與倫比的軍事力量、極具韌性的經濟體制和久經考驗的法律制度,無不與創新息息相關。創新是最難摹仿的也是最具生命力的國家競爭力,而美國的國家競爭力恰恰是創新,創新是美利堅民族的DNA,流在他們的血液里。創新靠的是人,人創新靠的是理念,即批判性思維。
中國在過去的30多年里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創新也終于提到政府和企業的議事日程上。“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提高教育現代化水平,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壯大創新人才隊伍,推動發展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依筆者之見,這也是“十二五”規劃中最難做的一件事,因為它牽涉到人的思維方式的改變,提倡的是對傳統“一元化”思維方式的挑戰,是對“聽話”文化的反叛,是對育人觀點和教育體制的革命!
美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先進的案例,3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為我們奠定了基礎,歷史為我們提供了這個機遇,此時不為,更待何時?
對于本文內容您有任何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