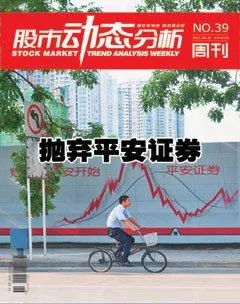觀歐債危機三種演變路徑定策略
本文意在指出一些預料之中的標志性事件,能夠“先市場一步”,以方便各位自己來鑒別未來危機演化的脈絡。當我們能夠清楚整個事件究竟走在哪一條線索之上時,給出判斷、制定策略并非難事。
在歐債危機中,我們不是去談論如何避免一場危機,這個問題用不著我們去傾注智慧。就一般投資人而言,如何防范極端風險與把握這千載難逢的機會——才是需要考量的問題。只有“看清”眼前危機可能的發展脈絡,才會發現其中蘊藏的風險與機會。
皆大喜歡結局:“歐聯邦財政部”的誕生
歐債危機發展至今,還存在“逆轉”的機會嗎?答案是肯定的,但需要滿足兩個條件:歐債危機得以“根本性解決”,全球經濟增長“不出軌”。前者的標志性事件是什么?——“歐聯邦財政部”的誕生。后者的標志性事件是什么?——至少2011年四季度經濟增長維持緩慢復蘇態勢。二者缺一不可。
出現這樣的組合,意味著歐債危機“結束”,至少半年以上的平穩期將出現,危機警報徹底解除。全球股市將迎來系統性機會,一輪可持續的中長期上漲行情,A股也必然惠及。
問題是,“歐聯邦財政部”的誕生能“根本性解決”歐債危機嗎?
簡單來說,歐債危機的“本質”是凱恩斯主義的“副產品”——家庭債務向國家債務轉移的必然結果。解決債務(國家、個人)的手段有且只有兩種:其一,讓它破產,甩掉債務包袱,重新開始積累;其二,壓制市場利率,放寬其信用,等待其收入出現“奇跡”。
要以最小代價解開當前歐債危機的“死結”,只有成立“歐聯邦財政部”這唯一途徑才是根本性辦法,其他方式都只是延緩危機進程。成立“歐聯邦財政部”,可以將希臘債務問題“完全轉化”成為歐元區“內部”問題。通過內部債務重組,或涉及主權的“硬約束”來調整其財政政策,從而避免歐元區“分裂”導致歐洲銀行間出現流動性風險。然而,僅靠目前“貨幣聯盟”的政治架構,是無法做到上述結果的。這一點基本上已經是“共識”。
“共識”為何遲遲不能轉化為政治主張或措施呢?問題在于,人性抉擇總是選擇“次壞”結果。如果不看到更壞的結果出現,人們總是無法接受看上去“較壞”的策略。歐元區各國領袖及國民(特別是“歐豬五國”)仍期望貨幣聯盟能夠解決問題,而不需要扔出“主權”作為籌碼。所以,這一博弈過程的曲折將帶來一些不確定性。這是歐債危機不斷升級的“關鍵點”。
一旦“成立歐聯邦財政部”列入歐元區會議日程,主要發達經濟體在四季度經濟數據不出現超預期下滑,那么負面預期的反身趨勢將可能被逆轉,從而迎來正面預期的反身趨勢。“歐聯邦財政部”的誕生,將作為危機結束的標志性事件來確認這一正面預期趨勢的成立。
中性結局:筑“防火墻”暫時脫險
“虎口脫險”的結局,同樣需要滿足兩個條件:歐債危機得以“階段性緩解”,全球經濟增長“不出軌”。前者的標志性事件——流動性危機“防火墻”的建立。后者標志性事件——至少2011年四季度經濟增長維持緩慢復蘇態勢。
一旦這一組合背景出現,意味著歐債危機“短期見底”,三個月左右的平穩期將出現。A股則迎來2011年“年內確定性最強”的一輪上漲周期。
我們需要重點關注:歐洲各國銀行的風險敞口是否收斂——比如,希臘能否得到下一波援助資金?歐洲某些銀行出現巨額投資虧損?歐洲貨幣聯盟或國家是否拿出資金來補充歐洲各國銀行的資本金?以及救助政策的明朗化?
簡單來說,當前金融市場的動蕩,是由歐洲銀行間流動性危機而起。流動性危機又是因希臘面臨違約為“引爆點”——歐債危機“升級”后的衍生傳導。無論希臘違約,抑或退出歐元區,對于歐洲銀行來說,都意味著需要做一次性債務減記。同時,這也是流動性危機“風險最高點”。倘若各國政府聯合出手為歐洲各國銀行“保命”度過這一關,等同于建立“防火墻”阻斷風險傳導,那么希臘債務違約在金融市場層面的風險影響就會大大收斂。
盡管“防火墻”只能確保一時,在下一個“希臘”出現時未必能夠再起作用。不過,三年前雷曼兄弟之死的經典案例還擺在案頭,令各國政府除了不斷筑高筑厚“防火墻”的墻體,暫時也不敢嘗試它法。
近日由歐央行牽頭,五大央行聯手提供美元流動性以幫助歐洲的銀行業應對年底的流動性匱乏,正是修筑“防火墻”之舉。只是這“墻體”還有待進一步加厚,方能抵御下一次沖擊。
舉個例子來說,當年朱镕基重組中國銀行業,特別成立了四家資產管理公司,通過特別國債形式將國有銀行“壞資產”置換出來,并通過股份制改革以及強化監管的一系列制度措施,進而才使得中國金融業“死里逃生”。
為什么朱镕基不只是讓中國央行多提供一些鈔票給四大國有銀行來解決債務減記呢?因為,靠短期拆借資金修筑的“防火墻”,只是保命之策,緩沖之策。
低成本流動性的無限供應,使得銀行不至于“突然暴斃”,但無法改變慢慢走向死亡的趨勢。所以,只要一大批等待倒下的“雷曼”依然在那里嗷嗷待哺,那么“防火墻”未來所承受的沖擊,只會因為負面預期的反身影響而不斷強化,直至金融體系最終崩潰。
期待中的“防火墻”是什么呢?歐洲各國政府拿出超預期的銀行救助方案,并且希臘債務與歐元區金融安全,歐元區與美、中金融安全之間都需要存在“防火墻”。在歐債危機得以“根本性解決”之前,“防火墻”的厚度決定了危機蔓延的進度。
悲劇結局:生靈涂炭
“生靈涂炭”之結局,也存在兩個條件:流動性危機演化為金融風暴,全球經濟增長受到拖累“出軌”。
一旦這一組合背景出現,意味著全球經濟病入膏肓,數年蕭條不可避免。特別是,凱恩斯主義所指導下的貨幣政策一旦開“倒車”(迫于通脹壓力而緊縮),負面作用相互疊加,全球經濟將付出沉重代價,A股與中國經濟同樣難以幸免,甚至于成為下一個風暴眼——房地產泡沫破裂與地方債危機爆發。
當然,沒有人會被動等待這一切發生,尤其各國政要。這樣的結局與樂觀結局只有一線之隔。當上層建筑被迫做出一些改變的時候,歷史所書寫的結局也會悄然改變。
流動性危機演化為金融風暴的標志性事件是什么?歐元區“防火墻”被攻破失效,歐洲銀行間流動性枯竭導致一批“雷曼兄弟”出現。
全球經濟增長受到拖累“出軌”的標志性事件是什么?主要發達經濟體紛紛陷入“滯脹”,甚至部分國家出現通縮,四季度消費數據、就業數據滑入低谷,與2008年相仿甚至更差。中國出口數據大幅下滑,房價下跌而成交稀少。
我們需要重點關注:歐洲各國銀行出現“倒閉潮”,這將是“序幕”。
“生靈涂炭”與“否極泰來”的分界點在哪里?坦率說,我并不清楚未來出現的“分界點”將會發生什么樣的標志性事件。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絕不會是另一個“四萬億”或QE(量化寬松)。因為,持續量寬的前提(債務轉移的過程完成)已經不存在,如果再加大劑量,只是加速滅亡,而不是重獲新生。
從好的一面來看,即便全球經濟陷入數年蕭條,也并非完全的悲劇。畢竟,通過量化寬松,完成了家庭債務向國家債務的轉移。私營部門的現金儲備遠遠好過2008年。只要后續不出現令人窒息的高通脹,一定程度的“通縮”并不會造成發達經濟體迅速走向衰亡。當然,這些分析并不適用于中國國情。
面對全球經濟陷入低增長或零增長甚至負增長階段,中國經濟的挑戰來自于支撐持續高增長的需求動力缺失。由于國內生產資料的高度壟斷與資源依賴癥的“惡化”,原有利益環鏈將承受格外巨大的“再造”訴求——即二次分配機制的重建。
倘若中國經濟能夠完成涅重生,依托各地發展不平衡的客觀環境,在體內構造足夠大的供求循環。那么,經濟也好,A股也罷,都會踏上新的征程。縱觀歷史,任何一個超級大國的崛起,都是以“災難”為契機來完成霸主地位的更替——上世紀美國經濟發展史就是一本最好的教科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