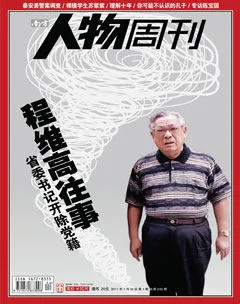亞利桑那槍擊案對美國的警示
2011-12-29 00:00:00丁果
南方人物周刊 2011年4期

分裂美國的最大隱患,變成了左右翼兩個極端的對立紛爭
美國歷史顯示,每次國內外重大事件,尤其是慘劇的發生,都會成為重塑美國的契機。大的國際事件,如上個世紀的兩場世界戰爭、韓戰越戰、“9·11”恐怖攻擊,都對美國產生了正面或者負面的影響;國內的事件,如肯尼迪總統和馬丁路德·金博士被暗殺,也都帶動了美國的改變。那么,近日發生在亞利桑那州圖森市的血腥屠殺案件,到底對今天的美國意味著什么?
兇手洛克耐爾針對的顯然是民主黨明星女議員吉福茨,但她跟臺灣槍擊案的受害政治人物連勝文一樣大難不死,而在現場的州首席聯邦法官約翰羅爾等6人,則成為兇手大開殺戒的槍下冤魂。
在容許自由持槍的美國,各類“狂人”針對政治人物,包括議員和總統的暴力襲擊和暗殺,并非什么新鮮事。陰謀策劃也罷,為了成名也罷,發泄不滿也罷,殺人滅口也罷,槍擊案的理由五花八門,但這次暗殺因由的輿論解讀,卻是最為復雜,意識形態意味最為濃厚。
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亞利桑那州雖然不大,但在最近一段時間里,卻成為美國乃至世界的輿論關注中心。因為它嚴厲對待非法移民,引發了全國的大討論,也讓媒體相信,州內炙熱的政治對立氛圍,可能是兇手痛下殺手的誘因之一;或者,至少槍手曾經對高度政治化的醫療改革法案不滿,因此施行暴力。另一方面,槍擊案一發生,有媒體就把矛頭指向共和黨原副總統候選人、在剛剛結束的國會中期選舉中成為最大贏家的茶黨精神領袖佩林。因為在選舉中,她的網站上曾把包括吉福茨在內的20名議員標上十字瞄準線,發誓要把這些人拉下馬。
因此,輿論認為,佩林的做法無疑創造了引發暴力的政治氛圍。對一場槍擊案的討論,陷入了政治攻擊的危險區。
按照慣例,美國一旦發生慘劇,立刻就會成為超越政治分歧的最佳黏合劑。政治領袖不管朝野,不管左右翼,不管共和民主黨,都會同仇敵愾,譴責暴力,呼吁團結。從表面上看,這一傳統并沒有改變,眾議院共和黨議長博納第一時間發表講話譴責暴力,奧巴馬總統也在追思會上發表宣言,聲稱分裂的力量戰勝不了團結的力量。
但從深一步看,被媒體批判宣揚政治暴力的共和黨保守勢力領袖佩林,選在12日打破沉默,8分鐘的視頻講話反擊批評者是制造“血祭誹謗”(指反猶太主義者對猶太教徒的虛假指控),實在是另一種形式的煽動仇恨與犯罪。
佩林的強烈反擊,以及白宮對此拒絕評論,都充分表明在奧巴馬成為總統緩和“黑白對立”之后,分裂美國的最大隱患變成了左翼和右翼兩個極端的對立紛爭。而這種紛爭正在吞噬美國的優良傳統和面對危機挑戰的團結。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紛爭不但體現在移民政策和醫療健保制度的改革上,同時也將影響到正在揭開序幕的2012年總統大選。奧巴馬在其政治發源地芝加哥已經成立競選連任總部,而人氣正旺的佩林也被視為共和黨保守派的最佳總統候選人。
如此一來,一場慘劇的應對,夾雜進總統選舉的私心,以及政黨爭斗的小算盤,極有可能演變成新的民粹主義。這對美國的發展形勢相當不利,也是對慘劇受害者的二度傷害。
為什么會產生這種狀況?美國在遭遇戰爭失利和金融危機的雙重打擊下,傳統的寬容大度日漸削弱,理性平和也漸成奢侈,再加上朝野和國會內部的政黨協商變得更為困難,導致政黨斗爭進入惡性循環,朝野不信任加劇,意識形態對立大行其道。
以美國的超強地位,被外來勢力打倒的可能性幾乎是零,而倒在國內水火不容的政治分裂中則完全有可能。因此,美國如何將這次亞利桑那州的悲劇,轉化成一種認真的反思,帶來美國政治現狀的變化,顯然對奧巴馬的白宮,對佩林陣營,都是嚴峻的考驗。民主政治,當然就是政黨制約,但是在政黨政治以外,美國如何在國際國內議題上形成共識,尤其在突發事件上形成共識,對美國的未來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