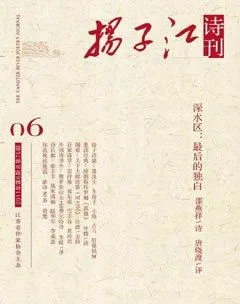蘇野的詩
影子之詩
凌晨,我的影子
從睡夢中醒來、直立
像尺蠖,在桑葉上
拉長肉身,借著
衰朽的月光
沉思擬態,和得救的倫理
所到之處,像推土機
把土地都得罪光了,很難
不躲著再在地上爬行
肉體,像讖語
在強大、暴戾的白晝之光里
只能生產遼闊的影子
為夢境殿后
可以活著,可以不
依賴起重機,給黑夜報信
那不透明的絨毛
拒絕命名,和分類
希望正在于此:
在整容室里,從一個人成為
所有人,成為遺忘
在虛無中贏得一席之地
短歌行
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古詩十九首》
我喜歡簡陋的及時行樂
喜歡重復和麻醉,但不是抽筋
我像瓦礫,耽溺于重力
又確實像塵埃一樣屈從于風
沒有變遷,我折磨著屬于我的時間
正如它的鈍鋸子折磨著我
讓它空心,我只與自己
與少數喪失自我的人保持連線
讓頹廢像園林和假山一樣精致
而不失木石的本性。讓我尋找我并不高尚的肉體
在“物”中的坐標。我是我虛有其表的法人
沉浸在賬目之中,而遺忘了欠債
要有原罪之盾,才會有救贖
必須停滯,才會有繁衍的神圣時間
我確實必須看見高速公路,才能說我有未來
以及“從惡中引出善”注的此刻
注:朋霍費爾語
擬古:與臧北書
你說,遠道而來的
都是絕望,都是完成的讖語
像紫藤,霸道
而年代久遠,那
尋找宿主和未來的寄生者
讓我們對言說
心生旋渦般的倦意
在信仰里,作為六道之中的微塵
我們循環得太久
而自我卻喪失得遠遠不夠
仍保有一片問難的衣角
呼應著光的節律,在風中偃仰起伏
需要重溫分類學
將擁有之物歸類,給絕望
填表格:這是罪孽
那是果報,還有籍貫、美善,和時間
那么,現在好了
現在是肉體的、傍晚的悲傷
一切都將無足輕重
肉 身
——與育邦、江雪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我們在同一個過道里踱著
它是迷宮的,也是
時間的;是墳墓、記憶和善的
也是括弧、肉體
和刺刀、機槍、汽油的
我們平視、撫摸、下沉
像飛機降落;偶爾
小便、靜息,凝望風物和六朝煙水
消化黑暗,漸漸喪失了
重力。似乎存在某種絕對的“小”
我們灌了鉛的震驚微不足道
正如呼號的肉體注滿
絕望的濁氣——只涉及肉體
我們有共鳴的味蕾
卻沒有交談——我們是一個人
替身千變萬化
消失是確定的
殘忍而粗暴,沒有美學與酒
并且來不及復活
一夜讀書,看黎明從同里湖升起
空氣中的清冽,毛手毛腳
沿著草木的高壓泵
步步升高,逼近嗅覺
書房里漸漸擠滿青色的天光
歷史、公正與偶然性
平躺在桌子上,與書架垂直
我將鼻子探出窗外,霧
像往昔一樣稀疏,且無往不在
湖面,一段素樸簡省的光譜
幾乎看不出修辭的坡度
鷂鷹一上一下,一遠一近,恰如
萬物和我的意識,要擺脫搖晃的影子
白晝的各各他
總是以安靜、秩序、短暫
和光的變化作為開始
這與人正好相反,我們
一直傾向于從加長的錯誤中
尋找天籟及和解
失敗之詩
到了該向蟋蟀學習的時候了
不飛,它們就
摩擦翅膀,損傷肉體
別人叫,它不叫
別人在高處叫,它在低處。就像
草叢和夜晚的聲帶
那失眠者的省略號
像孑遺的礦石,從河床上
圓鼓鼓地滾出來
大地上人來人往,而天氣乖戾
除草機帶著飛機的嗓門
熨斗般推銷著時代的面孔
明天絕不會保持安靜
我沒有成功地變得卑微
也不像鈾那樣高尚
因而深懷著為惡作偽證的歉疚